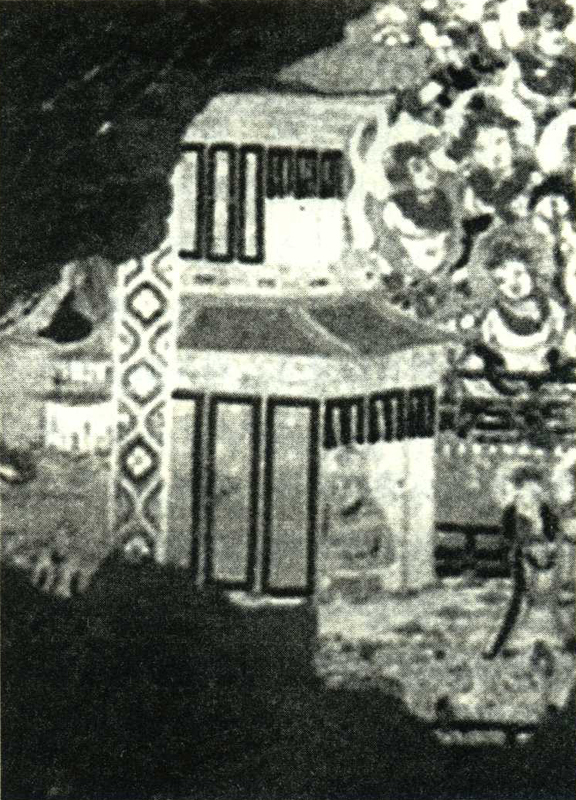唐朝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文化及其艺术的繁荣时期。作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也是佛教中心。我国甚至世界佛教的高僧在此荟萃;其佛教思想、佛教建筑及其艺术都直接影响周边,如甘肃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鲁番、库车等地区,以及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政治交往,可以因各种人为因素而分合、变化,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联系和文化影响,却会永远继承下来和发展下去,它自然会给人类和各民族留下共同前进与团结和睦的历史印证。
一、安西僧人东到长安促进译经事业的发展
公元640年,唐朝统一西域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公元648年,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辖有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当时据守龟兹的汉兵就达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它所管辖的佛寺竟有数千处,僧尼人约有数万人。
至于说到安西僧人在唐朝去长安传送佛经,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之事,那就自然多了。据宋人赞宁写的《宋高僧传》的记载,安西僧人去长安的就达10余人,其中有的还死葬在长安未归。下面选择几个较有成就的佛经翻译者略作介绍:
一、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利言。利言,龟兹本土名叫地战涅罗,意即真月,字布那羡,也称利言,或礼言。唐朝中期的佛经翻译家,也是龟兹地区继鸠摩罗什之后又一个较有成绩的佛经翻译家。早年,他曾师从东印度来的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修习密典。公元726年(开元十四年)受具足戒。此后,他更刻苦钻研,听习律、论、大小乘经,还学会了梵书、汉书、唐言文字,石城、四镇、护密、单于、吐火罗语等。这些都为他后来去长安等地翻译佛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利言充当“译语”随师法月赴长安奉献北天竺沙门阿质达散,在安西译出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正经》《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和《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等三部经。师徒俩经过两年的行程,于开元二十年(732)到达长安。据记载,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法月三藏翻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则是由利言译梵语并笔受。①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由唐玄宗批准,“依许八月十日在安国寺开经”的系列讲经会上,法月是主讲者之一,他讲解玄宗所著的《金刚经注》和《仁王般若经》的梵本经,利言仍充当汉译语。利言在长安停留的十年间,他的翻译水平得到锻炼和提高,除先后参与翻译多部经卷外,还将其师奉献的方药、本草等译成汉语,并奉进于上。
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唐玄宗诏不空三藏到武威翻译密典,同年十月又使牒:安西追僧利言河西翻译。次年二月,利言到武威,被安置在龙兴寺及报德寺,与不空“同案译经”。利言在河西等地究竟参与译经多少,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是不空翻译的经籍有:《金刚经注》《仁王般若经》《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观现证大教王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规轨》等,当也应有利言的功绩。利言后来又到长安参与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佛说大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等,被封为翰林待诏,称为翻译大德。《宋高僧传·圆照传》记,圆照曾撰《翻译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大正藏》中收集有《梵名杂语考》一书,署名为《翻译大德兼翰林待诏、光定寺归兹国沙门礼言集》。其中“光定寺”应为“光宅寺”;归兹国即为龟兹之异写,“礼言”即“利言”之异写。该书收集了1250多个名词,以汉文和梵文相对照,并用汉字注明梵语的读音,其内容与他从事的翻译业务是一致的。我认为《梵语杂名》应是利言所集,结合前述他一生的译经事业,我们可称其为翻译家。
利言两次赴长安都挂锡在光宅寺。光宅寺位于长安城光宅坊的横街之北。唐仪凤二年立,武后二年置七宝台。该寺中有尉迟所画之降魔变,其普贤堂也为尉迟所绘,其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等享誉古今②。如此多且精美的尉迟画,看来该寺似与西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至贞元十年(794)圆照集《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时,光宅寺仍保存有法月和利言奉献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三卷,三十五纸;《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一卷,五纸;《秽迹金刚禁百变法》一卷,三纸……《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二纸,今见在光宅寺。”圆照将“玄宗朝所翻经遗漏未入古今录者,其经本或有寄入般若经部龙字号帙内。”
二、释玄觉,高昌人,唐玉华寺之僧。曾“从玄奘三藏研严经论,亦于玉华宫参予翻译”。③译经有《大般若》《宝积经》等。
三、释智严,原姓尉迟氏,名乐,本是于阗国的质子。神龙二年(706)五月奏乞以居宅为寺,名奉恩寺。在长安时“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奉敕于此寺翻经,多证梵文,诸经成部,严有力焉。严重译出生无边法门陀罗尼经。”④
四、释慧琳,姓裴,疏勒国人。在贞元四年到元和期间,曾引用“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藏于唐京师西明寺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⑤
此外,龟兹僧人若那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并授与崇福寺僧普能,等等。
总之,唐朝之所以译经很盛,汤用彤分析其原因有四:“一人材之优美;二原本之完备;三译场组织之精密;四翻译律例之进步”。⑥而作为唐朝的安西为什么能出众多杰出的译经者,原因也在于此地不仅早就设有译经的译场,所译经籍中的密藏也不少。另外也由于当时安西的社会语言条件,从早期的鸠摩罗什、昙倩、法月、直到无能胜、莲花精进、利言等都是安西的精英。他们所译的经籍,对当时和以后我国的,特别是国都长安一带密教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应当说,这是安西。尤其是龟兹佛国僧人的贡献。至今,我们尚能在龟兹地区的一些石窟如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壁画中看到一些当年杂密和密宗的宗教思想痕迹。
二、长安僧人在安西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交流
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安西,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联系起来。佛教及其文化东传始于汉晋,但佛教的大力发展及其中国化,始于北魏而繁荣昌盛在唐代。
自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西域就正式统一在西汉中央政府属下,这个第一个都护府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政治和版图上解决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在丝绸之路的沿线上构筑众多的烽燧,设立了许多戍边的屯垦点。既发展了丝绸之路中段的经济,同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上的驻军和商旅、僧人的供应。据记载,我国最早西去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智严等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的。
后来,由于中原战争纷飞,中央政府弱化了对西域的管理,东西方的佛教文化交流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响。自隋唐统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唐朝中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主张各民族团结和睦,不断疏通和加强对丝绸之路的管理,因此,东西方的经济贸易来往和各种文化的交流,更是明显增多。这时赴印度瞻仰圣迹,寻求佛教经籍的道路畅通。
据史籍记载,安西大都护府时期,西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对来说是新疆中古史上最好的时期。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长安僧人也不少。汤用彤在谈到西行求法之运动时说:“隋炀帝锐意凿通西域,及至唐初,威力震远……中外交通因之大辟。而玄奘西征,大开王路,僧人慕高名而西去求法者遂众多。义净三藏作《大唐求法高僧传》,仅就一己闻见,时限太宗、高宗、天后三朝,所记已有六十人。义净自谓‘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则其湮没未彰不知凡几,而求法之盛概可知矣。”⑦据《宋高僧传》资料不完全统计,唐朝经陆地通道的名僧不少于20人。其中长安的僧人主要有:
释玄照,“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后来,“杖锡西迈……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山。……陟葱阜而翘心……途经速利,过吐火罗。”⑧。
释慧日,唐洛阳罔极寺,中宗朝得度,后遇义净三藏,造一乘极,他“誓游西域”;返回时,再“登岭东归,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⑨
释悟空,姓车氏,本名车奉朝,出家后,号达摩驮都,华言法界,住唐上都章敬寺。天宝九年(751)官宦张韬光率吏40余人,自安西出发西进,悟空随使臣西去。他历游印土,“取安西路,次疏勒国,次度葱岭”,前后40年,至德宗贞元五年(789)返国。他记载了疏勒、龟兹、焉耆等地的情况,并带回《十地经》《十力经》《回向论》等。⑩
此外,还有新罗僧人慧超,他留下的记录成为研究新疆佛教的重要资料。
当时西去求法的动机何在?汤用彤分析为“一在希礼圣迹,一在学问求经。”他认为这两者是“当时佛徒之注意所在。求得律藏,义净、道琳是矣;求得瑜伽,玄奘是矣;会宁之于涅槃、义辉之于摄论、俱舍;无行、玄照均常究心中观。凡此诸端,似为印土所流行,而中土人士所欲究心者也”。(11)
佛教文化要想发展和繁荣,它的基础必须是经济大发展,它的前提必须是政治与社会稳定,这是任何国家和任何历史时代所证明了的。我们说,中国隋唐时期,特别唐朝中期,佛教文化之所以兴盛、繁荣,全赖当时经济高度发展、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各民族团结和睦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我们新疆来看,安西都护府的建立,也是上述条件较好具备的最佳时期。
唐朝在新疆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公元640年治所先设在东部高昌(今吐鲁番),公元648年后又西迁至龟兹(今库车),无论它迁到何地,一是离不开丝绸之路,二是离不开佛教中心。唐朝时期安西大都护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继承和重视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新疆现存的著名石窟如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以及地面残存、现已毁坏的库车雀离大寺等佛寺遗址,都是唐朝兴盛时期使用的大佛寺和著名的典型石窟群。上述石窟和佛寺留下的佛教文化艺术连同历史上被外国探险者掠夺的壁画、佛像和文书等,都是珍贵的瑰宝。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不仅可以代表新疆历史上佛教文化的灿烂,可以反映唐王朝当时的兴盛轨迹,更能说明在唐朝管辖下的安西大都护府的关系,包括管理佛教的僧统都由长安僧人担任。例如库木吐喇第16窟曾被日本人大谷光瑞割去的壁画中有题名“大唐□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供养人像就是有力的历史证明。说明安西四镇的都统,原是“大唐□严寺上座”。此外,安西许多佛寺有来自中原,特别是京师长安的僧人,如安西的“大云寺主秀行……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晖……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连于阗龙兴寺、疏勒大云寺的主持分别是冀州、岷州人士主持。(12)
这些路经安西的和来自长安的僧人们为推动东西方佛教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长安佛寺模式影响了龟兹石窟形制与壁画内容
唐朝长安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大都市、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作为佛教中心来说,长安城中有许多重要的佛寺,据统计,唐玄宗时,全国佛寺主要是长安,竟达到5358个(僧寺3235,尼寺2123),僧75524人,尼50576人。(13)公元581—667年(隋—唐高宗乾封二年)的203个高僧中,有168人(82.76%)集中于长安中心地区。(14)其中的著名佛寺有:唐太宗时的弘福寺、高宗时的慈恩寺、西明寺、青龙寺、光宅寺、黄圣寺,中宗时的大国安寺、荐福寺等。由于云集各国僧侣、商客,长安同时又成了全国佛教传译中心,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多形成于此。建造佛寺是这一时期佛教繁盛的集中表现,佛寺建筑更成了都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长安佛寺建筑的形制布局不仅影响了西部的敦煌,以至西域的安西等地,甚至还影响到东边邻国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
目前,在长安佛寺中除了几座佛塔尚残存外,几乎都已湮没于地下,因此对佛寺的形制布局的研究,只能从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大量的壁画、美术资料中去探寻与研究。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记载,长安有寺塔34处。但随着改建与扩建,“多院式佛寺真正开始盛行却是在唐代,这可以从唐宋文献中屡屡出现的一寺多院的记载得到证明”。(15)另外,从青龙寺、西明寺两个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以及敦煌莫高窟第172等窟的壁画中的大型经变画,如观无量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经变等300多幅壁画里对唐代多院式佛寺的描绘也能得到证实。
唐代安西的佛教寺院情况,虽然在有些史籍,如《大唐西域记》等中有些记载,但仅是宏观的描述,对具体的形制、雕塑和壁画的内容等涉及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也就是说没有文字资料可供查寻;现存地面的佛教遗址也遭受严重破坏,被挖掘的面目全非,难以看出唐代时期的布局,更谈不上完整的雕塑和壁画了。但我们仍可以在现存的石窟壁画中追溯到唐代时的点滴的踪迹,那就是在现有一些汉风的石窟壁画,找到那么一点点尚能证实,也只能从一些极少的壁画中看到当时长安佛寺建制布局对西域各佛寺起过一些影响。
先从佛寺的建筑来看,尽管地面的佛寺已荡然无存,但在原安大西都护府附近的汉风比较典型的库木吐喇石窟群中第16窟主室左侧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中却绘出形似唐时佛寺的风貌。在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一处多院落式佛寺,寺周围有土红色墙耸立,右侧大门敞开,大门外紧接着又是一栋院落。建筑图的本身具有“向背分明”之感。此组图虽剥蚀严重,不能全面看清和辨认佛寺全貌,但多少也还能窥见到唐时长安典型的多院式佛寺一斑。
1999年曾在库车县城北面阿格乡琼勒塔格山库木鲁克艾肯沟内西崖上发现的阿艾石窟,也是一座典型的汉风窟,建于唐代安西都护府时,洞窟的正壁也像敦煌莫高窟壁画一样,绘有一幅《观无量寿经》变图。画面中也反映出唐代佛寺的建筑。(图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宏伟的佛殿中,众多菩萨围绕着佛倾听说法,形象十分生动,场面也很活跃。画面中的大殿、亭榭、窗棂、栏楯等完全表现了中原地区唐代寺院建筑的形制。
唐代汉风窟的库木吐喇第16窟中主室右壁和阿艾石窟所绘的《观无量寿》经变图,描绘着高耸云端的楼阁,绿色琉璃瓦垒出屋顶,蓝色琉璃瓦的屋脊和两端的鸱尾翘起。(图2)楼阁前方菩萨乘象奔腾在彩云中,系着飘带的筚篥、长箫等乐器,不奏自鸣。在第73窟的“乐舞”与“飞天”图,同样是描绘唐代经变画。画面上方残留佛坐的莲花,建筑物前面的池中水波涟漪,莲花挺立。台榭上,一舞伎着白裙,挥动红绸,踏脚起舞,左侧乐队坐毯伴奏,真是一幅歌舞欢乐景象。在吐鲁番的石窟中也有一些唐代故事图,其中反映了长安佛寺建筑情况,如胜金口现存的经变图。(图3)
唐代佛教寺院中描绘的众多经变故事画,一是随着佛教经籍的通俗化传播而盛行用绘画表示;二是唐代名画家高手众多,这些画家往往在寺院作画,施展才能。仅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就列出荐福寺、兴善寺、慈恩寺、龙兴寺等44座寺院的壁画,均出自各名家之手,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范长寿、吴道子等。壁画题材中最广泛的要算是净土经变的内容了。
总之,唐代长安城佛寺建筑的形制,影响了各地石窟壁画的内容,也同样在新疆安西时期的壁画中得到反映。
*作者简介:贾应逸,新疆博物馆研究员。
① 《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
②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寺塔记》。
③ 《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4页。
④ 《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41—42页。
⑤ 《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08页。
⑥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74页。
⑦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
⑧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⑨ 《宋高僧传》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722页。
⑩ 《宋高僧传》卷第3;《十力经》序,《大正藏》第51卷。
(1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12) 慧超著《往五天竺国传》,参见《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5页。
(1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52页。
(14) 参见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5)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6—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