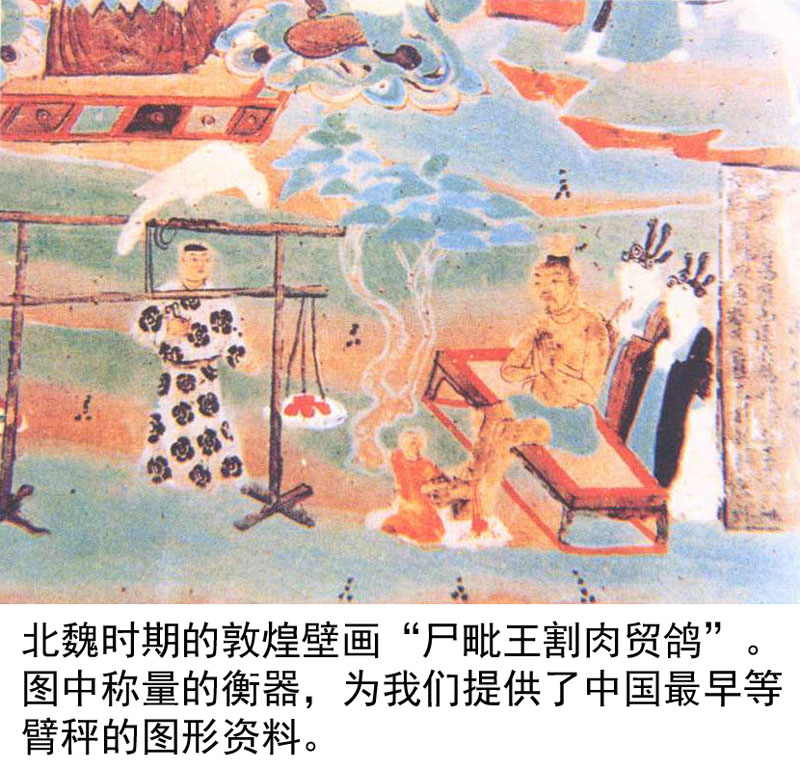唐代,随着佛教的深入民间和宗派的建立,出现了用讲经仪式、讲唱经文、着重敷演故事以吸引听众的「俗讲」。
俗讲时,依据讲经仪式,先有唱经题前的吟词,叫押座文;接着便有俗讲经文,即讲经文。讲经文由于故事性突出,后来便俗称为“变文”,或者称为变。这就是说,用通俗的语言,加上有韵的唱词话本,来宣讲佛经,便是俗讲,亦即后来的变文。变文与佛经变相(经变)互相配合,唱变文的人,为了使所讲佛经故事明白晓达,同时又把故事绘成画卷,张挂以配合说唱,这就是经变画。可以说,经变和变文,是俗讲的产物。
俗讲这种讲经形式,至少在初唐已经出现。唐《高僧传·善伏传》中,记载了贞观三年(629)常州义兴寺沙门善伏俗讲事:“窦刺史闻其(善伏)聪敏,追光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中,记载显庆元年(656)十二月五日:“其日,法师又重庆佛光王(唐中宗李显)满月,并进法服等,奏曰:辄敢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报恩经变一部。”这里,玄奘献给唐高宗的,是心经原本和报恩经变文。可见,贞观三年以前,已有佛经俗讲;显庆元年以前,已称俗讲经文为变文。
变相和变文这对亲兄弟,是佛教的产物。开始时只是严格地讲唱经文,有说有唱,在寺庙中由法师在高座上聚众宣讲。为了招徕听众,渐渐演变成不援引经文,只是讲唱佛经故事。甚至只沿袭变文讲唱对话的仪式,俗讲与佛经无关的中国固有的诗、词、传、记等文体,以铺叙故事取胜。从在寺院中讲唱,又流传到寺院以外的艺人。影响所及,深入民间,已非俗讲僧当初的原意了。到了宋代,僧人在“瓦子”中宣讲,有所谓“谈经”、“说诨”、“说参请”等出现。再后,便发展为宋金时的“宝卷”文学,可以说是唐代变文的嫡派子孙,中国俗文学史由此发端,演变成枝叶繁茂的民间文学,这是俗讲变文的贡献。
唐代寺院中俗讲,唐玄宗时已甚流行。《唐大诏令集》卷113载开元十九年(731)曾禁断俗讲:“近日僧尼,此风尤甚,因依讲说,眩惑闾阎……或出入州县……或巡历村乡,恣行教化”。
至长庆、太和、会昌以后,俗讲又盛。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淑等三人,以文淑最著名。唐赵《因话录》中记: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这种声音宛畅、说唱并举的俗讲,当然被没有多少文化的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便是佛教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变文这种文学体裁,因敦煌写经的发现而重见天日。除了阿弥陀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父母恩重经等佛经讲经文或变文外,也有采纳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而演义的《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变文。其中《降魔变文》,叙述舍利弗降伏六师故事,卷子背面绘有舍利弗与劳度叉斗圣的变相,每段图画与变文相应,这是经变与变文关系的最好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