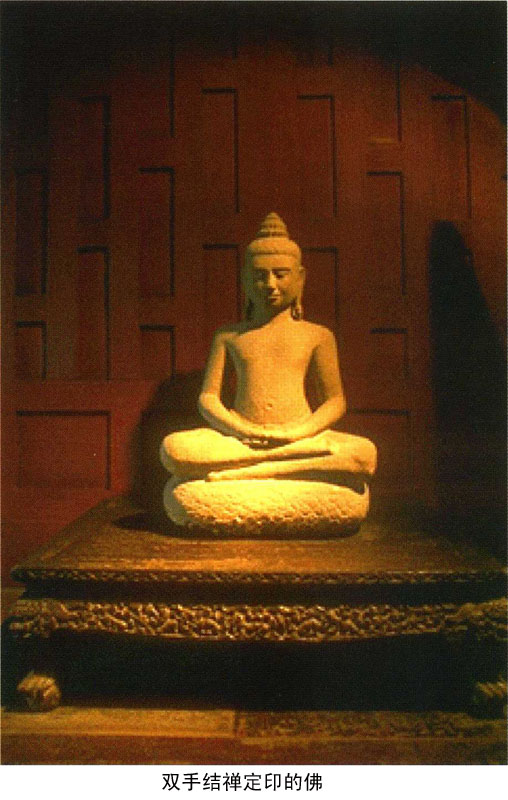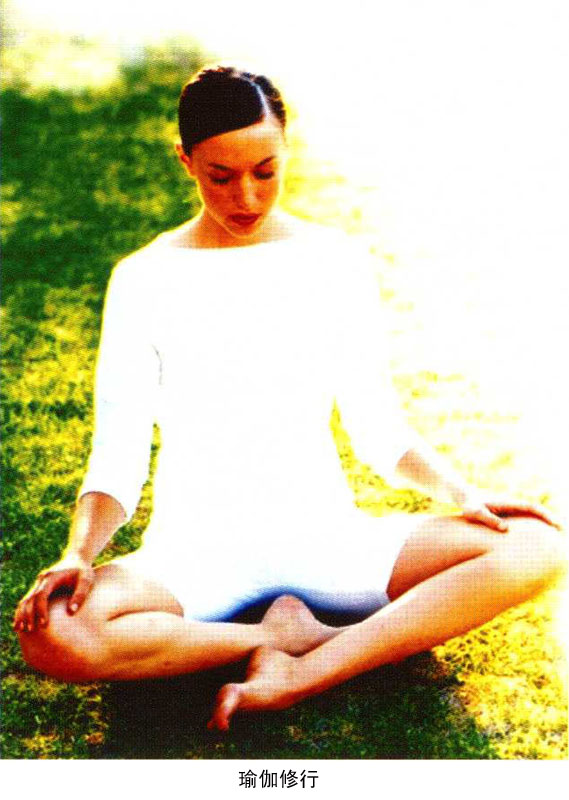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科学日新月异,渗透到各个领域。无论是对宏观世界或是微观世界的研究,都进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不管这两大类科学研究多广、多深、多细,始终是以人为主体展开的。
1.禅与大脑生理学
这里仅就人的脑而言,可分为:大脑、间脑、小脑、脑干四大部分,由左右两个大脑半球组成,两半球间有胼胝体等相连接。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其功能支配着人的一切感觉、思维、认识、记忆、言行、思想等一切精神活动。
大脑生理学实验表明,人的大脑只有左半球能够支配人用语言表达其思想意识,而大脑右半球则不能,只能控制行动、解决问题、记忆事情和产生情感。这样,右半球的非言语化思想就成为人格和能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换句话,人的大脑两个半球是以不同方式进行思维的,即左半球倾向于用语词进行逻辑思维,而右半球则倾向于以感觉形象直接思维。
由于左半球对语言和逻辑的思维功能大大地超过右半球,因此,人们往往忽视右半球的思维功能,习惯于使用左脑(即左半球)。然而应当看到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和难以按逻辑判断的思维,是左半球不能完成的,这时右半球却会发挥出特有的作用。对此,大脑生理学便提出了“右脑革命”的口号,主张积极发挥右脑的功能作用,使大脑两个半球合作互补,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健全大脑。
禅的修行方式重视“内省”(自证)思维方法,特别是南宗禅倡导的“不立文字”、“直截心源、“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法,体现出直觉、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在禅门公案中,凡是最初参禅悟道的学人(包括历代著名禅师未开悟之前),总是执迷不悟,原因在哪里?禅宗以“妄念”来解释,即执著于言语文学的分别意识和外在一切事物的空幻不实的假相,见不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本体心性),障碍了成佛的可能性。依大脑生理学解释,那些执迷不悟的学人习惯于左脑思维,即停留在言语表达和逻辑判断的功能上,忽视右脑的功能作用。如禅门公案中许多学人常向禅师提出“什么是佛性?”,这种提问就是从言语表达和逻辑判断出发的,即左脑思维。禅师回答:或“干屎撅”、或“庭前柏树子”、或“麻三斤”、或“镇州大萝卜”,等等,学人习惯于用左脑,对这些答非所问貌似“瞎扯”、“疯话”的答语,犹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莫名其妙。如果学人即刻用右脑思维,瞬间便会明白禅师答语中的用意,即在截断左脑的分别意识和逻辑判断,提醒学人立刻转换为右脑的直觉、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思维去参究。
2.禅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规律的科学,最初只是在哲学内部发展,19世纪中期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和实验方法的采用,德国冯特(Wilhelm Wandt,1832~1920)首创内省实验方法,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开创者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提出了“意识流”的概念,认为:内省是运用自然的才能,也就是说抓住一刹那间的生命过程和把自然背景中发生的转瞬即逝的事物固定下来,报告出来。即由机敏而聪明的观察者把印象很快而可靠地捕捉起来。
以德国韦特墨(Max Wertheimer,1880~1943)、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苛勒(Walfgang Kohler,1887~1967)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认为通过“完形”(整体),使人在引起顿悟之前能看到问题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启发人类的创造性思维。
奥地利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使现代心理学进入了新的转折。他早期对人的精神活动分为:“意识”、“无意识”、“前意识”,后来他作了修订,提出了“本我”(盲目的欲望满足的本能)、“自我”(现实化了的本能)、“超我”(道德化了的本能)。他认为“意识”只是整个人格的外表,而“无意识”则潜藏巨大的能量,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是先天的性行动本能(生与死的本能)。因此,人们会引起各种“焦虑”,或因害怕客观世界的真正危险而引起的“客观焦虑”,或因表现行动的欲望受到惩罚而害怕的“神经病焦虑”,或因对良知的畏惧而引起的“道德焦虑”。他认为“自我”是防御“焦虑”的调剂机制。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创立了分析心理学,他用“精神”(psyche)来指“心”,认为“心”有三个层次:“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意识”的中心是“自我”,包含知觉、记忆,等等。它同“无意识”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个人无意识”属于个体,在它的下层是“集体无意识”,属于“精神”,也包括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各代积累的经验的影响。他把“集体无意识”的先天倾向称为“原始意象”(Archetype,或译为“原型”),认为这是被体验为情绪和心理意象。进而他又提出了“人格发展”说,即用“自我实现”来表示人格各方面的和谐、充实和完整,也就是自我的最完满的发展。
荣格虽然没有弗洛伊德的名气大,但他却与上面所说的心理学不同,即那些心理学家并未直接或间接触及过禅佛教,只有“内省”、“顿悟”、“无意识”等,与禅宗修行思想有相近之处,但内涵不相同。而荣格则对禅有所研究,他曾写过《瑜伽·禅和易经》等论著,并认为“无意识”所潜藏的巨大能量,来自人的内心本性,最终可以实现人格发展的自我完善。同时,以“集体无意识”来说明禅的超感觉、心灵致动等特异现象的实在性。
美国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则重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同时,他对禅宗也作过比较研究。他在《禅与心理分析》文中说:“禅的目标是悟:当下直接体会真实而无情识的污染和知识的分化,明白了解自己与宇宙的关系……心理分析的目标,正如弗洛伊德所曾论述的一样,是使潜意识(即无意识)化为意识,是以自我(Ego)取代伊底(ld,即本我)。……禅的思想将可加深和扩大心理分析家的天地,帮助他在掌握真相方面求得一种更为彻底的概念,以之作为意识充分觉醒的究极目标。”
被称为“第三思潮”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反对精神分析学派把病态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也反对行为主义学派视人为物理、化学客体,他以人自己为中心,提出了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时,他发现“他一生中唯一最欣喜、最幸福、最完美的时刻”。后来,他把这种体验称为“高峰体验”,这种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刻,是“同启迪、顿悟、了然于心相伴随的高峰体验,这种启迪、顿悟和了然偶或甚至经常改变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参见《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也曾接触过禅佛教,他的“高峰体验”便是得益于南宗禅“顿悟”时的心境。
3.禅与医学
无论中国的医学还是西方的医学,都是各自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逐渐形成的。中国上古时期的《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为中国医学奠定了基础,构建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辨证施治的体系,总结出了“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疗”(汗、下、吐、和、清、温、补、消)等治疗方法。概言之,中国医学的两大显著特点是:一、整体观;二、辨证施治。西方医学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地、水、风、火”四大元素说和解剖。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了实验医学阶段,纠正了古希腊解剖学中的许多错误,并发现了肺循环和血液循环。后来显微镜的发明和运用,使人体细微构成的认识迈入了新的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有机体细胞构造、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促进了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物学的深入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现代医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药理学、分子遗传学、心身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等,以及电子、激光、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使西方现代医学向纵深发展。从总体上看,西方医学的两大显著特点是:一、分离观;二、物理、化学施治。
当代医学出现了中西互补、融通的趋势。人们已经看到纯科学的理性和逻辑认识,对许多特异的现象显得束手无策。反过来对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瑜伽、禅定、气功、特异功能等的极大关注。
近年来,欧美、日本等国的心身疗法专家热衷于研究以禅调剂身心的疗法,特别是对禅定的研究。对此,人们也许会提出疑问:不用任何药物疗治,只管参禅打坐真的能治病吗?在禅定的典籍中谈到禅定治病的不少,但较零碎,而隋代天台禅的创始者智顗在《摩诃止观》中却较为系统。
宗门中的“五戒”是制约僧侣们的道德规范,智顗禅师认为不严守“五戒”的人会犯各种疾病,他说:杀生会引起肝、目病;偷盗会致肝、鼻病;邪淫则生肾、耳病;妄语会发脾、舌病;饮酒易得心、口病。他认为人患病的症状很多,但必须找出其根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一种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便会出现以下四种病状:(1)“地”不调者,则肿结沉重,身体枯瘠;(2)“水”不调者,则痰阴胀满,食饮不消,腹病下泄;(3)“火”不调者,则生寒热,肢节皆痛,口气不和,大小便不通畅;(4)“风”不调者,则身体虚悬,战掉疼痛,肺闷胀急,呕逆气急。另一种原因是五藏不和:心主口,若心生病,便出现身体寒热及头痛口燥等;肺主鼻,若肺生病,便出现身体胀满,四肢烦疼,心闷鼻塞等症状;肝主眼,若肝生病,便出现多无喜心,忧愁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暗昏闷等症状;脾主舌,若脾生病,便出现身体而上,游风遍身,疴痒疼痛,饮食失味等症状;肾主耳,若肾生病,便出现喉堂塞,腹胀耳聋等症状。进而,他认为知道了病的根源后,就应寻求治病的方法,虽然方法很多,但最好是用“止观”来疗治。首先,是用“止”(定)来治病,即安心入定于病处,就能治病。(1)必须明白是支配因果报应的主宰;(2)止心守于“丹田”(即肚脐下一寸处);(3)止心足下,不管行住坐卧都应坚持;(4)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调适。因此,善修“止”法能治众病。其次,是用“观”(慧)法,观心想,以六种气治病:(1)“吹”气;(2)“呼”气;(3)“嘻”(唏)气;4)“呵”气;(5)“嘘”气;(6)“咽”气。“呵”治肝,“吹”治心,“嘘”治肺,“嘻”治肾,“咽”治脾,“吹”气去冷,“呼”气去热,“嘻”气去痛除风,“呵”气去烦,下气散痰,“嘘”气去胀满,“咽”气去劳乏。再次,观想运作有十二种调息方法,以此可治众病:(1)上息(观想气息从体内上升),可治沉重大病;(2)下息(观想气息下至足心),可治头部虚悬;(3)满息(观想气息遍行全身),可治枯瘠;(4)焦息(观想气息烧焦病灶),可治腹中胀满和身体肿胀;(5)增长息(观想气息的增益健身作用),可治“四大”不调;(6)减坏息(观想气息对病的破坏和散灭作用),可治病的恶化;(7)暖息(观想气息如暖流周遍全身),可治寒病;(8)冷息(观想气息如冷气周遍全身),可治热病;(9)冲息(观想气息如猛气冲击病灶),可治肿毒;(10)持息(观想气息持续不动),可治战动;(11)和息(观想气息协调平衡),可治“四大”不和;(12)补息(观想气息可滋补全身),可滋补“四大”不衰。明了以上的方法后,应用心于坐中治病,此具有十种方法:(1)信(坚信“止观”必能治病);(2)用(随时常用“止观”法);(3)勤(勤奋精进);(4)常住缘中(细心依法);(5)别病因法(如上所说);(6)方便(善巧成就,不失其宜);(7)久行(常习不废);(8)知取舍(取其有益,舍去有损);(9)持护(坚持维护);(10)识遮障(不要随便将“止观”中获得的体验和治病的效果告诉他人)。禅定有益于养生保健,但不能包治百病,有病者须求医服药,结合禅定亦可起到辅助作用。
4.禅与现代科学
心理分析学的开创者荣格在《现代人的心灵问题》一文中说:“当我们正用工业成就把东方人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际,东方人亦正以其精神成就把我们的精神世界弄得狼狈不堪。我们仍未想到,当我们从外面把东方人打败之际,也许东方人正从内部把我们包围住。”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又说:“现在,21世纪即将来临,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时代真的出现了。技术和人类潜能是今日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和遇……我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因此,向来以分析、综合的纯粹理性为其特征的西方科学,便把触角伸向东方以直觉、非理性的神秘文化中,形成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互补融通的现代科学大趋势。
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深化了理性思维,电脑和机器人的开发和运用,使人工智能进入了全新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和彭罗斯共同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为我们提供了宇宙源于何时的难题线索。如此等等,令人惊叹不已。不论形式逻辑或是数理逻辑等名理思维是何等的精细,却难于揭开不可言说的禅的奥秘。但现代科学并未因此而拒绝对禅的研究和运用。
从现代科学对禅的研究成果表明,禅已经被广泛运于心理学、医学、心灵学、行为科学、美学、文学、艺术、体育等中,而禅定更是作为西方精神分析疗法、自我暗示疗法、渐进松弛疗法、自律训练法、超觉静思法、形象控制疗法等的主要方法,并日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社会科学偏重于禅宗的历史和历代禅师的个案研究。其成果最突出的是日本,其次是中国。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则重于对禅定方法的运用,以及处于凝神时心身状态的量化分析。
心理学家马哈里希·约基对禅定凝神的研究发现在生理功能方面有一个持续的和重要的变化。在实验过程中,他通过脑电图所记录的脑电波反映出的脑电活动,证实当处于禅定凝神时脑电活动会转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这种状态与清醒、睡眠、做梦时的脑电活动不一样。即处于凝神状态人的氧的消耗量减少,血压、呼吸以及心率明显降低。正常人的心率为每分钟72次,凝神状态的人心率降至每分钟24次,呼吸率降至每分钟仅6次,氧的消耗量减少到只有通常的20%,心脏的输出量减少了30%,皮肤的电阻值却增加了400%,说明紧张与焦虑极大减少。(参见达阿尼·舒尔兹《心理学家应用》)
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他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或译为《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描述他自己曾在海滩上凝神冥想微观粒子的活动,突然顿悟,于是将现代物理学的新概念相对论、量子论等,与包括禅宗在内的东方神秘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以说明两者对宇宙图景的描绘有惊人的平行性,并归诸于禅思直觉的特殊认识途径。认为现代科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是人类精神互补的体现,只有两者互补融通,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之前,无意中翻阅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学著作,愈读愈使他心情不能平静,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正是我一向要在我的整个著述之中想要说的东西。”
从禅宗公案拈出个“无”字,不仅是历代禅师参究的“话头”,而且也是现代科学要解的题目。“无”既不是非存在的否定概念,也不是实际存在的肯定概念。日本禅学家柳山圣山概括为“无的哲学”。“无”没有质的规定性,又没有量的分析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想透过这一难关,现代科学任重而道远。
格式塔
是德文Gestalt的音译,意为“形式”、“形状”、“完型”,泛指任何一种被分离的整体。1912年,在德国创立了“格式塔心理学派”(又称“完形心理学派”),主张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所显示的结构性和整体性。代表人物之一的W.苛勒在《人猿的智慧》(1917)一书中提出了学习顿悟说。
焦虑
指个体担忧自己在工作、学习等中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而感到自尊心受到持续威胁所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且带有惧怕、自责、内疚等情绪状态。心理学认为焦虑有三种:(1)客观性和现实性焦虑;(2)神经过敏性焦虑;(3)道德性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