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研究论著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
谈策释錣
党士学
内容提要 策是古代驱马赶车的工具,从器名可知是用竹制成。古人常讲,策端有錣,以刺马不前也。但因过去仅在汉代画像上看到其形象,未见过实物,便不知策的具体形制,也不能理解策何以刺马。秦陵铜车马的铜策逼真地再现了古代马策的结构,为认识和研究策的形制和用法提供了前提保障。本文以铜策为物证,结合历史文献,谈策释錣,考证器名,探索源流,讨论用法,梳理演变。
关键词 策 錣 名称 用法 演变 考释
策,是古代用于驱马赶车的工具,我们现在常用的“鞭策”一词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两周秦汉时期的马策一般用竹棍制成,这从“策”字的写法就能够看得出来。由于竹质的马策很难留存下来,因此,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当时的马策实物。不过,关于马策的图像资料,倒是常常出现在考古出土的汉代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的车马图像中。车马画像中的策,一般是用一根向斜上方伸出的直线表示,多数执于御者手中,也有的斜插在御者身前。非常宝贵的是,在秦始皇帝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有幸发现了3根保存完整的铜质马策。铜马策完全模拟秦代的竹质马策制作,逼真地再现了古代马策的实物形状,从而为我们认识和探讨古代马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根铜马策中的2根出土于秦陵一号车即铜立车,1根出土于二号车即铜安车。3根铜策均作竹棍形,下粗上细,直径0.8-0.5厘米,长度分别为81、75、74.6厘米[1]。策身从上到下间隔铸有6道形象逼真的竹节,其中下端握手处的竹节短密,呈现为竹子根部特有的形态;其余部分的竹节相对疏长,节长大约作等距分布。为了使铜铸的马策外观上更像真实的竹策,秦代工匠在塑形的基础上,还对铜策做了涂色和描绘修饰,以表现竹子的颜色和细部特征。具体方法是:先用与竹子颜色近似的浅绿色对铜策做通体涂刷,使铜策成竹绿色;然后在本已铸出的竹节处,再用白色细线沿凸起的节棱上下环勾两周,意在显示竹节部特有的白色勾痕;同时又于每段竹节的一个侧面,用蓝、白两色线条勾画出象征竹身凹槽的流云纹。经过如此一番绘饰打扮,竹子的颜色、竹节的特点和竹子的身型特征,全然被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图一)。
作为古代驱马赶车的策,仅是一根不加处理的竹棍显然不够完备,通常还要对竹棍做必要的加工改造。在秦陵铜车所配备的铜策上,我们看到古人对用作马策的竹棍做了两处改造:一是在竹棍的顶端插装有一根钉状短刺,短刺粗2毫米,长约9毫米。二是在策的握手部位上方,横贯有一根短棒,棒的两头露出少许成为格挡。策顶端之短刺用于击刺马体,促使马匹服从人的指令。握手上方的格挡则作为对人手的阻制,能保证御者在做击刺动作时,握策之手不致向前滑动。
需要说明的是,随同两乘铜车马出土的3根铜策中,有2根铜策的顶端装有钉刺,另外1根与一号铜车伴出的铜策,其顶端却是无刺的齐头。这一现象表明,古代至少是秦时,赶车驱马的策有顶端装刺型和顶部无刺型两种类型。
策为形意字,上从竹,下从朿。《说文·竹部》:“竹,象形,凡竹之属皆从竹。”《说文·朿部》:“朿,木芒也,象形。”段玉裁注:“芒者,艸耑也。引申为凡尖锐之称,今俗用锋。铓字,古字作芒。朿,今字作刺。刺行而朿废矣。”策,是古人专为赶车驱马之器具命名所创设的器名字,本意是指竹质有尖锋之器械。策字的上半从竹,表明策是用竹棍制作;而下边从朿,自然表示策端的尖锋是以棘朿为之。《楚辞·九章·悲回风》有“施黄棘之枉策”句,王逸注:“施黄棘之刺,以为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虽然后来洪兴祖认为黄棘是地名,指楚怀王与秦昭王的黄棘之盟。但文中“黄棘”与动词“施”连文,如依王注,这句话则不好读通。故孙诒让《礼造》卷一二否定其说,并认为黄棘即《仪礼·士丧礼》所称的“王棘”。郑玄注以为王棘“善理坚刃”,故可用以为策。王棘乃棘朿,属木芒也。由此证明,早期的策的确曾以棘朿为尖锋。可能是因为朿做的策尖易折不耐用,所以后来古人又以金属针取而代之。通过对策字的解析,可推断出顶端有刺之策应当是古策的本形。
策端之钉刺古称錣。《列子·说符》记载:“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张湛注:“錣,杖末锋。”“马策端有利锋,所以刺不前也。”《淮南子·道应训》中节选了“白公胜虑乱”一段,句后高诱注曰:“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錣。倒杖策,故錣贯颐也。”许慎注也说;“錣,马策端有利针,所以刺不前也。”《韩非子·喻老篇》则作:“白公胜倒杖策而锐贯颐。”改錣为锐,字义相同。《淮南子》还有多处讲到策、錣的话句,如《原道训》:“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錣,不能与之争先。”王念先案:“錣为策末之箴,所以刺马者也,故劲策与利錣连文。”《修务训》:“良马不待策錣而行。”许慎注:“錣,策端有针也。”《氾论训》:“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韩非子·外储说右篇》亦有云:“延陵卓子乘苍龙与翟文之乘,前则有错饰,后则有利錣,进则引之,逻则策之。”古代还将驱羊车的顶端有锋之竹棍称为笍。《说文·竹部》:“笍,羊车驱箠也。箸箴其端,长半分。”段注:“笍,羊车箠也,端有鐵(鐵当是鍼)。按:驱即御,驱箠者,御马之箠也。箴当作针。所谓端有铁,可以卹勿而椓刺之。善饰之车驾之以犊,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箴刺而促之。”[2]《玉篇》:“笍或作錣。”以许慎《说文》和段玉裁对笍的解释,驱羊车之笍和马策实际是同一种器物,可能是因为使用对象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称谓。众多历史文献在提到策时通常是策錣连文,古人注释也大多讲到策端有錣,这说明顶端有刺之策是古策的常规形制,是秦汉及以前时代普遍使用的赶车驱马器具。秦陵两乘铜车者配备顶端有錣之策便是证明。
铜车马之策出土前,由于人们没有见过古策的具体形制,多以为策就是一根竹棍,加之后世人长期受挥鞭抽打驱马方式的影响,因此,虽然古文献中常有以策錣刺马之说,可今人对文献的解释并不完全理解,继而造成对古代马策用法的认识模糊不清。在铜马策面世后,我们有幸看到了古策的真面目,此时,再对照文献进行分析,头脑中关于策的用法豁然呈现。由此我们知道,古代马策通常是顶端装有钉刺的竹棍,御者赶车驱马时,不是挥动马策去抽打马,而是用马策顶端的尖刺击刺马体,正如古人所说的“马策端有利针,所以刺不前也”。御者手握马策以錣刺马时,手臂动作是平举向前用力,当策錣击刺到马体的瞬间,反作用力会使策产生回弹。为了防止马策回弹时在人手中滑动,古人便在策的握手上方横贯一根短棒,以两翼长出之棒头作为格挡。由于策的顶端装有利錣,所以驱马时不能采用抽击的方式,否则,很容易对马匹造成伤害。这是因为,人在做刺击动作时,力度和向前送策的距离很好掌握,能够做到“点到为止”。而人在以策抽打马匹时,手臂是上下挥动,用力的大小就不好把握。用力轻了,起不到效果;用力重了,策顶之錣极易将马体划伤。反过来讲,以无錣策驱马,只能采用抽打方式,不能用来击刺。因策顶无利錣,刺击犹如搔痒,对马匹没有威慑作用。
马策顶端是否有錣,不仅决定了策的使用方式,还决定了策的长度。就立乘车而言,用有錣之策赶车驱马时,策的长度以车上御者握住马策伸直手臂后,策的前端能够触击到马的臀部为宜。也就是说,马策的长度加上人手臀的长度,应大体等于或略长于车上御者肩部到驾马臀部的距离。策既不能短,也不可过长。策短了,则不足以刺到马臀;策过长,不仅会给御者使用带来不便,还容易造成策身的折断。
具体到两乘铜车马,由于车的形制一乘是立车一乘是安车,我们上面所说的用策长度原只适用于立车,在安车上则不能套用。从两乘车中御者肩部到驾马臀部的距离看,铜立车的御者立于车上轼后,肩部距驾马的距离略远;铜安车的御者跽坐在为御者专设的座位上,肩部距驾马较近。如果以御者与驾马之间的距离计算,立车所用的马策似乎应比安车的马策略长一些。但秦陵铜立车配备的有錣策长75厘米,铜安车配备的有錣策长74.6厘米,两策的长度却大体相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立车的御者以站立姿势御车,策马时手臂能够完全伸展,臂长得以充分利用。因此,尽管所用马策不是很长,但能够做到以錣刺马便足矣;而安车的御者以跽坐的姿势御车,座位和身姿都较低,人的肩部仅与马臀的高度相当。御者策马时必须抬肘弯臂,臂长得不到利用。因此,安车所用马策的长度,自然不能和立车的用策长度类比,要求马策相对略长一些才通用。由此可见,尽管两乘铜车中御者和驾马之间的距离不同,但由于车的形制和御者用策姿势的区别,长度大致相同的马策分别用在两乘车上仍然是适当的。
如果赶车时使用无錣马策,御者则须采取挥策抽打的方式,这就要求挥出之策的长度至少应超过马臀部20厘米以上,否则,策梢就无法抽击到马体。也就是说,驾驭同一辆马车,如果分别使用有錣策和无錣策,那么,无錣策的长度应当比有錣策更长一些。秦陵铜立车所配备的两根不同类型的铜策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有錣策长75厘米,无錣策长81厘米,两者相差6厘米。因为秦陵铜车是真车的二分之一大小,以放大一倍计算其当时实物,无錣策比有錣策长了12厘米。考虑到古人在选用有錣策时定会对其长度留出有少量的富裕,因此,铜立车所配备的无錣策长度应当是秦代车上用策情况的真实反映。
前面在讨论用策的长短问题时,是根据铜策的实际长度并结合铜车马的情况进行的。但铜策的长度却不是古代马策实物的原本尺寸,谈论古代马策更不能用铜策的实际尺寸作策长的标准。铜车马是按照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比例缩小制作的,车马人的大小尺寸均是实物的一半。因此,铜策的长度也只是实物马策的二分之一。现在看到的有錣铜策身长75厘米左右,与教鞭的长短相当,使用起来似乎相当顺手,易于操纵。可实际并非如此。古代实物马策的长度要以铜策的长度尺寸为基础放大一倍,实际策长会达到150厘米。操纵如此长度的竹策刺马,对御车人、尤其对坐在如铜安车一样低矮座位上的御者来说,着实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笔者讲课时,有人在听完白公胜倒杖策被策端之錣刺破脸部的故事后,提出铜策如此长短,树立起来仅及人的腰部,倒拄策,如何会刺破脸面?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客观存在的铜策在头脑中形成的印记很深,感性认知影响了应有的理性思维。铜策是不够长,但它是缩小了的明器,用作比照的只能是同样缩小制作的铜车马及车上的铜御者。如果还原为实际生活图景,实物策长达150厘米,树立起来,策端可及普通身高人的腮部。倒杖如此长度的马策,激动之时被策端之錣刺破脸部,便不足为怪。
策出现的时间应该和古人使用马车的早晚相当。作为早期策的常规形制,竹棍顶端装有钉刺的有錣策大体沿用了上千年。随着人们驯马经验的丰富和御车技能的提高,大约从战国时期起,策的形制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标志是出现了竹棍顶端没有钉刺的简化型策,随秦陵一号铜车出土的无錣铜策可作为实物例证。虽然无錣铜策是秦代之物,年代晚于战国,但它能够出现在皇帝乘舆中,说明这种策已经通过较长时间的实用考验,是一种成熟的赶车驱马用具。因此可知,无錣马策出现的时间必然在秦代之前。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有錣之策制作起来比较麻烦,古人在生活实践中随机应变地对策做了简化;也可能是受到胡人骑马所用鞭策的影响;抑或是从笞人所用之竹棍荆条中得到启发。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使用有錣马策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无錣马策在出现初期,并未对有錣马策的统治地位造成太大影响。从随同秦陵铜车出土的3根马策中只有1根是无錣马策看,秦代无錣马策的使用仍然不是很普遍,可能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拿出来使用。由于无錣马策不能以击刺的方式驱使马匹,只能用马策的末梢去抽击,从而导致马策的用法由原来的只能以錣刺马改变为刺击和抽打两种驱马方法同时存在。到了西汉时期,无錣马策的使用应当更趋广泛,这种认识的得出有汉代人对马策用法的描述作为旁证。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话句中以动词“振”来描写古人用策的动作。振者,挥动也。振动马策寓含抽打之意。用“振策”即准备抽打的动作来形容“御”的方式,足以说明在贾谊的思维中,策是用来抽打驱马器具。而能以抽打方式驱马的策,自然是顶端无錣的策。我们从贾谊“振长策”一词的潜意中,大致能够看到汉代无錣马策使用的广泛程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马车数量的增多和用车的普及,人们在用策的材质方面开始变得随意,出现了以木棍代替竹策的现象。汉代文献讲到驱马器具时,常以马棰、马*(左木右过)称之,这种称谓的出现绝非偶然。古代器名用字多与制作的材质有关,棰、*(左木右过)皆从木,应是当时人使用了木质马策后才会产生的别称。然而,无论马策的形制和材质有何改变,人们用策赶车驱马的习惯直到东汉末期还在延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墓葬壁画上面的车马图像。在为数众多的车马图案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表示马策形象的一根直线,这根直线既直观又生动地反映了东汉时代马策的使用情况(图二、三)。
在古代,策用于驱马御车,鞭则主要用于殴人。《尚书·舜典》:“鞭作官刑。”《左传·襄公十四年》:“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左传·哀公十四年》:“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周礼·条狼氏》:“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郑玄注:“趋辟,趋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车之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孙诒让疏:“鞭所以威人众,有不辟者,则以鞭殴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曰:“操鞭使人,则役万夫”;“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鹜矣”。句文将鞭与策对举,二者用途的区别更是一目了然。经典所记,鞭为殴人之物,且多是用于执法,罕用做驱马。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的“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也应是以鞭修饰行文而已,并非实际以鞭驱马。
古人之所以将驱马之器具称作策,正是因为它是一根顶端有钉刺的竹棍。然而《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和秦陵铜车马陈列说明中,却将顶端有刺的策称作錣[3]。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的称谓,缘于《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在讨论马策时对相关文献的误读和误解。《报告》将《列子·说符》“白公胜虑乱”一段话和许慎、张湛等人关于策、錣关系的清晰表述置之一旁而不顾,仅以《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文作为证据,并且把注文错断为:“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錣,倒杖策故錣贯颐也。”据此认为,前端有钉状锋的策不应称作策,而应称作錣。如果按《报告》的断句去读这句注释,确实能误导人产生端部有针的马捶名曰錣的错觉。然而,《淮南子·道应训》正文和《列子·说符》所记“白公胜虑乱”的语句相同,该段话很明白地说白公胜手持的是策,由于倒杖策,策端的錣才刺破了自己的面部。如果前端有钉状锋的策称作錣,如何要讲“倒杖策”呢?并且张湛注文明确地说,錣是杖末锋,又进一步讲“马策端有利锋,所以刺不前也”。许慎在注释策时也讲了同样的话。可见錣只是指策顶端的利锋(针),不是策(或称杖)本身的名称。高诱注文的正确断句是:“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錣。倒杖策,故錣贯颐也。”其实是说策(马捶)顶端的针谓之錣,由于白公胜将策倒杖,所以被其顶端的针(錣)刺破了脸面。话语中并无《报告》所认为的“顶端有钉状锋的策应称作錣”之意。通过本文的考释和讨论,足以证明《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将铜车马中出土的有錣铜策定名为錣是错误的。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于早前有关铜车马的研讨文章中纠正过[4],但秦陵铜车马陈列在已有正确认识的情况下,仍在器物说明中将铜策标识为錣,这种错误不应继续存在。
注释
[1]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第102页、22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段玉裁注:“笍,羊车箠也,端有鐵。”其说应是受《说文·金部》注文“羊箠也,端有鐵”的影响。《广韵·十五錧》錣字下亦有:“策端有鐵。”说笍或策端有铁,其语义不明,很难理解。《淮南子》许慎注则多言策端有“鍼”,针以刺马。知“鐵”应为“鍼”,“端有鐵”当是“端有鍼”。鐵、鍼二字形近,容易写混,写鍼作鐵,属笔下之误也。段氏不疑“端有鐵”之“鐵”为笔误,因而才有对“端有鐵”的进一步解释。又段玉裁按:“善饰之车驾之以犊,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箴刺而促之。”《释名·释车》说羊车是“善饰之车”,故段氏从之,用以释驱羊车之笍。对段氏“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箴刺而促之”之说,孙机先生在《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一文中提出质疑,认为:“刺即錣本来就装在策上,不挥策何以用箴促马?”其实段氏所言并不错误,问题出在孙先生只读了上半句而未理会下半句。所谓“驰骤不挥鞭策”,是因为策端有錣,驱马时须以錣刺马,刺击的动作是手臂向前用力,不是上下挥动抽打,故言不挥策。也正是由于古人不以挥策抽打的方式驱马,而以策端之錣刺击,所以段氏才说“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箴刺而促之”。
[3]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第36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铜车马陈列室铜策展柜说明牌标识作“铜錣”。
[4]党士学:《秦陵铜车马相关问题再探》,《秦文化论丛》第13辑第279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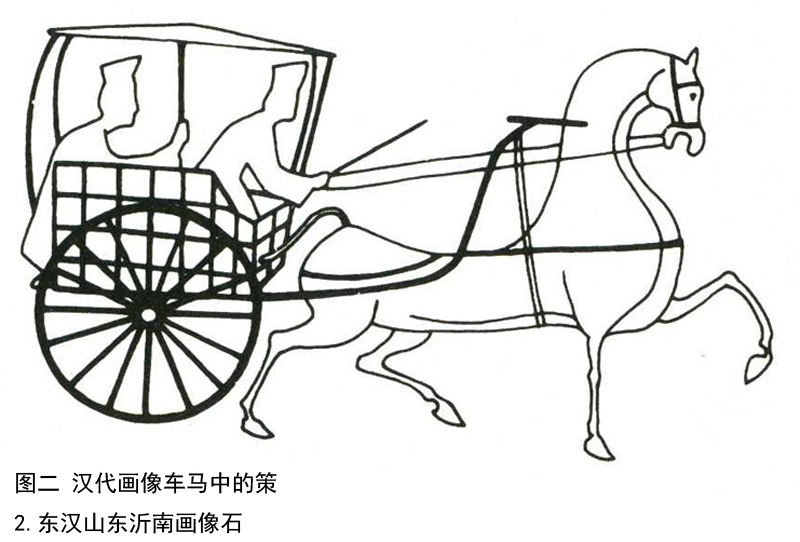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