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秦俑坑发现的“木箱”
刘占成
按语: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当年,作者对秦俑一号坑发现的无盖木箱遗迹引起很大关注,面对遗迹无解的时候,笔者联想到了在农村饲养室喂牛的槽具,于是就写了这篇论文,提出这些“木箱”遗迹很可能是象征养马的“马槽”。这一论点虽然还值得商榷,但作为对考古发现的遗迹现象的一种解释,也可备一说。希望由此引起大家的注意。
《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公诸于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秦俑坑翔实、直观的实物资料,为人们研究秦代军事、艺术乃至秦文化提供了方便的钥匙。事实上,秦俑坑除出土数量众多的兵马俑和大量的实战青铜兵器之外,还曾发现数处“木箱”遗迹。本文想对这些“木箱”遗迹,提出一点浅见和解释,或许对研究秦代马政及相关问题能起到引玉之效,恳请方家赐教。
“木箱”分布及规格
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在第三过洞一号车(报告称二号车)车舆后有一木箱朽迹,箱内外髹褐色漆,无盖。箱内没有任何遗物,板厚约3厘米,作用不明。在第七过洞一号车后(报告称四号车)发现47厘米×60厘米的褐色漆片,漆下有一层厚0.25厘米的板灰。此亦似为“木箱”的残迹。在后来的发掘中,又相继于第六过洞、第十过洞中发现了“木箱”遗迹三处。第六过洞一号车东侧的“木箱”,发现时,大片的漆皮分上、下两层叠压;二号车的木箱遗迹也是木质已朽,仅余漆皮。第十过洞的木箱遗迹有一部分压在第九隔墙坍塌土之下,位置可能为后期扰动,现距其前第四号车约6.3米。从清理出的残留漆皮看,木箱的底板、侧板等迹象也比较清楚。木箱漆皮均为褐红色。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相信诸如此类的“木箱”遗迹还会有所发现。
从实测数据可知,木箱规格为长方形,尺寸不一。第三过洞一号车后的木箱长86厘米、宽58.5厘米、高约30厘米。第六过洞的木箱一个长84厘米、宽17厘米、高16厘米;一个长93.5厘米、宽45厘米、高25厘米。第十过洞的木箱长100厘米、宽58厘米、高25厘米。
由以上兵马俑坑中“木箱”的分布与规格尺寸,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木箱与车马伴出,二是木箱无盖,三是木箱长宽大于高度。这三点对我们探讨木箱的用途、定名及相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木箱”用途及相关问题
秦俑是写实作品,已得到公认。那么,俑坑内发现的“木箱”,象征着什么含义呢?它代表着什么东西呢?我们依前节所述三点,再结合古时征战中的后勤供应情况,对这些木箱的作用、定名等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古代战争,军旅以备三日之粮作为后勤供应的一个基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孙膑兵法·延气》:“令军人人为三日粮”。《荀子·议兵篇》:“赢三日之粮”。曹操对《孙子兵法·作战篇》注文有“……言万骑之重车,驾四马,率三万军、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装,厩二人主养马……”云云。可见,人要吃粮,马要吃草,军事行动的成败,后勤供应也是一个兵家非常重视的重要条件和内容。
马不但要吃草,而且草中需搅拌饲料。《淮南子·氾论训》说:“秦之时……入刍槀,头会箕赋,输于少府。”讲的就是国家收纳饲料税。《云梦秦简·田律》:“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槀,相输度,可殴(也)”。刍是饲草,槀是禾秆,均为马牛等牲口的草料。熊铁基先生指出:秦时“马牛的饲料像人发口粮一样,是按月给发放的”①。“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旨致者,皆止,勿禀,致。……田律”。“官长及更以公车牛禀其月食及公牛乘马之禀,可殴(也)……司空”。这些也正是秦简中所记载关于领发马牛饲料的具体规定。在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的陶盘下,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喂马的饲料谷子和干草。②并在马厩坑发现了专职负责饲马的跽坐俑。到了汉代,情况亦如此,《居延汉简》中就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记载:给战马除供麦粟及稷这些精饲料外,一天十匹马还要喂十五至二十束干草。平均是按一天一匹马一束半到两束干草的比例来发给的。③
马既然要吃草,那么,就必须要有盛食料的器具。秦陵马厩坑出土的喂马食具是分槽单养的陶盆。本文认为,秦俑坑发现的称之为“木箱”的东西,应就是秦时用于搅拌草料喂马的木质马槽。同秦俑写实主义这一主题相适应,当时人们也没有忽略驾车战马带上食具这一环节。木箱多出土于战车之后,似说明马槽的携带,是在车后某一部位悬挂着的。木箱无盖,长宽大于高度,也恰具备马槽的特征。同现代马槽比较,形制上只是前者口底尺寸一致,后者口大底小而已,后者无疑是前者的发展和演变。
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马槽,本不是十分讲究,但俑坑内的“木箱”为何涂以漆皮呢?这一问题是否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考虑:一是纵观兵马俑坑几千件兵俑、陶马,均涂漆施彩,兵器木柄、箭杆也漆染上色,连战车也是着漆彩绘。为之相统一,小小马槽,以漆施色,也为易事,在情理之中。二是在现实生活中,马槽本来就涂色上漆,或许是为了节省水草而专门涂漆。
查文献资料,鲜见战车出征带马槽的记录,秦俑坑马槽的发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另外,仅秦俑一号坑就出土战车四十余乘,说明秦代战车仍占十分重要之地位;而车战是离不开马的,马的喂养调理,关系马的体质好坏,也直接影响到车战的胜负,驾乘身健体壮的良马,正是车战取胜的前提和条件。秦俑坑的战马,从外形观察,腹和臂部圆而丰富,双肩宽厚,体魄匀称、雄健,仰首嘶鸣,跃跃欲驰,实乃秦军良马之再现。俑坑中战车马槽的出土,正反映了秦人对战马的管理和喂养之高度重视。也从一个侧面让人窥视到,秦国已设有专门喂养训练军马的机构。
秦代马政
考秦代马政,史书记载不详,但从《史记·秦本纪》记载来看,秦人的祖先非子曾以善于养马而为周孝王主马汧渭之间,便说明秦人有善于养马的传统。战国时,秦国已成为“车千乘、骑万匹”的车骑大国,而且“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④。足见秦代马政事业之发展。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厩苑律》和《厩律》等律名,也说明了秦国已设有专门养马的机构。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有“中厩”“左厩”“宫厩”“大厩”等陶文,为研究秦代养马行政机构,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陶文中“大厩”“中厩”“宫厩”又恰与《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一致,确证了其为秦代设立的养马机构。
熊铁基先生在他的专著《秦汉军事制度史》第七章“军马”一节中,根据秦简《效率》的“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的条文记载,明确指出:秦代“显然是有牧养军马的苑囿”,“有主管官员所谓县司马或司马令史,以及丞、佐、掾等等”。当然,军马除过喂养外,还要经常进行训练、考核、评比等,即“到军课之”⑤。由此可知,秦人重视养马,发展养马业,主要是从军事需要出发。《左传》成公十六年“蒐乘补卒,秣马厉兵”讲的也是养马为军事战争服务。军马平时养于苑囿或马厩,战时在外用马槽喂养,保证了马匹的充沛精力。秦国后来能腾飞为“车千乘、骑万匹”的车骑大国,能“内平六国,北却强胡”,能威慑六国,统一海内,其中,战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郭兴文同志通过对秦代马政立法的研究,指出“《秦律》对马匹死亡注销户口及赔偿处理办法作了严明规定”,“《秦律》对马的保护使用也作了一些规定”,“《秦律》规定了牧养马牛的评比办法及赏罚制度”,“《秦律》对养马的器物管理也有具体规定”,从而总结出了秦代马政立法细而严的特点。⑥我们从秦俑坑发现的“马槽”,研究秦代马政以及养马业的发展,乃至对秦国为何取得统一中国的胜利,都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①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第八章:给养),第277页。
②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③[日]森鹿三:《论居延简所见的马》,载《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第96页。
④《史记·张仪列传》。
⑤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第七章:军马),第246页。
⑥郭兴文:《秦代马政考略》,载《陕西省考古年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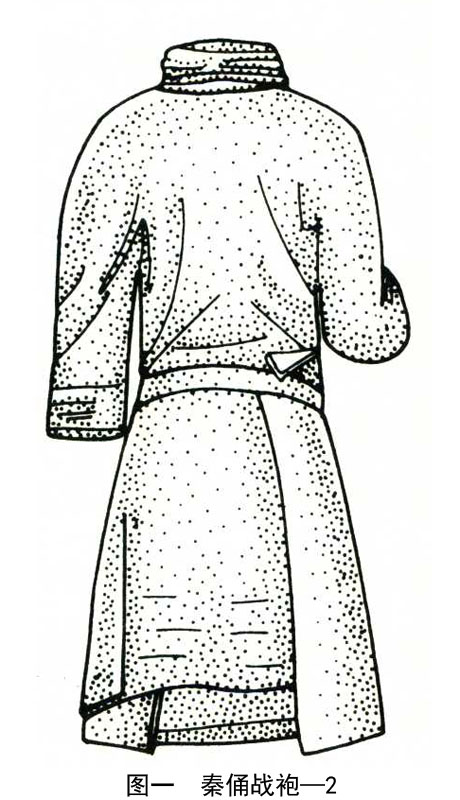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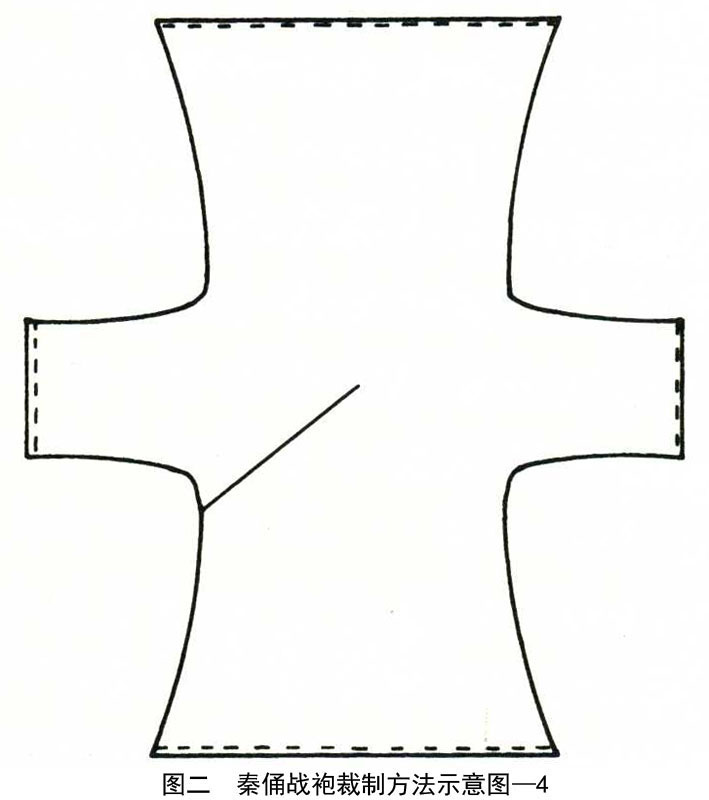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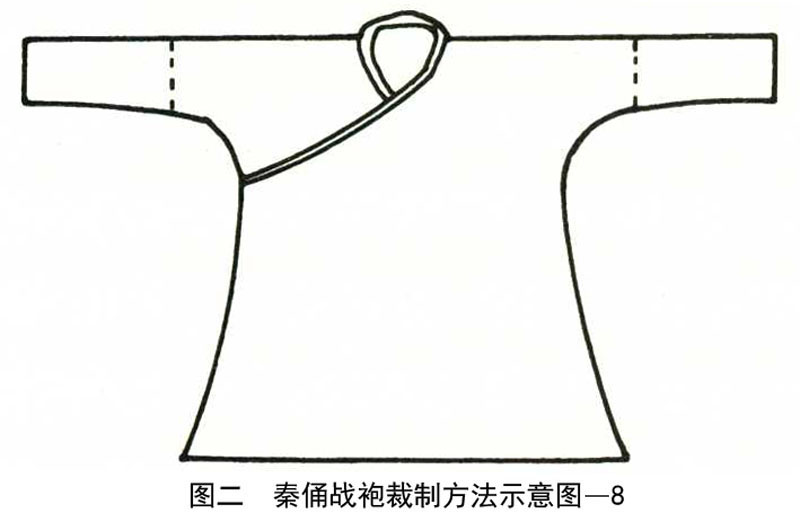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