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了个于阗画派
作者:王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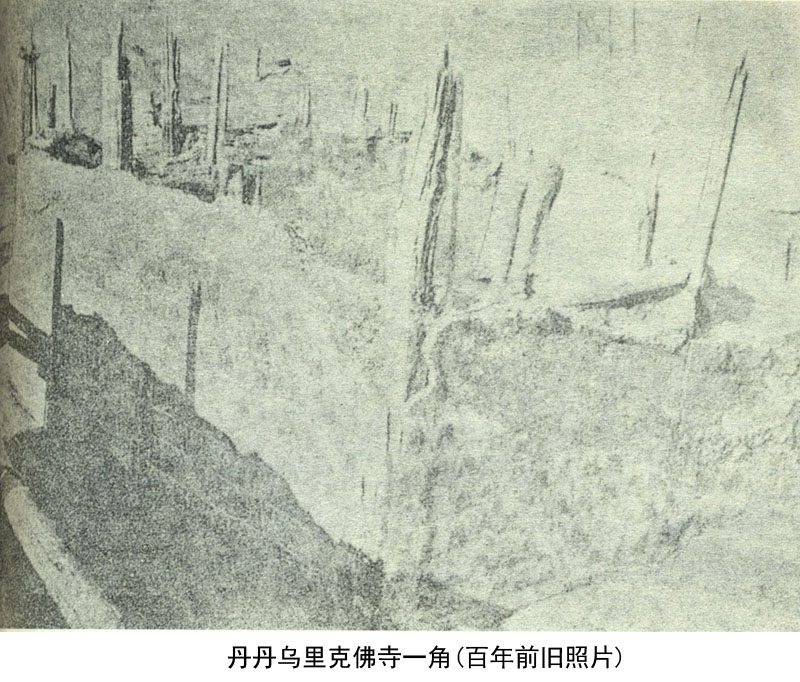
6
西域出了个于阗画派
隋唐时代,于阗的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达到高度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集多种外来艺术形式于一身,使于阗画家和作品形成自己的风格流派而著称于世。从上述丹丹乌里克出土四幅绘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兼收并蓄,中西合璧的特征。
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壁画和木板画等艺术品,是大约七世纪至八世纪之物,当时于阗画派的卓越代表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早已饮誉中原画坛。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论述于阗画派时说:“……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绘画证明这些作品在类型、源头、时代和主题上是异质的,于阗画派证明它已经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甚至还可能有花剌子模的影响,它们都曾被吸收,又被用无可争辩的创造力加以重新改造。”他还认为,丹丹乌里克等处遗址的于阗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图案等是从古犍陀罗之源衍变而来,一种强大的犍陀罗影响曾在于阗等地区起过作用,但并不否认这些艺术品是经于阗艺术家使用“真正的创造力,重新做成的”。丹丹乌里克《波斯菩萨》体形被特意拉长,黑色的络腮胡、四只手臂、绿色紧身束腰长衣、晕圈、光轮、王冠、短剑及其它附属物等,这种画面正是于阗绘画与外来画风巧妙结合的实证。在同一木板反面带有密宗色彩的神像,与波斯菩萨虽然可能有宗教意义上的象征性联系,但它们在风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分别显示出波斯式和印度式的不同特征。在被称为《传丝公主》的木板画上,中原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从主要人物的刻画、景物设置到叙事性的画面氖围,都表现出中国特色。但在《传丝公主》旁边的四臂神像身上,则透露出浓厚的印度风格。
由于于阗画派这种中西合璧的兼容性特点,印度学者B·N·普里在他的《中亚佛教》一书中将其称作“复合型的和田派”,他认为于阗画派是在吸收各种外来成分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改造的结果,好像该派的原生形态不是这样”。融合外来文化而使本土文化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风格,这是一种地域和民族文化成熟的表现。例如丹丹乌里克木板《龙女图》(或称《吉祥天女》),这幅杰作就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龙女优美的裸体,富于节奏韵律的“三道弯”姿势及小巧的装饰品,体现出古印度通常的造型手法和印度笈多派艺术风格。造像中男女比例的失调即女大男小的形式,是犍陀罗艺术观念的体现。刚柔兼济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线描手法以及龙女眉眼的画法,面带羞怯的表情和以手遮乳的姿态,则是中原绘画技巧和传统观念的写照。
丹丹乌里克板绘三头魔王(即阎文儒先生所称大自在天)的出现,还透露出印度密宗佛教进入于阗的信息。虽然早于公元五世纪于阗就出现过具有密教特色的经典,喻示了密宗的神秘苗头。但公元七八世纪是印度密宗佛教盛行的时期,丹丹乌里克和处于同一时代的附近寺院里大自在天、鬼母子图、大日如来、象头神像等密宗神像的连续出现,则说明印度密宗佛教已经传入于阗。
印度佛教及密宗的传入,激发了于阗画家的创作欲望,中原和西方的文化冲击又给于阗艺术家增添了艺术的灵感。在于阗这一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许多不留名的艺术家每天都以新奇的目光迎接着南来北往的人群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不断变换和补充着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在选择和融合的漫长过程中,中原文化以及印度、波斯、犍陀罗等文化因素并存于于阗文化中,所以外国一些学者把于阗文化及美术称作折中艺术、混合文化、复合型于阗画派。丹丹乌里克的大多数美术品,还仅限于匠人画的水平,只有少数能代表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仅管如此,这些绘画仍呈现出各种外来因素的成分和多样化的风格。由于当时社会和艺术结构的多元化,于阗美术的主题及风格都受制于外部因素,需要不断地舍取。不过,“不管它们受惠于这种或那种外来成分,但是于阗创作的画在特征上总是有着高度的创造性,并且表明该派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的结论是中肯的,应该说是没有贯常的西方偏见的。中西合璧的兼容性是丹丹乌里克甚至整个于阗绘画的特征,但在历史长河中这一特征仍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止。这种兼收并蓄的过程,必然引发于阗画家的创造精神。创立独具特色、自成一派的于阗画派,才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
西域古寺探秘/王嵘著.-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丹丹乌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