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被官府冤屈而死的汉长安商人——士奋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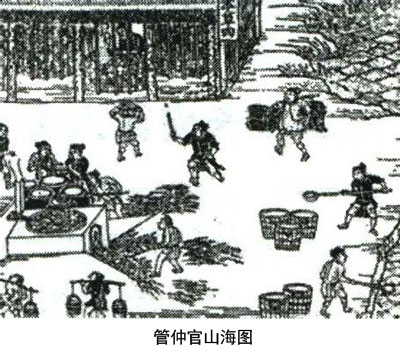
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常常是官府鱼肉的对象,就是家资千万,也常常逃脱不了官府的迫害。在东汉末年就发生过一场皇亲国戚压迫、迫害商人的千古冤案,这个商人就是长安士奋孙。
一、秦汉以来的官商关系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资源均为官方掌控,一切话语权也掌握在官方手中,中国的商人就成为与官方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商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其中主要有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和文化因素。
第一,传统社会中贯穿始终的“抑商”政策。中国是一个重农主义的国家,农业、农民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商周以降,中国历代都有商业发展的记载,在社会生活中,商业发挥着“通有无”的重要作用。但是为了保证小农经济这一国家命脉,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一直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商政策从整体上来看就是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对商业和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击。
从经济措施上,首先是“官营禁榷”制度,即: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有利可图,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管仲“官山海之利”;商鞅变法,继续实行“官山泽”政策。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出面经营一切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成为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制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秦汉以来,私人经营盐铁等重要物资,处以极刑,成为一种传统。其次是“重征商税”的办法,即所谓“寓禁于征”。早在商鞅变法时即定下“不农之征必多,有利之租必重”的国策。汉高祖刘邦对商人实行“重租税”打击。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商贾进行打击,“得民财以亿万计”,致使大批商人破产。汉代征收人头税,明定“贾人倍算”(对商人双倍征税)。自汉以后,历代王朝莫不重征商税。
从政治措施上,对商贾进行政治打击,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秦始皇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汉武帝“发七科调”(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经商者直接成为罪人,对商人与商业地位的界定算是到了一种极端的境地。很长时期,“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成为一种惯例,即是说商人作为社会最低层,不得改换门庭当官。这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对商人的服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中国古代服饰历来就有等级之分,而对商人更是严加限制。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律明定“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商人无论怎么富有,服饰上也不得逾制,“金银锦绣”商人虽然买得起却不准用,用就是违规。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传统的国家。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把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中国自战国以后即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官僚体制,“官”的地位崇高,几乎可以取得人们要追求的一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员的身份几乎可以满足一切,包括财富、荣耀、特权。这种一切向官看齐,以官为本的社会心态,也对商人与商业形成重大影响,不仅影响商业本身的发展,也影响人们对从业方式的选择和致富后出路的安排。
第三,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辨”与社会伦理中的商人地位。精神文化与伦理方面,义利之辨早已将商人界定为“小人”的地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追求物质财富的商人在身份上、伦理上甚至心理上,都成为君子的对立面。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商业及商人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的经常因素。战国以降,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在这样一种等级结构中,商人始终处于最低等的位置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的地位总体上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商人们除了经过艰苦努力,赢得财富而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地位并不能因财富的增长而有所提高。
这些就造成了商人每每被官府侵害的悲剧。
二、长安商人士奋孙的经营情况和被迫害过程
士奋孙的经营情况,《后汉书》“梁统列传”中有所记载:
“士孙奋字景卿,少为郡五官掾起家,得钱赀至一亿七千万,富闻京师也。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②
据资料可知,士奋孙是陕西扶风土著。其先祖士孙松(字世兰)是秦国扶风平陵(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其子士奋孙(字景卿)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万余,富闻京师,其子士孙瑞(?—195)字君荣(一说字君策),东汉末年大臣,士孙萌(字文始)之父。③
这士奋孙,原本是长安的一介富翁,先是经营商业,后来又兼营高利贷,发家致富,成为京师闻名的富户。也许是他太富有了,或是树大招风,被东汉末的皇亲梁冀紧紧地盯住了。这梁冀非同小可,他是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梁冀长相十分凶悍,说话口吃,读书甚少,仅能应付最简单的文字和筹算。他的姊妹中一人被顺帝立为皇后,另一位则被立为贵人。梁冀凭借外戚的特殊身份任大将军,历冲帝、质帝、桓帝四朝。顺帝死时,冲帝仍是一个婴儿,梁太后临朝听政,梁冀又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梁冀实际权力极大,在朝中也更加奢侈暴虐。冲帝死后,梁冀又立质帝。质帝自幼聪慧,对梁冀的骄横感受颇深。一次朝会群臣,质帝望着梁冀说:“这是一位跋扈将军!”梁冀听后怀恨在心,立即派人将质帝毒死。梁冀再立尚未成年的桓帝。他一手援立三帝,地位权倾朝纲。幼年的皇帝都不在他的话下,更何况一介商人。梁冀听说京师最有钱的富户是士孙奋,便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土孙奋非常富有,却又吝啬成性,一个铜板都能捏出汗来。他明知是梁冀设计勒索,但迫于淫威,不敢不借,借了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竟有如此不识抬举之人。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孙奋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严刑拷打,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这就是东汉末年一桩最有名的坑商冤案。这桩冤案被多种史籍记载,说明其冤情深重,影响深远。
三、士孙奋冤案的历史启示
汉长安商人士孙奋的冤案,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千古奇冤,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思索。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除了经商养家没有任何出路,就是经过艰辛经营,略有家资,也随时会成为官府侵吞的对象。这个士孙奋就是一介商人,兢兢业业的从事自己的商业经营,也没有任何劣迹,终于经过自己的努力,挣得了亿万家私。而且,从案情发展的过程看,这个士孙奋与官府没有任何瓜葛,也算是清白人家。仅仅是因为广有家财,而惹来杀身之祸,被官府整得家破人亡。其实,士孙奋的悲剧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悲情地位的真实写照。因为,在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管理体制下,官府尽管并不恶意排斥商业和商人,但官府对商人的容忍是有底线的。一旦商人的富有超过了官府所能容忍的底线,官府就会毫不留情地对商人祭起杀伐大权,可以依任何莫须有的罪名致商人于死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经商发财的不易。在封建社会,商人其实是值得同情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第二,在传统社会商人不能过度显富露财。在一个正常发育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奢侈是一种经济行为,是通过炫耀财富来争取销路、获取信贷的经济手段。所以,市场经济作为外向型经济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市场主体的奢侈行为。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因素不发育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商人的过度炫富常常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举动。因为过度炫富,冲击了官府管理的底线,会引起官员的心生嫉妒,使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权利的强制就会向商人倾倒,迫使商人回到原先官府设定的富裕程度之内。而士孙奋的悲情在于他过于露富于外,上亿资财的家私积累,绝不是官府所能容忍的,自然会成为官府侵夺的对象。从后来的发展看,士孙奋的后人再没有经商为贾,而是走向了读书做官的举业道路,他儿子士孙瑞官做到了大臣的高位。这是官本位社会“逼商为官”的唯一结局。
读懂了这些,我们就会明了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为什么保持着“驽而不贪”、“藏富不露”、“家有万贯资财,出入仅一布袍耳”④的传统,这正是他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①《论语》,中华书局1960年版,《里仁》。
②陈芳:《后汉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34,《梁统列传》。
③挚虞:《三辅决录注》,见《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51,《挚虞传》。
④乾隆《渭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一、秦汉以来的官商关系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资源均为官方掌控,一切话语权也掌握在官方手中,中国的商人就成为与官方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商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其中主要有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和文化因素。
第一,传统社会中贯穿始终的“抑商”政策。中国是一个重农主义的国家,农业、农民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商周以降,中国历代都有商业发展的记载,在社会生活中,商业发挥着“通有无”的重要作用。但是为了保证小农经济这一国家命脉,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一直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商政策从整体上来看就是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对商业和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击。
从经济措施上,首先是“官营禁榷”制度,即: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有利可图,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管仲“官山海之利”;商鞅变法,继续实行“官山泽”政策。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出面经营一切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成为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制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秦汉以来,私人经营盐铁等重要物资,处以极刑,成为一种传统。其次是“重征商税”的办法,即所谓“寓禁于征”。早在商鞅变法时即定下“不农之征必多,有利之租必重”的国策。汉高祖刘邦对商人实行“重租税”打击。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商贾进行打击,“得民财以亿万计”,致使大批商人破产。汉代征收人头税,明定“贾人倍算”(对商人双倍征税)。自汉以后,历代王朝莫不重征商税。
从政治措施上,对商贾进行政治打击,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秦始皇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汉武帝“发七科调”(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经商者直接成为罪人,对商人与商业地位的界定算是到了一种极端的境地。很长时期,“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成为一种惯例,即是说商人作为社会最低层,不得改换门庭当官。这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对商人的服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中国古代服饰历来就有等级之分,而对商人更是严加限制。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律明定“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商人无论怎么富有,服饰上也不得逾制,“金银锦绣”商人虽然买得起却不准用,用就是违规。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传统的国家。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把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中国自战国以后即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官僚体制,“官”的地位崇高,几乎可以取得人们要追求的一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员的身份几乎可以满足一切,包括财富、荣耀、特权。这种一切向官看齐,以官为本的社会心态,也对商人与商业形成重大影响,不仅影响商业本身的发展,也影响人们对从业方式的选择和致富后出路的安排。
第三,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辨”与社会伦理中的商人地位。精神文化与伦理方面,义利之辨早已将商人界定为“小人”的地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追求物质财富的商人在身份上、伦理上甚至心理上,都成为君子的对立面。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商业及商人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的经常因素。战国以降,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在这样一种等级结构中,商人始终处于最低等的位置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的地位总体上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商人们除了经过艰苦努力,赢得财富而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地位并不能因财富的增长而有所提高。
这些就造成了商人每每被官府侵害的悲剧。
二、长安商人士奋孙的经营情况和被迫害过程
士奋孙的经营情况,《后汉书》“梁统列传”中有所记载:
“士孙奋字景卿,少为郡五官掾起家,得钱赀至一亿七千万,富闻京师也。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②
据资料可知,士奋孙是陕西扶风土著。其先祖士孙松(字世兰)是秦国扶风平陵(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其子士奋孙(字景卿)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万余,富闻京师,其子士孙瑞(?—195)字君荣(一说字君策),东汉末年大臣,士孙萌(字文始)之父。③
这士奋孙,原本是长安的一介富翁,先是经营商业,后来又兼营高利贷,发家致富,成为京师闻名的富户。也许是他太富有了,或是树大招风,被东汉末的皇亲梁冀紧紧地盯住了。这梁冀非同小可,他是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梁冀长相十分凶悍,说话口吃,读书甚少,仅能应付最简单的文字和筹算。他的姊妹中一人被顺帝立为皇后,另一位则被立为贵人。梁冀凭借外戚的特殊身份任大将军,历冲帝、质帝、桓帝四朝。顺帝死时,冲帝仍是一个婴儿,梁太后临朝听政,梁冀又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梁冀实际权力极大,在朝中也更加奢侈暴虐。冲帝死后,梁冀又立质帝。质帝自幼聪慧,对梁冀的骄横感受颇深。一次朝会群臣,质帝望着梁冀说:“这是一位跋扈将军!”梁冀听后怀恨在心,立即派人将质帝毒死。梁冀再立尚未成年的桓帝。他一手援立三帝,地位权倾朝纲。幼年的皇帝都不在他的话下,更何况一介商人。梁冀听说京师最有钱的富户是士孙奋,便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土孙奋非常富有,却又吝啬成性,一个铜板都能捏出汗来。他明知是梁冀设计勒索,但迫于淫威,不敢不借,借了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竟有如此不识抬举之人。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孙奋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严刑拷打,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这就是东汉末年一桩最有名的坑商冤案。这桩冤案被多种史籍记载,说明其冤情深重,影响深远。
三、士孙奋冤案的历史启示
汉长安商人士孙奋的冤案,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千古奇冤,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思索。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除了经商养家没有任何出路,就是经过艰辛经营,略有家资,也随时会成为官府侵吞的对象。这个士孙奋就是一介商人,兢兢业业的从事自己的商业经营,也没有任何劣迹,终于经过自己的努力,挣得了亿万家私。而且,从案情发展的过程看,这个士孙奋与官府没有任何瓜葛,也算是清白人家。仅仅是因为广有家财,而惹来杀身之祸,被官府整得家破人亡。其实,士孙奋的悲剧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悲情地位的真实写照。因为,在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管理体制下,官府尽管并不恶意排斥商业和商人,但官府对商人的容忍是有底线的。一旦商人的富有超过了官府所能容忍的底线,官府就会毫不留情地对商人祭起杀伐大权,可以依任何莫须有的罪名致商人于死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经商发财的不易。在封建社会,商人其实是值得同情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第二,在传统社会商人不能过度显富露财。在一个正常发育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奢侈是一种经济行为,是通过炫耀财富来争取销路、获取信贷的经济手段。所以,市场经济作为外向型经济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市场主体的奢侈行为。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因素不发育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商人的过度炫富常常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举动。因为过度炫富,冲击了官府管理的底线,会引起官员的心生嫉妒,使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权利的强制就会向商人倾倒,迫使商人回到原先官府设定的富裕程度之内。而士孙奋的悲情在于他过于露富于外,上亿资财的家私积累,绝不是官府所能容忍的,自然会成为官府侵夺的对象。从后来的发展看,士孙奋的后人再没有经商为贾,而是走向了读书做官的举业道路,他儿子士孙瑞官做到了大臣的高位。这是官本位社会“逼商为官”的唯一结局。
读懂了这些,我们就会明了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为什么保持着“驽而不贪”、“藏富不露”、“家有万贯资财,出入仅一布袍耳”④的传统,这正是他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①《论语》,中华书局1960年版,《里仁》。
②陈芳:《后汉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34,《梁统列传》。
③挚虞:《三辅决录注》,见《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51,《挚虞传》。
④乾隆《渭南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