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忠厚仁义的大唐商人——赵意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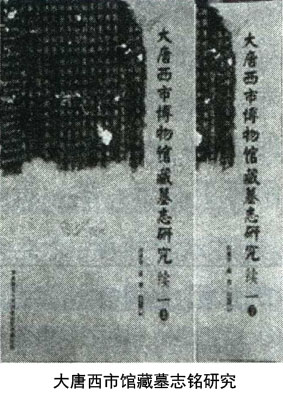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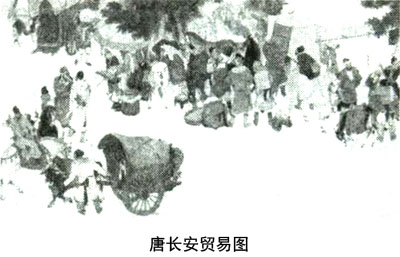
明清之际形成的“陕西商帮”,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形成了以“厚重质直,忠义仁勇”为核心的“陕商精神”。这种陕商精神,是陕西长期作为国都历史地位和传统优秀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唐代关陕商人赵意满,在其经营实践中体现的“忠、孝、贵、富、寿、正、善”的优秀品质,为陕商精神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佐证,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陕商精神”形成的传统基因和历史元素。
一、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的经营概况
据《唐故处士赵府君(意满)墓志铭》载:
“公讳意满,字阿四,天水人也。少遭闵凶,七岁丧父孤孤孩骇。兄弟五人负担相依。枕块无力,隙服未几,亲又长辞,姊妹又种。公年十一,天灾关辅,岁号永淳,骨肉相捐,贵及于残,死弃道路,少及于长……公于是协力西土,提携京东,无所不逮。兄弟因免于委弃,姊妹赖是从夫。光荣里闾,悦怡宗族,受道不士,安贫宴如……夫在白屋奉王税,自幼及长,不求减免,谓之忠;少不失义,长能抚孤,岁寒不移,荣枯若壹,谓之孝;不文不武,不隐不吏,不远王城,不居他职,无忧无惧,非贤非愚,日出而出,日入而入,谓之贵;不汲汲,不惶惶,临财能廉,处均不滥,家有余积,衣服鲜明,谓之富;学荣期之独舞,乐知命之天年,知正足之源,守生死之分,谓之寿;壮年荒荡,晚岁归真,觉今是而昨非,将言行而皆变,祛邪就正,廻向释门,依止师僧,存念儿女谓之正;平生口业,临终守诚……兼此七善。”①
这一大段文字,将一个勤劳守法、诚实经营发家的关陕商人跃然于纸上,并详细刻画了传统陕西商人“忠、孝、贵、富、寿、正、善”精神风貌的历史元素,为我们解读陕商精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佐证。
秦汉以来的墓志铭,一般都是写实的,尤其是民间素封百姓,绝少虚拟夸耀之词。从赵意满的墓志铭看,赵意满是唐秦州人。天水曰秦州,“唐复曰秦州。天宝初,曰天水郡”②,隶属于京畿道,“州当关、陇之会,介雍、凉之间,屹为重镇。秦人始基于此,奄有丰岐……虞允文曰: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③。这也就是最早的“关天一体化”。赵意满身世坎坷,七岁丧父,弟妹五个无所依靠,家无陇亩,衣不暖肤,又遭遇天灾,漏船偏逢连天雨,在艰苦困顿之中,他挺身而出,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以十一岁的少年之躯,务农经商,足迹遍及秦陇,达于洛阳,凡是能赚钱的营生都做遍了,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了经营的成功,“家有余积,衣服鲜明”,为兄弟成家立业,使姊妹嫁娶有归,而且还“光荣里闾,悦怡宗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我们提供了“勤奋劳动致富,合法经营发家”最有说服力的历史典型。
二、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体现的陕商精神元素
关陕商人赵意满的经营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墓志铭》用大量的文字总结了他经营成功的经验,这就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忠、孝、贵、富、寿、正、善”陕商精神的基本元素。人是要有一定精神的。赵意满经营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陕商精神的胜利。他以自身成功的经营实践,阐释了“忠、孝、贵、富、寿、正、善”陕商精神的基本元素。
一是“忠”。“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祥之地,又是中国古代皇都所在,十三朝推为极选,“陕西黄土埋皇上”,千年的帝都文化培育,使陕西人形成“家国一体”的历史自觉和为国争光、光宗耀祖的英雄情结。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是国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基本细胞。血缘关系的纽带将许多家庭集合在一起,形成宗法关系的家族。无数个家族在共同利益驱使和同一文化认同下形成民族,民族的政治表达形式就是国家。这种历史逻辑关系,使陕西人形成“在国为市井之臣”的家国意识,将家庭、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国家利益至上看得高于一切,以“国事为重”,视“为国捐躯”为基本人生价值选择,形成“为国尽忠”、“壮哉民族”的人生价值观和“大丈夫当以国事为先”效忠国家的英雄主义情怀。赵意满正是凸显了这一陕西文化的特点。他以自己成功的脱贫致富经营业绩,“光荣里闾,悦怡宗族”,为家族争得了荣誉,这只是他所表现的陕西文化“忠”的基本层面。而赵意满“忠”的更高境界是“富而不忘国家”,表现了“以商事国,以商兴国”的历史自觉。他“受道不士,安贫宴如”,发财不炫耀张扬,兢兢业业从事自己的经营事业,“夫在白屋奉王税”,以自觉的纳税行为恪尽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而且是“自幼及长,不求减免”,从不逃税避税,体现了陕西人厚重质直的人生性格。赵意满以一介市井小儿,能如此自觉地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谓之忠”。
二是“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忠”是国家行为需求,“孝”则是家族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为孝”。在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层次分明的社会构架下,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家族社会阶梯之中,“上有父老,下有妻小”,享受着一定的家族社会权利,承担着一定的家族社会义务,从而构成稳定的家族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秩序。赵意满正是良好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的行为要求。他以十一岁的少年之躯,在父丧家贫、适逢天灾的重大人生变故面前,挺身而出,“少不失义”,勇敢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经商业贾,商海求财,以自己艰辛的商业行为奔走于关陇洛阳之间,经营陇亩与商贾的琐碎之事,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抚育弟妹,振兴家业,“长能抚孤”,使一家人过上了“男有娶,女有归”的好日子,恪尽了自己的家族责任。而这种“孝悌”的个人行为层级认定,有巨大的社会行为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认清了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时,就会产生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释放出能动的历史创造性正能量,激发“岁寒不移,荣枯若壹”的坚定信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了陕西人强毅果敢、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性格特点。赵意满这种在家族生活中敢于担当、百折不回的经营实践,“少不失义”,不能不“谓之孝”。
三是“贵”。在传统中国社会,践行“忠”、“孝”贵在职业坚守、持之以恒,不管商海潮起潮落,人间风雨沧桑,一心一意从事自己所经营的事业,在“贵于一”的坚守中追求经营效益。中国商谚曰:“大生意在守。”做生意不能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而是要托身行铺,锐意经营。生意顺畅时,不能张扬夸耀,挥金如土,而要素守本分,锱铢必较,预防“彩虹过后风雨骤”的商海风波;生意逆境时,不能哀叹命运,壮志如灰,而要株守家园,咬牙坚持,期盼“来日喜鹊唱枝头”的经营喜讯。靠一股坚忍不拔、忠贞不贰的劲头,在高手如云的商海竞争中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赵意满正是坚守了始终如一的职业节操。他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商业经营,“不文不武,不隐不吏”,既不羡慕为官为宦的高官厚禄,也不追求旌旗猎猎的武门节钺;既不图求猎取高名的隐士雅客,也不委身为吏为衙作威作福,而是恪守自己的商业操守,埋头自己的商业经营,“不远王城,不居他职”,凸显了很高的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表现了秦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并且在经营中,“无忧无惧,非贤非愚”,能保持一种坦然的平静心态,“起居佳胜,营谋遂意;成败由天,造化由命”,敢于面对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商贸事业。这种持之以恒、“日出而出,日入而入”的职业坚守,不能不“谓之贵”。
四是“富”。追求发财致富、生活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生命理性。赵意满正是怀着改变家族命运强烈的致富欲望,以少年柔弱之躯挟资江湖、奔走长路、栉风沐雨、鸡声茅店,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赚钱事业。他身怀使命,“不汲汲,不惶惶”,认准目标,埋头苦干,终于实现理想,脱贫致富,使家人过上了“家有余积,衣服鲜明”的富裕生活。这种靠勤奋经营致富,是一般诚实商人都能够做到的。但赵意满的可贵之处在于,发财致富后能正确地对待财富,不嗜钱如命、见钱眼开、锱铢必较、见利忘义,而是对金钱财富能够保持一种淡然释怀的心态,“临财能廉”,能保持一种不为金钱丧失节操的高贵气节和经商业贾“上以济人,下以利己”,“亏本射利,贾家常事”的良好心态,不为利失义、损人利己,始终坚持诚信待人、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处均不滥”,以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了市场口碑,成为传统商人诚商良贾的代表,表现了秦人博大耿直、“驽而不贪”的人生品格。这种“自己追求利益,不妨碍他人利益”的市场正义和市场诚信,不能不“谓之富”。
五是“寿”。商海经营,长安觅利,得失荣枯,原非一定。面对风波骤起、潮涨潮落的商海风云变幻,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经营业绩,对每一个成功商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传统中国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和贱商剥商的社会氛围下,“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厄运。而赵意满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学荣期之独舞,乐知命之天年”,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夹缝中”④那样,目不交睫地熟探市价、逆料行情,怀致富之奇谋,握持筹之胜算,在商业经营中如鱼得水。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知正足之源,守生死之分”,老老实实地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不投机取巧,不欺行霸市,不假冒伪劣,不以次充好,而是恪守本分,诚信发家,以秦人率真质直的本色品格知足乐命、诚实经营,遵循“利从信中出,益从诚中来”的经营理念,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认同,博得了诚商良贾的市场名声和市场信义,遂使“宝肆宏开,财源不涸,陶朱奇顿,指日可待”,保持了昌盛不败的营业记录。这种按商业经营规律办事的经营作风,不能不“谓之寿”。
六是“正”。陕西沃野千里、一望无垠的自然风貌和皇天后土、周公化育的历史特点,使秦人形成“正义”的社会风气,“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一切以礼仪节操为准,将一身勃然正气传诸儿女。这种讲究“正气”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优秀商人养成的良好土壤。赵意满早年为家族的脱贫致富奔走商海、寄迹廛市,晚年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这是传统商人自我命运的一种取舍,本身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廻向释门”后,一方面“依止师僧”留心佛家典籍,自我修治;另一方面,依然“存念儿女”,以佛家“觉今是而昨非,将言行而皆变”的灵空感悟教育后代、造福子孙、“祛邪就正”,坚持和恪守人间正道,这是一个成功商人的机智策划。因为按照佛家籍典,修世说到底是为了修人。他“晚岁归真”,并没有脱离红尘,而是念念不忘用佛家“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理念,教育子女“祛邪就正”,保持纯正的传统家风,这在中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种“正气”的选择,对于一个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素封商人而言,能够做到这些,也不能不“谓之正”。
七是“善”。赵意满一生经商所遵循的“忠、孝、贵、富、寿、正”理念,最终归结是“善”。“平生口业,临终守诚”,这种“善”既是人性本真的自我流露,又是社会陶冶的最好体现,因为这种“善”,既是人性本身的展现,又是社会道德化育的积极成果,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居“白屋奉王税”承担公民的社会义务,还表现在对家族的“少不失义,长能抚孤”,承担个体生命的家族义务;不仅表现在职业操守中的“岁寒不移,荣枯若壹”的坚定意志,还表现在“临财能廉,处均不滥”的良好道德节操;不仅表现在“乐知命之天年,知正足之源”的个体生命认知,还表现在“存念儿女”、“祛邪就正”的优秀品德遗传。这些不能不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规范。
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身上所体现的“忠、孝、贵、富、寿、正、善”优秀道德品质,是陕西首善之区的历史地位和优秀区域文化长期潜移默化的必然结果。它为后来的陕西商帮形成“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陕商精神”提供了历史养料和遗传基因,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商人优秀品质合理内核的认识。
①龚敬:《唐代三方墓志》,《文物与考古》2010年第2期。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57。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57。
④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74页。
一、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的经营概况
据《唐故处士赵府君(意满)墓志铭》载:
“公讳意满,字阿四,天水人也。少遭闵凶,七岁丧父孤孤孩骇。兄弟五人负担相依。枕块无力,隙服未几,亲又长辞,姊妹又种。公年十一,天灾关辅,岁号永淳,骨肉相捐,贵及于残,死弃道路,少及于长……公于是协力西土,提携京东,无所不逮。兄弟因免于委弃,姊妹赖是从夫。光荣里闾,悦怡宗族,受道不士,安贫宴如……夫在白屋奉王税,自幼及长,不求减免,谓之忠;少不失义,长能抚孤,岁寒不移,荣枯若壹,谓之孝;不文不武,不隐不吏,不远王城,不居他职,无忧无惧,非贤非愚,日出而出,日入而入,谓之贵;不汲汲,不惶惶,临财能廉,处均不滥,家有余积,衣服鲜明,谓之富;学荣期之独舞,乐知命之天年,知正足之源,守生死之分,谓之寿;壮年荒荡,晚岁归真,觉今是而昨非,将言行而皆变,祛邪就正,廻向释门,依止师僧,存念儿女谓之正;平生口业,临终守诚……兼此七善。”①
这一大段文字,将一个勤劳守法、诚实经营发家的关陕商人跃然于纸上,并详细刻画了传统陕西商人“忠、孝、贵、富、寿、正、善”精神风貌的历史元素,为我们解读陕商精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佐证。
秦汉以来的墓志铭,一般都是写实的,尤其是民间素封百姓,绝少虚拟夸耀之词。从赵意满的墓志铭看,赵意满是唐秦州人。天水曰秦州,“唐复曰秦州。天宝初,曰天水郡”②,隶属于京畿道,“州当关、陇之会,介雍、凉之间,屹为重镇。秦人始基于此,奄有丰岐……虞允文曰: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③。这也就是最早的“关天一体化”。赵意满身世坎坷,七岁丧父,弟妹五个无所依靠,家无陇亩,衣不暖肤,又遭遇天灾,漏船偏逢连天雨,在艰苦困顿之中,他挺身而出,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以十一岁的少年之躯,务农经商,足迹遍及秦陇,达于洛阳,凡是能赚钱的营生都做遍了,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了经营的成功,“家有余积,衣服鲜明”,为兄弟成家立业,使姊妹嫁娶有归,而且还“光荣里闾,悦怡宗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我们提供了“勤奋劳动致富,合法经营发家”最有说服力的历史典型。
二、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体现的陕商精神元素
关陕商人赵意满的经营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墓志铭》用大量的文字总结了他经营成功的经验,这就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忠、孝、贵、富、寿、正、善”陕商精神的基本元素。人是要有一定精神的。赵意满经营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陕商精神的胜利。他以自身成功的经营实践,阐释了“忠、孝、贵、富、寿、正、善”陕商精神的基本元素。
一是“忠”。“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祥之地,又是中国古代皇都所在,十三朝推为极选,“陕西黄土埋皇上”,千年的帝都文化培育,使陕西人形成“家国一体”的历史自觉和为国争光、光宗耀祖的英雄情结。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是国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基本细胞。血缘关系的纽带将许多家庭集合在一起,形成宗法关系的家族。无数个家族在共同利益驱使和同一文化认同下形成民族,民族的政治表达形式就是国家。这种历史逻辑关系,使陕西人形成“在国为市井之臣”的家国意识,将家庭、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国家利益至上看得高于一切,以“国事为重”,视“为国捐躯”为基本人生价值选择,形成“为国尽忠”、“壮哉民族”的人生价值观和“大丈夫当以国事为先”效忠国家的英雄主义情怀。赵意满正是凸显了这一陕西文化的特点。他以自己成功的脱贫致富经营业绩,“光荣里闾,悦怡宗族”,为家族争得了荣誉,这只是他所表现的陕西文化“忠”的基本层面。而赵意满“忠”的更高境界是“富而不忘国家”,表现了“以商事国,以商兴国”的历史自觉。他“受道不士,安贫宴如”,发财不炫耀张扬,兢兢业业从事自己的经营事业,“夫在白屋奉王税”,以自觉的纳税行为恪尽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而且是“自幼及长,不求减免”,从不逃税避税,体现了陕西人厚重质直的人生性格。赵意满以一介市井小儿,能如此自觉地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谓之忠”。
二是“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忠”是国家行为需求,“孝”则是家族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为孝”。在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层次分明的社会构架下,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家族社会阶梯之中,“上有父老,下有妻小”,享受着一定的家族社会权利,承担着一定的家族社会义务,从而构成稳定的家族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秩序。赵意满正是良好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的行为要求。他以十一岁的少年之躯,在父丧家贫、适逢天灾的重大人生变故面前,挺身而出,“少不失义”,勇敢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经商业贾,商海求财,以自己艰辛的商业行为奔走于关陇洛阳之间,经营陇亩与商贾的琐碎之事,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抚育弟妹,振兴家业,“长能抚孤”,使一家人过上了“男有娶,女有归”的好日子,恪尽了自己的家族责任。而这种“孝悌”的个人行为层级认定,有巨大的社会行为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认清了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时,就会产生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释放出能动的历史创造性正能量,激发“岁寒不移,荣枯若壹”的坚定信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了陕西人强毅果敢、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性格特点。赵意满这种在家族生活中敢于担当、百折不回的经营实践,“少不失义”,不能不“谓之孝”。
三是“贵”。在传统中国社会,践行“忠”、“孝”贵在职业坚守、持之以恒,不管商海潮起潮落,人间风雨沧桑,一心一意从事自己所经营的事业,在“贵于一”的坚守中追求经营效益。中国商谚曰:“大生意在守。”做生意不能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而是要托身行铺,锐意经营。生意顺畅时,不能张扬夸耀,挥金如土,而要素守本分,锱铢必较,预防“彩虹过后风雨骤”的商海风波;生意逆境时,不能哀叹命运,壮志如灰,而要株守家园,咬牙坚持,期盼“来日喜鹊唱枝头”的经营喜讯。靠一股坚忍不拔、忠贞不贰的劲头,在高手如云的商海竞争中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赵意满正是坚守了始终如一的职业节操。他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商业经营,“不文不武,不隐不吏”,既不羡慕为官为宦的高官厚禄,也不追求旌旗猎猎的武门节钺;既不图求猎取高名的隐士雅客,也不委身为吏为衙作威作福,而是恪守自己的商业操守,埋头自己的商业经营,“不远王城,不居他职”,凸显了很高的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表现了秦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并且在经营中,“无忧无惧,非贤非愚”,能保持一种坦然的平静心态,“起居佳胜,营谋遂意;成败由天,造化由命”,敢于面对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商贸事业。这种持之以恒、“日出而出,日入而入”的职业坚守,不能不“谓之贵”。
四是“富”。追求发财致富、生活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生命理性。赵意满正是怀着改变家族命运强烈的致富欲望,以少年柔弱之躯挟资江湖、奔走长路、栉风沐雨、鸡声茅店,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赚钱事业。他身怀使命,“不汲汲,不惶惶”,认准目标,埋头苦干,终于实现理想,脱贫致富,使家人过上了“家有余积,衣服鲜明”的富裕生活。这种靠勤奋经营致富,是一般诚实商人都能够做到的。但赵意满的可贵之处在于,发财致富后能正确地对待财富,不嗜钱如命、见钱眼开、锱铢必较、见利忘义,而是对金钱财富能够保持一种淡然释怀的心态,“临财能廉”,能保持一种不为金钱丧失节操的高贵气节和经商业贾“上以济人,下以利己”,“亏本射利,贾家常事”的良好心态,不为利失义、损人利己,始终坚持诚信待人、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处均不滥”,以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了市场口碑,成为传统商人诚商良贾的代表,表现了秦人博大耿直、“驽而不贪”的人生品格。这种“自己追求利益,不妨碍他人利益”的市场正义和市场诚信,不能不“谓之富”。
五是“寿”。商海经营,长安觅利,得失荣枯,原非一定。面对风波骤起、潮涨潮落的商海风云变幻,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经营业绩,对每一个成功商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传统中国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和贱商剥商的社会氛围下,“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厄运。而赵意满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学荣期之独舞,乐知命之天年”,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夹缝中”④那样,目不交睫地熟探市价、逆料行情,怀致富之奇谋,握持筹之胜算,在商业经营中如鱼得水。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知正足之源,守生死之分”,老老实实地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不投机取巧,不欺行霸市,不假冒伪劣,不以次充好,而是恪守本分,诚信发家,以秦人率真质直的本色品格知足乐命、诚实经营,遵循“利从信中出,益从诚中来”的经营理念,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认同,博得了诚商良贾的市场名声和市场信义,遂使“宝肆宏开,财源不涸,陶朱奇顿,指日可待”,保持了昌盛不败的营业记录。这种按商业经营规律办事的经营作风,不能不“谓之寿”。
六是“正”。陕西沃野千里、一望无垠的自然风貌和皇天后土、周公化育的历史特点,使秦人形成“正义”的社会风气,“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一切以礼仪节操为准,将一身勃然正气传诸儿女。这种讲究“正气”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优秀商人养成的良好土壤。赵意满早年为家族的脱贫致富奔走商海、寄迹廛市,晚年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这是传统商人自我命运的一种取舍,本身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廻向释门”后,一方面“依止师僧”留心佛家典籍,自我修治;另一方面,依然“存念儿女”,以佛家“觉今是而昨非,将言行而皆变”的灵空感悟教育后代、造福子孙、“祛邪就正”,坚持和恪守人间正道,这是一个成功商人的机智策划。因为按照佛家籍典,修世说到底是为了修人。他“晚岁归真”,并没有脱离红尘,而是念念不忘用佛家“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理念,教育子女“祛邪就正”,保持纯正的传统家风,这在中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种“正气”的选择,对于一个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素封商人而言,能够做到这些,也不能不“谓之正”。
七是“善”。赵意满一生经商所遵循的“忠、孝、贵、富、寿、正”理念,最终归结是“善”。“平生口业,临终守诚”,这种“善”既是人性本真的自我流露,又是社会陶冶的最好体现,因为这种“善”,既是人性本身的展现,又是社会道德化育的积极成果,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居“白屋奉王税”承担公民的社会义务,还表现在对家族的“少不失义,长能抚孤”,承担个体生命的家族义务;不仅表现在职业操守中的“岁寒不移,荣枯若壹”的坚定意志,还表现在“临财能廉,处均不滥”的良好道德节操;不仅表现在“乐知命之天年,知正足之源”的个体生命认知,还表现在“存念儿女”、“祛邪就正”的优秀品德遗传。这些不能不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规范。
大唐关陕商人赵意满身上所体现的“忠、孝、贵、富、寿、正、善”优秀道德品质,是陕西首善之区的历史地位和优秀区域文化长期潜移默化的必然结果。它为后来的陕西商帮形成“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陕商精神”提供了历史养料和遗传基因,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商人优秀品质合理内核的认识。
①龚敬:《唐代三方墓志》,《文物与考古》2010年第2期。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57。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57。
④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