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唐长安靠贩丝绸发家的富商——邹凤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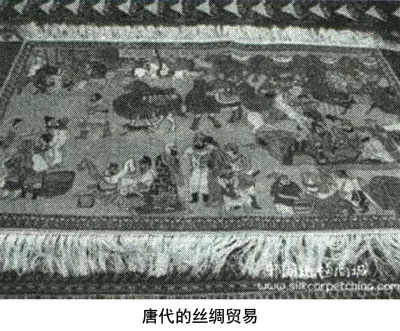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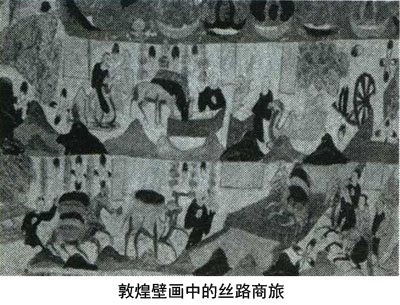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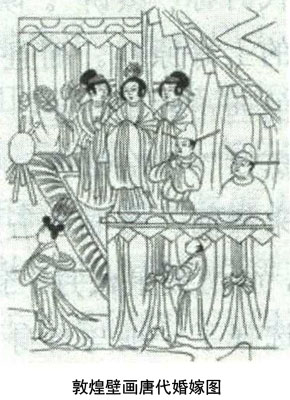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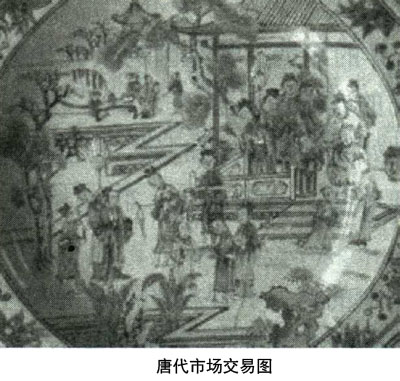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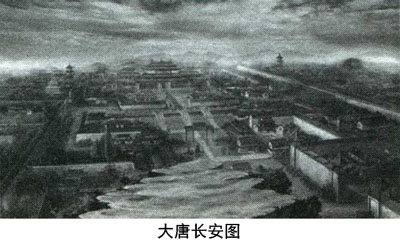

商无定所,市无常法。市场经济下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凡能抓住机遇又善于经营者,就会利用这一平台,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在唐代长安西市,就有一位身患残疾的人,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贩丝绸发家,成为长安城中最富有的人。他就是长安残疾人富商——邹凤炽。
一、唐长安是全国丝绸中心和集散地
长安是唐朝的国都,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生产丝绸历史悠久。唐代丝绸手工业较之前代更为发展,丝绸产地分布广泛,这就使长安的丝绸有了极为广泛的来源。唐朝的丝绸,绢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是唐朝政府户调所征收的重要物品。绢的生产遍及全国许多府州,这从唐政府所定的绢的等级可以略窥全貌。唐政府所定各州绢的等级共分八等90州。前三等为:一等,宋(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亳(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两州;二等,有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沐(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曹(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县)、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四州;三等,有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卫(治所在今河南极县)、陈(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魏(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相(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冀(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德(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海(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徊(治所在今江苏盯眙县)、淮(治所在今山东郸城县)、徐(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充(治所在今山东兖州)、贝(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博(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县)十四州,足见全国丝绸生产的普遍。①
长安所在的关中,也普遍种桑。长安城外的桑树历历成行,所以近处的道路为人们美称“采桑路”②。东边,在今蒲城县南的下邳县是白居易的故乡,他宦居外地时,十分怀念那里“条桑初绿”的种种情景。西边,陇山近处的麟游县,诗人李娇在赴那里的九成宫途中也看到当地“郁郁桑拓繁”的景观。因为关中各地都有蚕桑,所以,长安近处的京兆府(治今西安市)、华州(治今华县)、同州(治今大荔县)都收取赋绢。
同时,长安是国都所在,地处水陆交通中心,联系全国各地,各地的绢和各种丝绸都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年间,水陆转运使韦坚,以三百只船从东南州郡运来当地贡品,其中包括丝绸。船只停泊在禁苑东部望春楼下,渭河上的广运潭内。船上标明丝绸品种名称,还标明丝绸产地。其物品之精奇,其声势之壮,引起“观者山积”,而“京城百姓多不识释马船措竿,人人骇视”③。
唐代按行业形成各种行。丝绸业也有行,现在所能考证的在长安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丝帛彩帛行、总绵丝织行。这些经营丝绸的行,必是丝绸贸易的所在。有一个绢行又兼作“举钱之所”④,反映了这个绢行经营丝绸得体,买卖赚钱,又为人所信任,所以才有他人存钱的事情。
在唐代,丝绸不仅是市场上的热门货,在中国的出口物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以长安为起点通往西域中亚、南亚、西南亚,乃至欧洲的交通大道,正由主要输出中国生产的丝绸,换回西域的黄金,因而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正因为此,在唐代丝绸是人们财富的主要标志之一,唐代市肆交易既用货币,也用实物。绢是作货币使用的。唐朝初年已经规定:“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⑤。贞观十一年(687)马周上疏:“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而天下贴然,百姓皆知陛下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言。至五六年来,频岁丰稳,一匹绢才得粟十余石,百姓皆以为陛下不爱怜之,咸有怨言,”⑥百姓必须的粟米是以绢计价的。开元二十年(732)敕令指出:“绞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通用。”⑦
就是这个锦绣繁华的大唐长安丝绸世界,为而后邹凤炽的闪亮登场准备了舞台。
二、邹凤炽的经营概况
《太平广记》中对邹凤炽的经营有所记载:
“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他曾经请市终南山中树,一棵树估绢一匹,自称“山树虽尽,臣绢未竭。”⑧
邹凤炽的发家与一段传奇有关。
唐天宝年间,在长安胜业坊,一个人艰难地推着小车朝大街方向走去,两肩高后背弯曲,像骆驼似的。他姓邹,因为驼背,远近的人们都管他叫“邹骆驼”。他以卖蒸饼为生,那辆小车上装着制作蒸饼的灶具和面粉。当车子经过一个拐弯处时,轮子碰上了露出地面的石块,小车翻倒在地,车上的面粉撒了一地,他黯然地坐在地上,望着满地的面粉伤心落泪。这几块露出地面的石头已经多次造成小车倾倒,这一次邹骆驼再也忍不住了,他从家里拿来工具要挖出这些绊脚石。如果不是这一挖,邹骆驼的小车恐怕会一直推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但这一挖改变了他的命运,埋在土下的石块有好几层,一层一层挖下去之后,露出一个瓷瓮,打开瓮口一看,里面装着砂金,大约有五斗。
这“五斗金”使他迈开了通向致富的步伐。他看到当时的长安丝绸是中外经营的大路货,贩卖丝绸没有不发财的,于是就将这五斗金投资丝绸贩运,不料一举成功,成为长安城有名的大富翁,“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的财产以积绢计算,当时绢每匹200钱左右,即使有一万匹也不过数千贯钱。他把家搬到了富人们居住的怀德坊南门东,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邹凤炽”。
他几乎成为当时国内的首富。四面八方的货物全被他收买下来,即使是古时的猗顿,也超不过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仆女仆,都是穿锦衣吃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曾经因为女儿出嫁,邀请朝廷中的官员参加婚礼酒席,来庆祝的宾客有几百人,到了夜间,还供应帐幕休息,里面华丽到极点。等到姑娘快出来的时候,一群女仆围绕着新娘,都穿着绮罗,戴着珠翠,低着头,小步走路,特别艳丽,大家都愣了,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子。
他曾经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1棵树的价格是1匹绢。他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不会光。”事情虽然没有实行,终于被天下人传诵。
三、邹凤炽经营故事的历史启示
邹凤炽以商求富的历史故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启迪:
首先是他的身残志坚,不惧艰难。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残疾人一般是被社会歧视的对象,他们能够艰难生存已经不易,很难做到大富大贵。而邹凤炽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身有残疾,自强不息,在长安西市靠推车卖蒸饼为生。“蒸饼”就是今日的“蒸馍”,唐代时称“蒸饼”。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盛产小麦,是制作蒸馍的上好原料。而且,陕西人自古就喜欢吃劲道、有嚼头的蒸馍,在唐代的西市和里坊里,到处都有卖“蒸饼”的小店和沿街叫卖的小贩。做“蒸饼”十分辛苦,一般三更天就要起来揉面、蒸制,五更天就要上市出卖,可谓披星戴月。邹凤炽不辞劳苦,他选择了一项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的经营项目,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表现了秦人坚毅不屈的倔犟性格。同时也说明,生意在路上。做生意不在大小,凡是有需求的就是好生意,对经营项目的选择,不能好高骛远,不着边际,而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久而久之,坚持不懈,就会积累丰富的市场经验,生意就会越做越大。
其次是适时营销,目光高远。市场是需求的统一,做生意就要逆料行情,掌握变化。邹凤炽早年卖蒸饼,就是最保险的经营项目。因为,唐长安600万人,市场巨大,需求集中,陕西人又喜好吃蒸饼;而做蒸饼投资不大,技术易于掌握,只要做到货真价实,不愁没有市场。靠卖蒸饼掘得市场的第一桶金后,邹凤炽没有故步自封,稍富即安,满足于自己的小本经营,而是将投资目光盯住了当时最能取得丰厚利润的丝绸贸易之上。因为,隋唐时期,中国强盛,中国的丝绸贸易正处在最鼎盛时期,西域各国包括欧洲大量需要中国的丝绸,大量西方胡商不远万里到中国来采购丝绸,中国商人组成驼队将丝绸贩运到西域,赚取了大量的黄金,西安何家村唐代陵墓出土的文物中,大量都是罗马和西域的金币,就是明证。加之,长安又是全国丝绸集散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丝绸市场,做丝绸生意,需求集中,市场广大,容易发财致富。邹凤炽以娴熟的商业经营目光,又盯住了这一块最有发展潜力和最能获利的市场,大胆投资,迅速致富,成为大唐西市有名的富翁,其富裕程度可以与古代的大富豪郑通、猗顿相酹,一时名扬海内。邹凤炽的发财经历说明,市无贵贱,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商机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小人物也能做成大生意。关键在于熟悉行情,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敢冒风险,残疾人也能脱蛹化蝶,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是张扬财富,博取名声。邹凤炽发财致富后,并没有像一般陕西人那样藏富不露,而是在中国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下,敢于冲破传统,大肆张扬财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他家的富有在当时被称为“邹家富窟”,女儿出嫁时,满园佳丽,像是在搞“选美大会”。他还向唐高宗提出,用1棵树1匹绢的价格,购买终南山上所有的树木,并夸耀说:“终南山的树尽,而吾家绢不尽。”
这种不遗余力的夸耀财富,并不是邹凤炽的小人得志、土豪形象。当我们联系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商人们夸耀财富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合理阐释。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下,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人格得不到社会平等的认同和待遇,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地位上却与贱民同列,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下。在这种社会高压下,商人们的心理被扭曲,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弹,他们往往会选择夸耀财富的方式,顽强地向社会宣示他们的社会存在,并通过炫耀财富来引起社会的重视,宣泄心中的积愤,求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这应当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行为。同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营方式。市场经济是实力经济,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市场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权利是一样的,丛林法则永远是市场无法抗拒的残酷现实。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富有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拥有财富的多寡,市场永远会向成功者投去掌声和鲜花,商人们通过夸耀财富便是向社会宣告他们的成功,并通过这种炫富为自己挣得合理的社会地位,争取更多的投资和订单。马克思一再说,在商品经济下奢侈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商人争取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的手段,没有奢侈就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封建自然经济的传统眼光看待商人们的耀富行为。而且,邹凤炽如此大胆地炫耀财富,正证明了大唐时代是一个富裕和开放的时代,唐王朝的励精图治,就是让民众富裕起来,像邹凤炽这样的残疾人尚且可以取得如此富有的商业业绩,使人们可以从一滴水中看到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最后,邹凤炽作为一个残疾人,在他成功经商的历程中,一定经历了许多正常人无法体验的歧视和磨难,当他经营成功后,将家园搬到长安的富人区“怀德坊”,并将自己的名字由“邹骆驼”改为“邹凤炽”,正是他对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实的合理反叛和心灵抗争。这本身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们的耀富行为不能冲破官府可能容忍的底线,否则,就会因官府的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
①曹尔琴:《唐代长安的丝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②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页。
③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5,《韦坚传》。
④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303,《王塑》。
⑤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6,《赋税下》。
⑥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74,《马周传》。
⑦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16,《杂录》。
⑧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495,《杂录3·邹凤炽》。
一、唐长安是全国丝绸中心和集散地
长安是唐朝的国都,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生产丝绸历史悠久。唐代丝绸手工业较之前代更为发展,丝绸产地分布广泛,这就使长安的丝绸有了极为广泛的来源。唐朝的丝绸,绢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是唐朝政府户调所征收的重要物品。绢的生产遍及全国许多府州,这从唐政府所定的绢的等级可以略窥全貌。唐政府所定各州绢的等级共分八等90州。前三等为:一等,宋(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亳(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两州;二等,有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沐(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曹(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县)、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四州;三等,有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卫(治所在今河南极县)、陈(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魏(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相(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冀(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德(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海(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徊(治所在今江苏盯眙县)、淮(治所在今山东郸城县)、徐(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充(治所在今山东兖州)、贝(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博(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县)十四州,足见全国丝绸生产的普遍。①
长安所在的关中,也普遍种桑。长安城外的桑树历历成行,所以近处的道路为人们美称“采桑路”②。东边,在今蒲城县南的下邳县是白居易的故乡,他宦居外地时,十分怀念那里“条桑初绿”的种种情景。西边,陇山近处的麟游县,诗人李娇在赴那里的九成宫途中也看到当地“郁郁桑拓繁”的景观。因为关中各地都有蚕桑,所以,长安近处的京兆府(治今西安市)、华州(治今华县)、同州(治今大荔县)都收取赋绢。
同时,长安是国都所在,地处水陆交通中心,联系全国各地,各地的绢和各种丝绸都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年间,水陆转运使韦坚,以三百只船从东南州郡运来当地贡品,其中包括丝绸。船只停泊在禁苑东部望春楼下,渭河上的广运潭内。船上标明丝绸品种名称,还标明丝绸产地。其物品之精奇,其声势之壮,引起“观者山积”,而“京城百姓多不识释马船措竿,人人骇视”③。
唐代按行业形成各种行。丝绸业也有行,现在所能考证的在长安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丝帛彩帛行、总绵丝织行。这些经营丝绸的行,必是丝绸贸易的所在。有一个绢行又兼作“举钱之所”④,反映了这个绢行经营丝绸得体,买卖赚钱,又为人所信任,所以才有他人存钱的事情。
在唐代,丝绸不仅是市场上的热门货,在中国的出口物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以长安为起点通往西域中亚、南亚、西南亚,乃至欧洲的交通大道,正由主要输出中国生产的丝绸,换回西域的黄金,因而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正因为此,在唐代丝绸是人们财富的主要标志之一,唐代市肆交易既用货币,也用实物。绢是作货币使用的。唐朝初年已经规定:“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⑤。贞观十一年(687)马周上疏:“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而天下贴然,百姓皆知陛下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言。至五六年来,频岁丰稳,一匹绢才得粟十余石,百姓皆以为陛下不爱怜之,咸有怨言,”⑥百姓必须的粟米是以绢计价的。开元二十年(732)敕令指出:“绞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通用。”⑦
就是这个锦绣繁华的大唐长安丝绸世界,为而后邹凤炽的闪亮登场准备了舞台。
二、邹凤炽的经营概况
《太平广记》中对邹凤炽的经营有所记载:
“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他曾经请市终南山中树,一棵树估绢一匹,自称“山树虽尽,臣绢未竭。”⑧
邹凤炽的发家与一段传奇有关。
唐天宝年间,在长安胜业坊,一个人艰难地推着小车朝大街方向走去,两肩高后背弯曲,像骆驼似的。他姓邹,因为驼背,远近的人们都管他叫“邹骆驼”。他以卖蒸饼为生,那辆小车上装着制作蒸饼的灶具和面粉。当车子经过一个拐弯处时,轮子碰上了露出地面的石块,小车翻倒在地,车上的面粉撒了一地,他黯然地坐在地上,望着满地的面粉伤心落泪。这几块露出地面的石头已经多次造成小车倾倒,这一次邹骆驼再也忍不住了,他从家里拿来工具要挖出这些绊脚石。如果不是这一挖,邹骆驼的小车恐怕会一直推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但这一挖改变了他的命运,埋在土下的石块有好几层,一层一层挖下去之后,露出一个瓷瓮,打开瓮口一看,里面装着砂金,大约有五斗。
这“五斗金”使他迈开了通向致富的步伐。他看到当时的长安丝绸是中外经营的大路货,贩卖丝绸没有不发财的,于是就将这五斗金投资丝绸贩运,不料一举成功,成为长安城有名的大富翁,“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的财产以积绢计算,当时绢每匹200钱左右,即使有一万匹也不过数千贯钱。他把家搬到了富人们居住的怀德坊南门东,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邹凤炽”。
他几乎成为当时国内的首富。四面八方的货物全被他收买下来,即使是古时的猗顿,也超不过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仆女仆,都是穿锦衣吃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曾经因为女儿出嫁,邀请朝廷中的官员参加婚礼酒席,来庆祝的宾客有几百人,到了夜间,还供应帐幕休息,里面华丽到极点。等到姑娘快出来的时候,一群女仆围绕着新娘,都穿着绮罗,戴着珠翠,低着头,小步走路,特别艳丽,大家都愣了,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子。
他曾经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1棵树的价格是1匹绢。他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不会光。”事情虽然没有实行,终于被天下人传诵。
三、邹凤炽经营故事的历史启示
邹凤炽以商求富的历史故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启迪:
首先是他的身残志坚,不惧艰难。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残疾人一般是被社会歧视的对象,他们能够艰难生存已经不易,很难做到大富大贵。而邹凤炽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身有残疾,自强不息,在长安西市靠推车卖蒸饼为生。“蒸饼”就是今日的“蒸馍”,唐代时称“蒸饼”。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盛产小麦,是制作蒸馍的上好原料。而且,陕西人自古就喜欢吃劲道、有嚼头的蒸馍,在唐代的西市和里坊里,到处都有卖“蒸饼”的小店和沿街叫卖的小贩。做“蒸饼”十分辛苦,一般三更天就要起来揉面、蒸制,五更天就要上市出卖,可谓披星戴月。邹凤炽不辞劳苦,他选择了一项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的经营项目,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表现了秦人坚毅不屈的倔犟性格。同时也说明,生意在路上。做生意不在大小,凡是有需求的就是好生意,对经营项目的选择,不能好高骛远,不着边际,而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久而久之,坚持不懈,就会积累丰富的市场经验,生意就会越做越大。
其次是适时营销,目光高远。市场是需求的统一,做生意就要逆料行情,掌握变化。邹凤炽早年卖蒸饼,就是最保险的经营项目。因为,唐长安600万人,市场巨大,需求集中,陕西人又喜好吃蒸饼;而做蒸饼投资不大,技术易于掌握,只要做到货真价实,不愁没有市场。靠卖蒸饼掘得市场的第一桶金后,邹凤炽没有故步自封,稍富即安,满足于自己的小本经营,而是将投资目光盯住了当时最能取得丰厚利润的丝绸贸易之上。因为,隋唐时期,中国强盛,中国的丝绸贸易正处在最鼎盛时期,西域各国包括欧洲大量需要中国的丝绸,大量西方胡商不远万里到中国来采购丝绸,中国商人组成驼队将丝绸贩运到西域,赚取了大量的黄金,西安何家村唐代陵墓出土的文物中,大量都是罗马和西域的金币,就是明证。加之,长安又是全国丝绸集散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丝绸市场,做丝绸生意,需求集中,市场广大,容易发财致富。邹凤炽以娴熟的商业经营目光,又盯住了这一块最有发展潜力和最能获利的市场,大胆投资,迅速致富,成为大唐西市有名的富翁,其富裕程度可以与古代的大富豪郑通、猗顿相酹,一时名扬海内。邹凤炽的发财经历说明,市无贵贱,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商机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小人物也能做成大生意。关键在于熟悉行情,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敢冒风险,残疾人也能脱蛹化蝶,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是张扬财富,博取名声。邹凤炽发财致富后,并没有像一般陕西人那样藏富不露,而是在中国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下,敢于冲破传统,大肆张扬财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他家的富有在当时被称为“邹家富窟”,女儿出嫁时,满园佳丽,像是在搞“选美大会”。他还向唐高宗提出,用1棵树1匹绢的价格,购买终南山上所有的树木,并夸耀说:“终南山的树尽,而吾家绢不尽。”
这种不遗余力的夸耀财富,并不是邹凤炽的小人得志、土豪形象。当我们联系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商人们夸耀财富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合理阐释。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下,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人格得不到社会平等的认同和待遇,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地位上却与贱民同列,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下。在这种社会高压下,商人们的心理被扭曲,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弹,他们往往会选择夸耀财富的方式,顽强地向社会宣示他们的社会存在,并通过炫耀财富来引起社会的重视,宣泄心中的积愤,求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这应当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行为。同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营方式。市场经济是实力经济,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市场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权利是一样的,丛林法则永远是市场无法抗拒的残酷现实。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富有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拥有财富的多寡,市场永远会向成功者投去掌声和鲜花,商人们通过夸耀财富便是向社会宣告他们的成功,并通过这种炫富为自己挣得合理的社会地位,争取更多的投资和订单。马克思一再说,在商品经济下奢侈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商人争取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的手段,没有奢侈就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封建自然经济的传统眼光看待商人们的耀富行为。而且,邹凤炽如此大胆地炫耀财富,正证明了大唐时代是一个富裕和开放的时代,唐王朝的励精图治,就是让民众富裕起来,像邹凤炽这样的残疾人尚且可以取得如此富有的商业业绩,使人们可以从一滴水中看到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最后,邹凤炽作为一个残疾人,在他成功经商的历程中,一定经历了许多正常人无法体验的歧视和磨难,当他经营成功后,将家园搬到长安的富人区“怀德坊”,并将自己的名字由“邹骆驼”改为“邹凤炽”,正是他对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实的合理反叛和心灵抗争。这本身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们的耀富行为不能冲破官府可能容忍的底线,否则,就会因官府的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
①曹尔琴:《唐代长安的丝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②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页。
③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5,《韦坚传》。
④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303,《王塑》。
⑤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6,《赋税下》。
⑥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74,《马周传》。
⑦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16,《杂录》。
⑧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495,《杂录3·邹凤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