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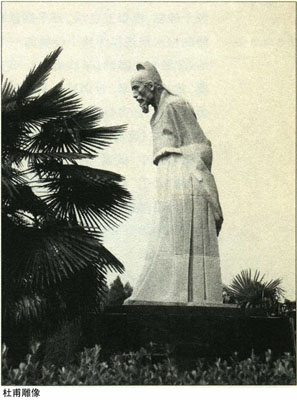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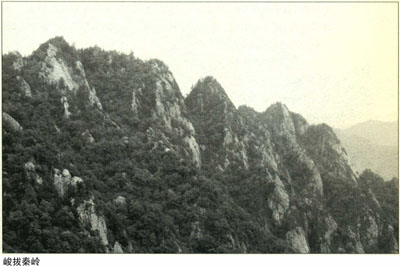
中国素以诗国相称。有唐一朝,三百年春秋,千余名骚人墨客,更是诗国文明中的绚烂华章与绝唱国风。基于此,盛唐又被称之为“诗唐”——即“诗的唐朝”与“诗的王国”。闻一多先生也说要认识唐诗,须先认识“诗唐”,即“诗的唐朝”,他说:“‘诗唐’的另一涵义,也可解释为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唐人作诗之普遍,可说是空前绝后,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写,达到任何失误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唐诗与长安》阎琦,P.6)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就诗歌文本看,秦朝与唐朝无法相比。秦岭简直是一座唐诗之山,诗唐之山,是一座人类诗歌创造的“诗山”和“灵山”。盛唐的诗歌创作,使秦岭成为诗唐之山,秦岭仍然未演变为“唐山”。我们对此并不以为憾,反更觉诗唐之大气与唐诗之美境。唐诗一般称秦岭为南山、终南山、太乙山,这一方面是文化传承上的周秦汉遗风,一方面来自于秦岭的地望审美。在唐诗中,最接近“唐山”的,是“秦山”名称。皇甫冉《送孔党赴举》:“楚水通荥浦,春山拥汉京。爱君方弱冠,为赋少年行。”杜甫《登慈恩寺》:“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在皇甫冉《送孔党赴举》中,“秦山拥汉京”与“楚水通蒙浦”相对应,“秦山”呼应“楚水”。在杜甫《登慈恩寺》中,“秦山忽破碎”,写家国之愁。“秦山”在诗唐的出现,或为纯粹文本上的对称修辞需要(皇甫冉),或因登高怀古的家国愁情(杜甫)。至于诗唐出现的“秦岭”,则直接意味一种悲剧之缘,韩愈著名的“云横秦岭”,是纯粹的个人悲剧与国家悲剧。在诗唐文化语境,一般而言,“秦岭”与南山(寿比南山)相比,总是一种否定性、悲剧性的命名呼叫。在诗唐世界,一个自然地理实体,呈现出“南山”和“秦岭”的两重天:一个乐观赞美,一个消极否定。再举数例,可知诗唐中的“秦岭”意境的否定性和悲剧色彩。
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
尚颜《冬暮送人》:“长安冬欲尽,又送一遗贤。醉后情浑可,言休理不然。射衣秦岭雪,摇月汉江船。亦过春兼夏,回期信有蝉。”
岑参《登总持阁》:“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杜甫《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闻道王乔舄,名因太史传。如何碧鸡使,把诏紫微天。秦岭愁回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杂,吾舅意凄然。”
杜甫此诗,道出了“秦岭”意境否定性和悲剧色彩的三种因素:①在“紫微天”比照下的“低”。岑参《登总持阁》中,是以“金仙”和“逼诸天”高阁,引出“槛外低秦岭”。杜甫此诗,是以“闻道王乔舄”的“紫微天”,写“愁回马”的秦岭。②离开京畿长安的“悲”。杜甫的“吾舅意凄然”,源于“自京赴任青城”。“初贬官”的白居易,是从长安去江州的“过望秦岭”。③在天涯漂泊的“醉”。尚颜《冬暮送人》是在长安的“醉后情浑可”,杜甫是在四川的“涪江醉泛船”。
与此相反,诗唐对于“南山”和终南山基本是赞美和歌颂。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写终南山接近“天都”,写终南山就是“天都”。李世民的《望终南山》:“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写终南山“恬千虑”的巨大作用,等于“访九仙”。
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写“明主弃”“故人疏”,只有“南山敝庐”才是咱的家啊!
杜甫《曲江五句》之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面对南山,从《曲江五句》之三开始,杜甫“自断此生休问天”。“南山桑田”,才是咱的家啊!与王维《终南山》的“天都”、李世民《望终南山》的“九仙”对照,孟浩然的“南山敝庐”和杜甫的“南山桑田”就是南山诗的两重天。杜甫《曲江五句》的“自断此生休问天”,甚至于不想“问天”。尽管与天子(李世民)骄子(王维)们的终南山无法比较,孟浩然的“南山敝庐”和杜甫的“南山桑田”表明:对于他们而言,南山还是陶渊明的“吾亦爱吾楼”啊!
从诗唐大的范围看,秦岭南山诗的创作可分为主体全景、背景特写和比兴喻指三个类型。主体全景类型,是指诗作的内容全部是秦岭的山水描写。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常建《梦太白西峰》和李世民的《望终南山》。我们以孟浩然《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为例。其诗写道:“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邵平能就我,开径剪蓬麻。”背景特定类型,指秦岭的山水描述仅为整个诗境的一个自然要素。如李白的《黄葛篇》,杜甫的《昔游》,王维的《早秋山中》。我们以李白的《黄葛篇》为例:“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绵幂。青烟蔓长条,缭绕几百尺。闺人费素手,采缉作絺绤。缝为绝国衣,远寄日南客。苍梧大火落,暑服莫轻掷。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迹。”在《黄葛篇》中,李白固然写了秦岭山中的“黄葛”和“洛溪”,描写了秦岭山中“黄葛”的“青烟蔓长条,缭绕几百尺”;但诗的主体乃是“闺人”的“素手”和“妙手”。通过“闺人费素手”,远方的那位“南客”获得了人间的温暖情感,百代的我们认知了秦岭的一件“国衣”。
秦岭唐诗的第三种类型,即比兴喻指类型。比兴喻指类型,既不同于主体全景类型,也不同于背景特定类型——前两种唐诗类型都落脚于自然景物及其生成延伸的生活环境,比兴喻指唐诗则落实于政治社会背景。在把秦岭山川仅仅作为诗歌的一个要素上,背景特定与比兴喻指是一致的;而在将秦岭山川作为自然描写方面,主体全景与背景特写又是相一致的。李白的《白马篇》、杜甫的《义鹖》、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皆属于比兴喻指类型。我们以白居易《草茫茫》为例。其诗写道:“草茫茫,土苍苍。苍苍茫茫在何处?骊山脚下秦皇墓。墓中下涸二重泉,当时自以为深固。下流水银象江海,上缀珠光作乌兔。别为天地于其间,拟将富贵随身去。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籍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草茫茫》虽然也有“骊山”“秦皇墓”和“灞陵原”,其旨趣根本上在社会政治内涵,更多是围绕王朝迁变的历史地理与秦岭的政治地理内容。以白居易、元稹为领袖的唐诗比兴喻指类型,其诗学无疑来源于《诗经》的比兴风格。
唐代之后,秦岭终南山也并未因诗唐文化而改名叫做“唐山”,华夏国人却被称呼为“唐人”。欧美国家有许多“唐人街”,美国旧金山有著名的“唐人街”。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经常就有唐诗朗诵啊!唐诗,构成华夏伟大的历史文明,有九州的大好河山;“唐人”更多属于海外赤子,是华夏同胞的梦里江山。
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高从宜,王小宁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