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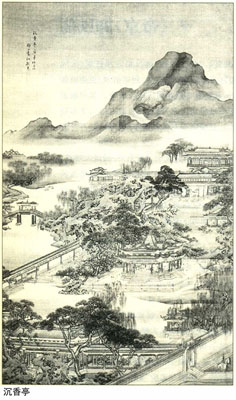
华夏上古有《尧典》有《禹贡》。秦汉以降,高汉祖刘邦曾唱《大风歌》,建安曹操父子有《观沧海》《洛神赋》与《典论》。唐盛诸君,更迈前朝帝王,唐中宗、唐玄宗、唐宣宗、武则天皇后均留诗作于万世。其中最著名者,还是“秦王”李世民。历史世界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文本领域他又豪情大赋《帝京篇十首》,显赫帝业与雅奥诗章交相辉映,万古流芳矣。
中国古代帝王,世称天子。李世民作为天子,《帝京篇》的最大特点,即气派雄大的“天子”眼光。《帝京篇》之五,他写“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帝京篇》之三,他写“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帝京篇》之六,他写“落日双阙昏,回舆九重暮。长烟散初碧,皎月澄轻素”;《帝京篇》之九,李世民有最明确的天子宣言:“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且让我们欣赏《帝京篇》之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在这首《帝京篇》之一,唐太宗用“雄”“壮”,描写秦岭形胜对“帝宅”“皇居”的营构衬托与美感力量。这种力量是强大厚重的,李世民选择用“雄”“壮”表现,于自然审美上属崇高范畴。“连薨”“飞观”是“秦川”“函谷”雄壮,“帝宅”“皇居”的具体伸延,着眼于“遥接汉”“迥凌虚”的无限空间幅度,及其与“天”的亲切对话。“遥接”“迥凌”更多的是空间性力量的气势崇高;“倚殿”“离宫”,则是时间性的审美逗留;“千寻”“百雉”是数量化的绵延无限。
近代美学将人类的审美现象分为优美、崇高、喜剧与悲剧四大范畴。李世民《帝京篇》应该属于崇高一类。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又将崇高分为力学与数学两大类型,《帝京篇》都有体现。末尾两句的“雪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又以“雪日”寒景与“风烟”朦胧给全诗崇高之境以节制,予以“绮疏”化,意味绵长,得含蓄之美。这种诗学上的道理,在《帝京篇》之十也即最后一篇,李世民已经写清楚了:“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过分高危了,需要“隐于雪日”;过分盈荡了,应该“入乎风烟”。李世民《帝京篇》,崇高与优美平衡的诗学风格,源自《易经》的“潜龙”智慧与“六五之道”——《帝京篇》末尾写道:“六五诚难继”啊!从《帝京篇》,人们可以见出李世民的精神、功底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的秦岭终南山,给予唐太宗的精神境界。诗唐有千余首诗歌吟过终南山,其中就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望终南山》。撇开诗人九五之尊贵,千古之王气,就诗艺本身而言,李世民的《望终南山》亦可圈可点。其亮点有三:其一,起句“重峦俯渭水”,就把关中宏观自然地理的一山(秦岭)一水(渭河)的社稷形象优先表达了出来。其二,“出红”到“疑全”,在对秦岭景色的描写中,“红日”“绿夜”与“朝”都融入其中了,只差一个“月”,秦岭的这首“帝风篇”,真正是“日、月、朝、夜、红、霞、绿、烟”八面玲珑、满汉全席,庶为南山的皇室绝唱。其三,李世民以“无劳访九仙”,给予秦岭以崇高精神地位——终南山在“九仙”之上!在《望终南山》,李世民这样描写秦岭: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对唐太宗李世民而言,秦岭终南山那些“俯渭水的重峦”,那些“插遥天的碧嶂”,还有那些“朝若夜的叠松”与“阙疑全的复岫”,已经那么形象直观地道说了天道自然的“上”(“插遥天”)与“下”(“俯渭水”),已经那么深沉地呈现了人间世界的“永恒”(“朝若夜”)与“变易”(“阙疑全”)的奥妙道理,当然是“无劳访九仙”啊!或曰:秦岭终南山,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世最好的高仙天师吧。否则,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大忙君”,何以用眼“望终南山”之后,还要用笔《望终南山》呢。
面对帝京,李世民一派御气;面对南山,李世民一派御气;就是面对“旧宅”,李世民也是一派御气。围绕《过旧宅》,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两首诗。《过旧宅》其一写道:“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新丰”,在今天的西安市临潼区,有李世民的“旧宅”。尽管“径新园荒”“苔古阶斜”,唐帝仍发现了“旧宅”的生命力:“前池旧水”的“树发今花”;并在此生命力发现与延续的基础上,作出高昂乐观的结语:“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一朝”对“四海”,“旧宅”对“大家”——这“离别”的经历,唐帝李世民写成了何等高昂乐观的主题!在“四海为家”的主人面前,“停翠辇”的新丰“旧宅”,分明吹拂着浓郁的御风啊!
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高从宜,王小宁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