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法定律
郭志坤
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实行法治的原则。据《唐律疏义》解释:“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一也。”又说,战国时期,魏李悝辑各国的法,编成《法经》,后来商鞅“改法为律”。“律”是齐一的意思。据《说文解字》云:“律,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秦始皇强化法律制度,实行法治,目的也完全是为了“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的。
第一节 编纂法典
秦始皇当政后在着手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的同时,就提出了编纂成文法典的任务。
编纂法典的时间
秦的法律和制度,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清代学者孙楷曾经指出:秦虽然立法过于严峻,但“自汉以来递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秦会要原序》)。由于年代久远,关于秦代具体编纂法典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史料也甚为缺乏。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除了《编年纪》以外,都与秦的法律制度有直接关系。其中《语书》是公布法律的文告;《为吏之道》是官吏守则,实际是官吏执法、守法之道;《法律答问》主要是对刑法条文的运用和解释,涉及《盗律》、《贼律》、《囚律》、《杂律》、《具律》等多方面的内容;《封诊式》主要是诉讼程序法规和有关侦查、勘验、审讯等法律文书的程式。其他则涉及行政法、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内容。在《法律答问》中也有一部分是行政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
从睡虎地新出土的秦简上看,除了商鞅变法时颁行的《刑律》、《军爵律》之外,还有《田律》等三十项单行法规。这些为数众多的单行法规和其他法律文献,就为秦始皇编纂比较完善的成文法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秦始皇编纂法典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当前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即进行对法典的编纂。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这项工作早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着手进行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泰山刻石》说:“皇帝临位,作制明法。”《琅琊刻石》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芝罘刻石》说:“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会稽刻石》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秦始皇继承王位时,年仅十三岁,朝廷大权还掌握在太后、嫪毐、吕不韦集团的手中,显然还谈不上由他主持编纂法典的工作。“刻石”中所言“临位”、“临国”又能“作始”、“作治”,那当指粉碎嫪毐、吕不韦集团之后的事。
比较系统的法典到什么时候编成呢?这里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
一、《芝罘刻石》中说:“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法典编成后还“外诛暴强”,这说明编纂法典工作在全国统一前已经完成了。
二、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南郡守腾发布《语书》说:“今法令已具矣。”这里更是说明秦始皇编纂法典工作当在此以前完成。
从公元前238年粉碎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后,秦始皇便着手进行成文法典的编纂工作,大约到公元前227年以前完成了这项任务,前后共花费十多年时间。
法典的主要内容
《会稽刻石》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这说明秦始皇编纂新的成文法典是把众多的单行法规根据新的情况略加修改后汇编而成的。其基本内容来源于战国初期魏国李悝的《法经》。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将《法经》的六法改为六律,是为秦国制定法律之始。李斯等人又在原六律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损益,制定了轻罪重罚、繁密苛刻的《秦律》。尽管《秦律》的正式文本亡佚了,但据文献的零星记载,可见其概貌。从睡虎地新出土的秦简上看,秦始皇编纂的成文法典中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在刑事和民事以及诉讼法方面,除了商鞅变法时颁行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之外,还包括新出土的《法律答问》的全部内容。这里涉及犯罪构成、量刑标准、刑事责任、共犯、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自首、累犯、数罪并罚、损害赔偿、婚姻的成立及解除、财产继承等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概念,也涉及诉讼权利、案件复查、诬告、失刑、不直、纵囚等诉讼法的理论原则问题。仅《法律答问》就有一百八十七条,除去二十六条关于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其余一百六十一条中有关惩治盗窃的有四十五条,属于惩治所谓“贼”的有四十一条。这里所谓的“贼”,当然不是指别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备受压迫剥削而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民众。这正体现了李悝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主张(桓谭:《新论》)。这充分说明,秦律的主要惩治对象是劳动民众。
二、行政法是秦始皇编纂的法典中的重要内容。秦律除了对劳动民众实行镇压的内容外,还有对官吏们实行控制的规定。商鞅变法后,秦国家政权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以中央统一任免官吏的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度。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队伍,就需要用法来规定各级国家机关的有组织的活动,规范和约束大小官吏的行为。在秦简中,有不少类似现代国家的行政法规。如《置吏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等。秦律对官吏的任用是严格的,它重视政治标准,也突出强调官吏的才能。秦简《为吏之道》说:“审民能,以任吏。”这里把任用官吏的要求上了法律。对于在职官吏,秦律规定了名目繁多的考课法,从基层评比到政府机构上计,成绩优的奖励,劣的惩罚,秦的官吏实行“保任”制度。司马迁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蔡泽列传》)这就是说,官吏犯法不仅本人要受惩处,保举人也要“连坐”。秦始皇执法是严厉的。他执政以后,以“为乱”的罪名处置了嫪毐集团,对嫪毐在内的主犯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殉,灭其宗”。对从犯,“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在处理窃葬吕不韦案件之后,秦始皇下令:“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灭其家”、“灭其宗”的刑罚,远远超过了“夷三族”的刑罚,又附加以“籍其门”,株连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了。很显然,对政治犯罪这种广泛的株连和残暴的刑罚,必然写进秦始皇主持编纂的法典中。
三、用法律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这也是秦律的重要内容。在“诸侯争力”的战国时代,秦国有着重视军队建设的传统,他们说:“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秦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把他们的这一主张具体化、制度化,并以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秦简中的《除吏律》、《军爵律》、《中劳律》、《屯表律》、《戍律》、《公车司马猎律》和《秦律杂抄》中摘录的其他一些法律条文,都是有关军队建设的法律。这些法律和条文,对服兵年龄、士吏训练、军事检阅、战斗指挥、军队纪律、功劳计算、爵位子夺、军马饲养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队列中可以想见。如秦国的男子自十五岁傅籍以后,随时皆有被征调入伍的可能。据云梦秦简《编年纪》载,喜这个人在秦王政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入伍。可见,秦国的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绝不止一次,当兵的年龄也绝非自二十三岁开始。正由于秦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才保证有源源不绝的兵源,使秦国的军队数目最多达到“带甲之士百万”,为统一中国准备了重要的条件。统一中国之后,这些法律规定是否失去了作用?没有。因为当时的军事活动没有停止。
四、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封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也是秦始皇编纂的法典中的重要内容。法属于上层建筑,它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一样,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秦简中有不少类似现代国家的经济法规和条款,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均工律》、《工人程》等。这些法律对所有制关系、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种子保管,防止风涝、除虫灭害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关于山林和野生植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上亦下卵)(卵)彀,毋……毒鱼鳖,置阱罔(网)。”(《田律》)对于种子的保管与使用,《仓律》有这样的规定:“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其意是说,留作种子的麦子,应像和谷子一样收藏。还有这样的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作如此详尽的规定,充分说明秦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秦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工商业实行打击。从秦律看,并非如此。对工、农、商之间的地位,秦始皇当然有所区别,而且他把重心放在“重农”上,看来这也是正确的,但不能由此得出打击工商的结论。秦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是相当重视的。秦律对手工业管理、劳动力调配、生产计划以及产品规格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有关规定看,秦非常注意手工业技术力量的保护和使用。在《均工律》有这么一条规定说:“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在《军爵律》有一条规定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前条是说,凡是有技术的奴隶,不要让他们从事一般杂役;后条是说,手工业技术奴隶解放之后,要让他们继续当技术工。所谓“隐官工”,是指在较隐蔽的地方工作的工人。对于商业贸易,在《金布律》等也作了许多规定,这都表明秦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重视。在《史记·律书》也指出,秦王朝重农而不轻商,这正是秦始皇的高明之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律广泛运用“赀甲”,这是一种进步。应该说,运用“赀甲”作为对一般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的惩罚,这是一种进步。当时还有“赎耐”、“赎黥”、“赎迁”、“赎死”等赎刑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广大民众,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有利于贵族、官僚、地主以及富商大贾,因为他们可以钱财抵罪,纵使犯了死罪也可以逃脱惩罚,而贫困百姓一直处于严酷的刑罚之下。
第二节 立法原则
为了有效地制定法律,秦始皇根据秦国的传统,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原则,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法之统一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诸侯们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发布政令。这些政令,数量繁多,变动无常,往往形成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的局面,严重影响到整个法律的统一。由于法令不一,使得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避,也使犯罪者因法出多门而售其奸。针对这一弊端,秦始皇提出“法令由一统”的主张。这一主张,当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有很大差别的,但至少是比以前的“法规不一、政出多门”前进了一大步,这里的“一统”包含了两层意思:
其一,天下统一法度。在《泰山刻石》强调的“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的说法,应该是商鞅变法以来进行法制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秦始皇编纂法典的指导方针。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主张效法自然,统一法令,实行中央集权,以《月令》作为《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的首篇,强调新建的王朝,必须依据十二月令的自然变化,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这里完全是借助阴阳五行家的《月令》的图式,有效地统一行动、统一政令。秦始皇深受吕不韦思想的影响。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便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出一”,指出于最高的统治集团,具体地说,就是出于秦始皇为首的中央政府。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将他主持编纂的法典公布出来,作为天下的统一法律。
其二,法律的协调。法律是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决定了法律规范的繁复性。治理一个统一的大国,不仅需要有刑事立法,以保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还需要有行政立法、经济立法、民事立法,把国家机关的运转、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民事纠纷的调解,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所以,在立法时就得注意各种法律之间的和谐,使立法和执法、守法协调发展。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各种法律之间协调得十分妥帖,但比较的协调还是能够做到的。对此,韩非的老师荀子提出过“以类相从”的主张,他说:“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其意是讲,奖赏和功劳要相称,刑罚和罪行要相称,倘若赏罚的事情有一件没有协调好,或处理不恰当,就会引起全局的混乱。
法之适时性
法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了,法也要发展变化。商鞅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认为古代的政教不同,都是针对当时的形势的。建立法度,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法制。韩非也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这就是说,法律制度不能据守百世不变,它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加以变革、修订。《尚书·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荀子引用了这句话论证了法的适时性,认为随着社会治乱的不同,刑罚就会有轻重的区别,这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时候行厚赏,什么时候立严禁,这是要看整个社会形势的。他说:“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荀子·正论》)荀子认为,在安定的时候犯罪,刑罚必定是重的;在混乱的时候犯罪,刑罚必定是轻的。为什么这样呢?清人王先谦曾作过很好的解释:“治世刑必行则不敢犯,故重;乱世刑不行则人易犯,故轻。”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可以研究,但法的适时性原则的提出本身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秦始皇依据阴阳家的学说,推定秦取代周是以水德代替火德的,正如《史记》索隐所指出的那样:“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削刻,以合五德之数。”在思想上造成一种宗教式的迷信严刑峻法的观念,在实践上“刚毅戾深”,加重了刑罚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法之稳定性
审时度势地制定法律,绝不意味着法律可以朝令夕改,轻易变更。商鞅说:“法立而不革。”(《商君书·靳令》)这就是说,一经变法,就要保持新法的相对稳定性以便取信于民。对此,荀子提出了“定论”的原则,他说:“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荀子·王制》)定论者,确定原则之谓也。这就是说,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原则,让老百姓能够明明白白地知道,在家里做了好事也会在朝廷上得到赏赐,在阴暗的角落里干了坏事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惩处。为什么要考虑到立法的稳定性呢?荀子说:“和解调通,好假道人,而无所凝止之,则奸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荀子·王制》)这里指出了法令不稳定的害处:第一,法令不稳定,人心必多惑。“尝试之说锋起”,如此,法令就失掉了人们的信任。第二,法令不稳定,势必产生前后矛盾,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便可乘隙作奸,而且“奸言并至”。第三,法令不稳定,“则听大事烦”,又多又琐碎,人们不易记清,势必影响法令的执行。荀子的大弟子韩非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还说:“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五蠹》)他甚至把破坏法的稳定性,看成是亡国的征兆。他说:“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几代君主均能保持法的稳定性,秦始皇深受这些思想家的影响,更是以相对稳定性的理论来指导他的立法。《会稽刻石》颂扬秦始皇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所谓“显陈旧章”,就是说,秦始皇在编纂新的法典时,已经把原有的各种单行法规作为重要的内容编进新的法典之中。这也说明,秦始皇在注重法的适时性时,并没有否定要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法的稳定性和法的适时性的统一,这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在内。
法之严肃性
法律一旦公布,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令既出,群臣百姓都不得加以议论,不得讨价还价,不得徇私枉法。荀子说:“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在立法方面要考虑坚持法的严肃性,对待臣下和百姓不能有丝毫的不合理,应该断于一律,不得以感情办事,即使是对待鳏寡孤独的人也应该这样。荀子的弟子韩非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坏)缪,绌羡齐非。”(《韩非子·有度》)他认为法的严肃性既表现在不迁就和不屈从权贵大臣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又不忽视庶民百姓为国出力和贡献。坚持了法的严肃性,就会使最有智慧的人无法辩解,最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反抗。
法的严肃性突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不阿贵”的原则。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拥有立法、司法大权,这就使他具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地位。君主若能守法,就能使法具有权威性。商鞅变法坚持了法的严肃性,处罚了太子的师和傅。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记载了秦昭王坚持法治原则的故事。有一年,秦发生饥荒,许多百姓快要饿死了。应侯范雎为民请命,要求把君主打猎的“五苑”中的野菜和果实收下来,用以救济灾民。昭王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他宁肯丢掉“五苑”中的野菜和果实,任凭灾民自己去采集,也不肯破坏“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的法治原则。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坚持法的严肃性。那些主张恢复分封制的人不满意皇帝“富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的状况。要求分封皇帝子弟及功臣为不同等级的新诸侯。秦始皇不同意分封制而坚持郡县制,并对那些主张恢复分封制的人绳之以法,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大无畏的魄力。
笔者无意于美化秦代的法律。上面说的所谓法的统一性、适时性、稳定性、严肃性,都具有相对的性质,而且文字上的东西往往又与实际具有差距。这一点也是必须指出的。
第三节 宣明法制
秦始皇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重视法令宣传的传统,主张把法律、法令公布于众,并且通过种种方式进行法律的普及工作,使更多的人知法守法,这就是所谓“宣明法制”。李斯曾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秦始皇同意李斯关于学习法令、宣传法令的建议,并明令:“若欲有学法令,以史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明白易知
秦统治者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要叫民众服从法令,必须使法令“明白易知”,人人都能领会其意义。商鞅说:“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这里所说的明白易知,看来包括语言上的尽量口语化以及内容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吻合。这两条秦法都是做到了的。荀子也指出:“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荀子·大略》)又说:“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荀子·宥坐》)他认为刑罚繁多,会使民众迷惑,因而不知所措而堕落,随之而来的是受到制裁。所以说,刑繁没有威信,它不能战胜邪恶。刑罚简省了,就容易深入人心。法令“明白易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
其一,愚智皆知。商鞅认为,“明白易知”,就能够周知万民,无论是愚昧人或是聪明人都能懂得,即“愚智遍能知之”。这里的“愚智皆知”,从上下文看,还包括文化程度高的人能懂,文化程度低的人也能懂,这样,法的覆盖面就广了。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韩非子·难三》)“法莫如显”,这个“显”字,可作浅显解释。也就是说,法令“明白易知”,可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其二,知其本意。商鞅认为,“明白易知”,就能够使人正确领会,不生疑义。他说:“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商君书·定分》)这就是说,如果法令条文含义不易懂,天下人就会议论纷纷,对法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各执己见,造成认识的分歧。
从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材料来看,秦律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是法律条目简单明白,如:
《田律》六条
《厩苑律》三条
《金布律》十五条
《关市律》一条
《仓律》二十六条
《工律》五条
《均工》三条
《工人程》四条
《徭律》一条
《司空律》十三条
《军爵律》二条
《置吏律》三条
《效律》二十六条
《傅食律》三条
《内史杂》十条
《尉杂》一条
《行书》二条
《属邦》一条(以上见《秦律十八种》)
条目简明,固然反映了法律初创时的特点,但也表明秦统治者包括秦始皇坚持“明白易知”的立法原则。
公开颁行
法的宣明性,既表现在法律、法令条文的明白易懂,还表现在法必须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于众。当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编纂完毕之后,吕不韦把它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结果,“时人无能增损者”(《吕氏春秋·序文》)。这完全是以“悬赏”之名,行宣传和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之实。这看来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世界各国凡是成文的法律,都公开颁行,如汉谟拉比法典刻于大理石上。自古以来“著书布天下”的做法给秦始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韩非的思想也给他巨大的影响。韩非认为要使人接受法治,就得把法令制度绘成图画,写成文件公布于老百姓,他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即把法令公开颁布。
秦有定期公布法律的制度和习惯。新出土的《尉杂》律规定:“岁仇辟律于御史。”(《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9页)《内史杂》律要求“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4页)。公布和宣传法律是各级行政机构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新出土的《语书》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过程中南郡守腾颁布的一篇法律文告,属于地方性法规。这份文告突出地阐述了法律的作用,认为“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正)民心,去其邪辟,除其恶俗”。他把公布有关法律、田令的目的明确归结为“令吏人皆明知,毋至于罪”(《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页)。具体说来,公开颁布法令有如下作用:
第一,公开颁布可以使“愚智遍能知之”。百姓就能依据法律的规定,自觉地去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正如商鞅所说的那样:“万民皆知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选择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不选择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躲开祸害,走向幸福,这样就有助于老百姓逐步形成自觉守法的习惯,即所谓“自治”,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第二,公开颁布可以造成“民不敢犯法”的形势。秦统治者保留着许多野蛮的司法实践,如鞭笞于众、刑人于市、悬首暴尸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法的尊严,也是一种法制教育形式。秦始皇对嫪毐、吕不韦集团的处置,又是车裂示众,又是灭其宗,并株连成百成千的人被夺爵迁蜀,就是为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秦始皇自己也公开申明:往后若有人做类似于嫪毐、吕不韦这样事的,皆“籍其门”,并和此次事件作同样处理。孟德斯鸠说:“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在专制国里,应该是恐怖。”(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9页)秦始皇运用这种恐怖手段教育民众,使民众知道法律,以为这样会造成“民不敢犯法”(《商君书·定分》)的形势。
第三,公开颁布可以使官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商鞅说:“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商君书·定分》)其意是说,法令公开颁布,让老百姓都懂得法令了,这样一来,官吏明明知道老百姓都懂得法令,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来对待老百姓。这种做法,看来好像是为了老百姓,其实,用法来整顿吏治,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达到更好地控制民众的目的。
设置法官
所谓“宣明法制”,就是主张把什么是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怎样的刑罚;什么是应该受到奖赏的行为,应该受到多少赏赐,都要明确无误地写进成文法中。同时,还要广泛地加以宣传。就是在这个“宣明法制”思想基础上,秦始皇在朝廷、郡、县等各级行政机关中普遍设置法官或法吏,负责法律的公布、解释、宣传和实施的任务。秦统治者对于法官或法吏的要求很高。据《商君书·定分》篇说,这些人必须精通法律,“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所谓“忘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违背。这就是说,各个主管法令的人如果胆敢违背执行法令条文的某项规定,就各按照他们所违背的法令条文的某项规定来办他们的罪。这条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不仅法官或法吏要掌握法律和法令,就是一般的官吏也必须努力学习法律和法令。据南郡郡守腾说,区分“良吏”与“恶吏”的重要标准就是视其能否明了法律。他在《语书》上说:“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律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7页)如果不努力学习法律、法令,就不能继续为官。
秦统治者特别强调,对法令的解释要确切,不得以己“心意议之”,不然“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商君书·定分》),为了准确地解释法令,商鞅作了种种严格的规定。例如,解释法令时不得删改,“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如果有人任意增减一字,就是死罪;又规定,“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即执法的人如有迁移或死亡,当新的执法人上任前,就派一人向他诵读法令条文,给他定出规程,限期要他通晓法令条文,若不合规程,就用法令办他的罪。这看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其实这样做正是为了强化执法系统,而且使这种执法系统代代相传。
商鞅还特别强调主管官吏要首先学习和领会法律与法令,指出“郡县诸侯一受赍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即谓各级官吏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就得学习。他说:“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商鞅还规定,当民众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条文时,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准确地告诉他们,即谓“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商君书·定分》),并把所问的法令条文写在一个一尺六寸长的“符”上,还注明年、月、日、时。在讲解之后,就把“符”的左片给予询问者,把“符”的右片装在木匣里,藏在屋里,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日后作为凭据,用以证明所回答的法令条文是否准确。还规定:“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就是说,如果主管官吏没有及时、准确地进行讲解,等到询问者犯了罪,所犯的正是所询问的那一条,那么,就按照询问者所询问的那一条款所规定的罪来惩办主管官吏。
官吏不仅要认真学习法律,准确解释法律,而且要依法办事。从新出土的秦简上看,秦律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法律答问》载:“何如为‘犯令’、‘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1—212页)这就是说,法律规定了的就要去做,法律规定不要做的就不去做,这是在法律上为官吏规定的依法办事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法律义务,有法不依,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法律答问》指出:“废令、犯令,遝(及)免、徙(调任)不遝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页)只要“废令”或“犯令”,即使已被免职或调任,也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亲自讲法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历代君主都注重法律宣传和法律教育。睡虎地新出土的秦简证明秦始皇继承了这种传统,注重法的宣传和教育。秦始皇时期的《尉杂》律规定:“岁仇辟律于御史。”就是说,负责法律宣传教育的官吏,每年都要到御史处去核对刑律。《内史杂》律规定说:“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其意是说,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遵用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宣传法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荀子就曾说过:“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荀子·君子》)还说:“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荀子·王制》)就是在这个“宣明法制”的思想上,秦统治者广泛地宣传法令。县官要讲法,郡守也要讲法,南郡郡守腾的《语书》就是一篇进行法律教育的文告。秦始皇更是带头讲法,他在巡视各地的重要活动就是宣传法律和法令。让所有的官吏都讲法,目的是为了首先使他们守法。
在《泰山刻石》说:“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就是说,要广泛宣传法制,使全国臣民完全领会,并按法律法令办事。
在《琅琊台刻石》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就是说,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就有了办事的准则;确定法令,消除疑点,使大家都能遵守而不触犯。
在《芝罘刻石》说:“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就是说,全面地推行法治,使之永远成为治理天下的准则。
在《会稽刻石》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就是说,秦始皇亲自执政以后,开始确定了崇尚刑名,明白地宣布继承秦国以往的规章制度。
经过朝廷君臣和官吏们的努力,秦律大大深入人心,当时秦始皇在《琅琊台刻石》中说:“驩欣奉教,尽知法式。”认为百姓懂得了法律,知道了守法和违法对自己的利害得失,就会乐于接受教化,都能通晓法律制度。
第四节 “事皆决于法”
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实行法治的原则。上至军政大事,下至民众日常生活,都有法律的限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讲到秦始皇法律思想的特点时,司马迁说:“事皆决于法。”秦始皇把法看成治理国家唯一有效的工具。
法网严密
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封建社会的种种法典往往只是封建帝王和封建官僚意志的摆设品,而秦帝国却是法网严密,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系列成文法典,它所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秦始皇主持编纂的法典是秦国法律的总汇。前文已述,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代。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唐律疏义·序》)。此后,秦国统治者根据社会斗争的需要,不断添加新的法律。到秦始皇时,见于文献记载和新发现的秦简材料,仅律目就有三十余种。秦律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官吏的任免、军政、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司法行政、监狱管理、徭役戍边、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宗教祭祀、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正如秦始皇在《泰山刻石》中所说的那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秦始皇颁行的法律不仅规范类型较为完全、结构较为严密,而且确定性程度相当高,为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明确指出应该做什么、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要求做什么,并且也有对违犯规范的后果作出法律制裁的具体规定。
秦始皇制定的一系列限制性法律的阶级烙印特别明显。
秦始皇限制百姓通行自由,在全国各县、各交通要津设置关卡,保证合法通行,限制非法交通,这是战国时代留下来的,统一之后仍然保留这条法令,只有经许可持有证件者才能通行。当时的通行证件有的叫“验”,有的叫“传”,也有的叫“符”。没有“验”既过不了关卡,又找不到住处。商鞅逃亡时就亲自尝过这条法律的苦头。由于限制通行,就必然有伪造通行证件的人,于是又颁有禁止伪造证件的法令:“发伪书,弗知,赀二甲。”(《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道:“今咸阳发伪传书,弗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知者当皆赀。”就是说,有伪造通行证件的,如果第一关没有发现,传到其他关口都未发现,就都负有行政责任。
秦始皇还限制百姓的言论自由。在秦律中把对君主人身的任何非议和侵犯,都属严重政治犯罪,必须处以族刑。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当项羽观看秦始皇有威仪的车驾时说:“彼可取而代之。”其叔父项梁连忙掩其嘴说:“毋妄言,族矣!”说明秦始皇时,只要有蔑视皇帝的言论,就构成“谋反罪”,必须处以夷三族的刑罚。秦始皇还下令禁止不同学派的存在,宣布:“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完全是对民众言论自由的绝对禁止。贾谊指出,在秦始皇的法网下,“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
行赏告奸
秦始皇为了实行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将六国的百姓重新编入户籍,且较原先更为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把连坐法作为司法的普遍原则,对同居、同里、同行政组织之内的成员依法规定了连带的刑事责任。在这个范围内,他人的犯罪行为也被看成是他自己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告发,就分别情况给予相应的刑罚。依据《傅律》的规定,在徭役上弄虚作假,“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3页)这样,就把第三者对犯罪行为的揭发控告权利,看成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法令,秦始皇还普遍实行“赏告奸”的原则。在讲到“赏告奸”的时候,韩非子说“告之者其赏厚而信”。厚到什么程度呢?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斩一敌首,爵一级。而爵一级相当于粟一千石的价值,恰是三万钱,一个普通劳动者连续十年不休息方能赚得这么多的钱。
既颁连坐法,又下告奸令,这就有力地控制着民众的行动。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把第三者的犯罪行为看成是他自己的犯罪行为。例如《法律答问》载:“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8页)在这里可以看出,当丈夫犯有流刑,其妻也被看成犯有流刑的罪犯,至少是被看成是应受流刑处罚的人,因此才有“妻先自告”的提法。《法律答问》又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4页)这个案例和问答说明,丈夫有罪,妻能够履行告发即自告的义务,不但自己可以免于刑事追究,而且保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诸如娘家陪嫁的奴婢、衣服、器具等。反过来,如果是妻子有罪,丈夫能够告发,不但可以保住自己不受刑事追究,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财产。不仅鼓励夫妻之间互相告发,而且鼓励父子之间互相告发。若不告发的还要受到严惩。这也就是人们评论秦始皇时,指责其“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原因。
秦始皇不但奖励百姓揭发犯罪,而且奖励百姓侦缉和追捕逃犯,其赏金是高额的。《法律答问》说:“捕亡完城旦,购几何?当购二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9页)还说:“夫、妻、子五人共盗,皆当刑城旦,今甲尽捕告之,问甲当购几何?人购二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9页)只要是捕获了确实够“完城旦”或“刑城旦”以上罪的犯人,每捕捉一人,就奖给黄金二两,捕捉五人就奖给黄金十两。除赏金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法律答问》说:“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所捕耐罪以上得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7页)只要捕到应处耐罪以上的逃犯,就可以取得逃犯随身携带的钱财。也正因为有这样高额的奖赏,在新出土的秦简中有关百姓捕捉逃犯的记载就有多例。奖也罢,惩也罢,无不是为了控制民众、镇压民众,这就是秦始皇法治的阶级本质。但若仅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看,他在推行法治过程中的不少规定和要求,作为历史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以吏为师
在刻石中有言:“秦圣临国,始定刑名”,“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把一切法律制度都说成是秦始皇开始制定的,这未免夸大其词了,但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法治倒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秦始皇之所以主张法治和注重法律教育,是由于他相信“人性恶”的学说。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恶焉”,人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由此出发,荀子主张用法来改造人性,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荀子·性恶》)韩非进一步发挥老师的观点,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八经》)还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韩非子·五蠹》)这里的所谓“三美”,指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教育。韩非认为这些教育没有根本的作用,唯一有用的是法律教育,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荀子的思想通过李斯和韩非子影响了秦始皇,使秦始皇接受了荀子的“人性恶”的学说。秦始皇在巡游时公开宣称:“禁止淫泆,男女絜诚。”(《会稽刻石》)认为,对于纵欲放荡的行为只有采取禁止的办法,才能使人的品德高尚起来。在秦律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法律和刑罚可以“矫正民心,去其邪辟,除其恶俗”(《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页)。这也就是说,只有使用刑罚和法律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恶性,才能预防犯罪和消除犯罪。
秦始皇在全面实行法治的实践中,把以法纠恶的观念发展到极端。思想上的“唯法论”,必然导致在政治上“以吏为师”。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专任狱吏”。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都得不到秦始皇的信用,唯独狱吏受到特别的信用,即谓“狱吏得亲幸”。李斯曾以廷尉的身份参加朝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由廷尉晋升为丞相。赵高出身虽然卑贱,但由于“通于狱法”(《史记·蒙恬列传》)被任命中车府令,成为秦始皇的亲信,又因赵高“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又得到秦二世的特别信任,最后晋升为丞相。狱吏成了秦始皇推行法治的骨干力量。
其二,取缔“私学”。沿着“唯法论”的道路走向极端,必然导致依法取缔私人的一切其他教育设施。秦始皇指出:“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认为,人民如果喜欢私学,这就影响了法教。“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于是秦始皇下令取缔一切“私学”,规定“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而且只能“以吏为师”。
第五节 专任刑罚
“事皆决于法”,这是秦始皇统治时期法律制度特点之一,特点之二则为“专任刑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秦国的酷刑推广到新占领区域,史载:秦始皇兼吞六同之后“专任狱吏”(《史记·秦始皇本纪》)。
轻罪重罚
秦始皇不相信人们经过道德教育可以不犯罪,仅仅相信经过刑罚人们才不敢犯罪。《后汉书》集解也指出,秦王朝认为实行“轻罪重罚”,才能消除犯罪。其理论根据是什么?还是韩非之说。韩非认为轻罪重罚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他说:“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韩非子·六反》)在韩非看来,刑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犯罪者本人,而是在于预防犯罪。为了防止犯罪,必须轻罪重罚。他认为,把重刑加在犯罪的“盗贼”身上,要在尚未犯罪的“良民”心灵上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害怕刑罚而不敢犯罪。韩非还从“性恶”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韩非子·六反》)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很会为自己打小算盘,任何事物都要计较得失。实行轻罪重罚,犯罪者得到微不足道的好处,却要受到严峻的处罚,从而使自己蒙受几倍于犯罪所得的损失,这样就会使犯罪现象消除。与此相反,重罪轻罚,犯罪者得到巨大的好处,却受到轻微的刑罚,即使是扣除因受刑罚而蒙受的损失,从犯罪中还能获得好处。这样,民众就会因为羡慕这种好处,而傲视法令,犯罪现象就会不断发展和扩大。
秦始皇正是从韩非这种理论出发,坚信只有重刑才能制止犯罪。在秦律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如,“为人妻去夫亡”,即妻背夫逃亡,秦律规定“当黥城旦舂”。(《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3页)把“妻去夫亡”宣布为犯罪,不问情由,一律处以“黥城旦舂”的重刑,也属轻罪重罚。
又如,“同母异父相与奸”,秦律规定:“弃市。”(《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5页)同母异父的近亲通奸,也属于通奸行为,秦律处以最严厉的“弃市”,当属轻罪重罚了。
又如,“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刑德》)。盗一匹马就处死刑,盗一头牛就比常刑加重,这显然是轻罪重罚。
又如,秦律规定:“誉敌以恐众心者戮。”(《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2页)如果把说敌人几句好话的行为,都认定为“誉敌”,并处以“戮”刑,问题就严重了。如果是“投敌”、“倒戈”、“反叛”又怎样处罚呢?至多也不过是“戮”刑而已,这岂不是轻罪与重罪同罚了吗?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新颁发的秦律,如“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弃市”、“失期者斩”的刑罚,这不仅是轻罪重罚的问题,有的完全是无罪滥罚了。
轻罪重罚,从秦始皇的本意看,是为了加强统治,强化法治,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破坏了法治,使法律原则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再说,轻罪重罚的结果使得民怨沸腾,造成了民众的反抗,这看来是秦始皇始终所未料到的!
扩大株连
老百姓在新落地的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句,借以威吓他。秦始皇采用连坐法,扩大了株连的范围,“尽取石旁居人诛之”。这样不但把刑罚强加在被认为有犯罪行为的人身上,而且也把刑罚强加在同罪犯仅有法定的连带责任关系而本人并无犯罪行为的人身上。扩大株连范围,这是秦始皇“专任刑罚”的另一个表现。株连范围有家属连坐、邻里连坐、部门连坐等。
家属连坐。所谓“家属连坐”,就是依法规定同户人负有连带的刑事责任,户内有人犯罪,其他人有告发的责任。如果不履行这种责任,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给予法律规定的刑罚。《法律答问》引律说:“盗及诸它罪,同居所当坐。”例如:“宵盗,赃值百一十,其妻、子知,与食肉,当同罪。”引律又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4页)明确规定,如果丈夫有罪,妻子能在事前告发,就可以免受株连,而且妻子本人的“臣妾、衣器”都不没收。
邻里连坐。所谓“邻里连坐”,从新出土的秦简来看,邻里连坐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同伍连坐,即一家有罪,四邻必须告发,如不告发,就受到株连。《法律答问》中有问:“何谓四邻?”回答说:“四邻,即伍人谓也。”(《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4页)另一方面是里典连坐,即居民犯罪,居民组织的首脑必须告发,如不告发,就受到株连。秦始皇时,居民组织的首脑称“典老”。《法律答问》有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同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3页)这里说得很明确,一家受害,同伍和里典、伍老负有救护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被害时,四邻确实不在家,可以不论处。里典和伍老不在家,连坐的刑事责任可以不追究,但是行政上渎职罪却不能免除。
部门连坐,也称作职务连坐。推行于军队的连坐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同伍连坐,即把同伍的战士编为一伍,其中一个逃亡,就加刑罚于其他四个人。二是上下级连坐:“战及死吏,而轻(刑)短兵。”就是说,在打仗时,指挥官战死的话,士兵就要受到刑罚。推行于政府官员的连坐法,随着株连面的扩大,其限制也明确,一是依据隶属关系的远近规定不同刑事责任的法律,二是以知情为条件。职务连坐法也适用于人事任用方面,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据新出土的《编年纪》的记载,应侯范雎就是根据这项职务连坐法被处死的。
明代进士赵用贤指责秦政:连坐法严格地迫使父子、夫妻、亲友和上下级之间互相告发,这就造成了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气氛。难怪周围的人认为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韩非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连坐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并编织了一套连坐法的理论。他说:“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窥)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志),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韩非子·制分》)很清楚,连坐法就是利用人们避害趋利的自私心理,强迫人们相互监视、相互告发,企图由此达到预防犯罪和揭发犯罪的目的。秦始皇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控制民众的。
连坐之法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极大地毒化了人际关系,伤害了人们的感情,对民族自信心的培养和民族整体观念的养成都极为不利。在这点上,秦始皇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对此,他应负历史性责任。
施行酷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以后,“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后来,秦始皇于咸阳又“坑”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此“坑”就是“生埋”,是一种酷刑。施行酷刑,这是秦始皇“专任刑罚”的第三方面的表现。
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刑罚,是由死刑、肉刑、耐刑、笞刑、徒刑、流刑、赀刑等组成。秦始皇信奉商鞅、韩非等人的重刑理论,就不可避免地从历史寻找并继承许多残酷的刑罚。
从《史记》的记载上,秦律有“车裂”、“腰斩”、“戮尸”、“枭首”、“坑”、“赐死”六种处死的刑罚。从新出土的秦简中看,秦律的法定死刑有“戮”、“磔”、“弃市”、“定杀”、“生埋”五种。
戮刑——《法律答问》解释说:“生戮,戮之已乃斩之之谓也。”(《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3页)就是先活着刑辱示众,然后再斩杀之。还有一个“戮尸”的刑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反叛者已在战场上被杀死了,未经过法定程序,因而须补以“戮尸”。戮尸是戮刑的一种。
磔刑——碎裂犯人肢体的死刑。这种酷刑也是从奴隶社会的刑罚中继承下来的。“车裂”即为磔刑。秦始皇施于嫪毐的刑罚就是车裂。
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在街头。《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定杀——投入水中活活淹死的刑罚。《说苑》有秦始皇“囊扑二弟”之说,即把太后私生的两个儿子放在“囊扑”中,然后丢到河中淹死。
生埋——活埋的刑罚,又称为坑刑。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即为生埋的酷刑。
枭首——斩首高悬以示众的刑罚。秦始皇在处理嫪毐叛乱案时,对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处以枭首。
腰斩——是秦执行死刑的主要刑罚。商鞅变法时规定了这样一条法律:“不告奸者腰斩。”李斯就是被处以腰斩。
族刑——是在适用死刑的对象方面扩大刑罚的范围,不仅对有犯罪行为的人执行死刑,而且对与犯罪者仅有血统关系而无犯罪行为的人执行死刑,以加重刑罚的严峻程度。秦始皇对荆轲“湛七族”,后来又下令:“以古非今者族”,“诽谤妖言者族”。
从其他资料看,秦还有“凿颠”、“抽胁”、“镬烹”、“绞”等处死的刑罚。这些酷刑都是从以往奴隶社会的野蛮刑罚中直接继承过来的,有的还加以发展,使其变得更加残酷和野蛮。肉刑就是一种残害人身的极其野蛮的刑罚,先秦时期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也反对肉刑而主张“象刑”。荀子不同意这种主张,他提出两条理由:其一,肉刑是历代帝王所使用的。荀子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其二,肉刑是现实社会的“治国之法”。荀子认为惩罚残暴凶悍的人,这是国家最安定的表现。他说:“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荀子·正论)在荀子看来,肉刑是维护封建统治所不可缺少的手段。荀子的这些思想通过李斯、韩非的介绍,而使秦始皇信奉残酷和野蛮的肉刑。
宫刑——又称腐刑,这是残害男子生殖器,破坏妇女生殖机能(一说将妇女禁闭于宫中)的刑罚。这是仅次于死刑的最重的肉刑。在秦始皇身边的赵高就受过宫刑。
斩左止——为刖刑的一种。有的说,秦需要大批手脚齐全的刑徒筑长城、治驰道、修阿房宫和骊山陵而“很少适用刖刑”(栗劲:《秦律通论》,第246页),这仅仅是一种推论。既然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为什么又坑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呢?事实上秦始皇没有这样来考虑。《盐铁论·诏圣》篇说秦“断足盈车”。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并非耸人听闻的言词。
劓刑——这是割掉鼻子的酷刑。
黥刑——墨刑的异称。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秦始皇在《焚书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耐刑与髡刑——用剃光头发和胡须的刑罚来代替宫刑,于是产生了髡刑,保留头发的完好,只剃去鬓须,就成耐刑。秦始皇为了防止修筑长城的服徭役者和犯人逃跑,强行对他们“髡头”。
“宫其器”、“刖其足”、“劓其鼻”、“墨其面”和“髡其发”五种肉行之外,还有笞刑、鋈足、饿囚等刑罚。
秦始皇的明法定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有其一定的进步性。它对普及法的观念,完善法制体系,提高法在整个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秦始皇的明法定律毕竟是从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的严刑峻法及所推行的那一套轻罪重罚、连坐等法治手段,都是不足为训的,是民族文化中的糟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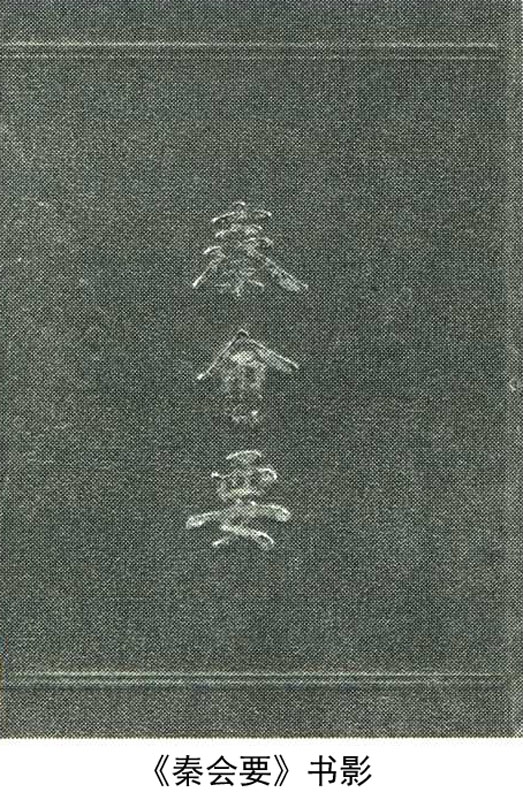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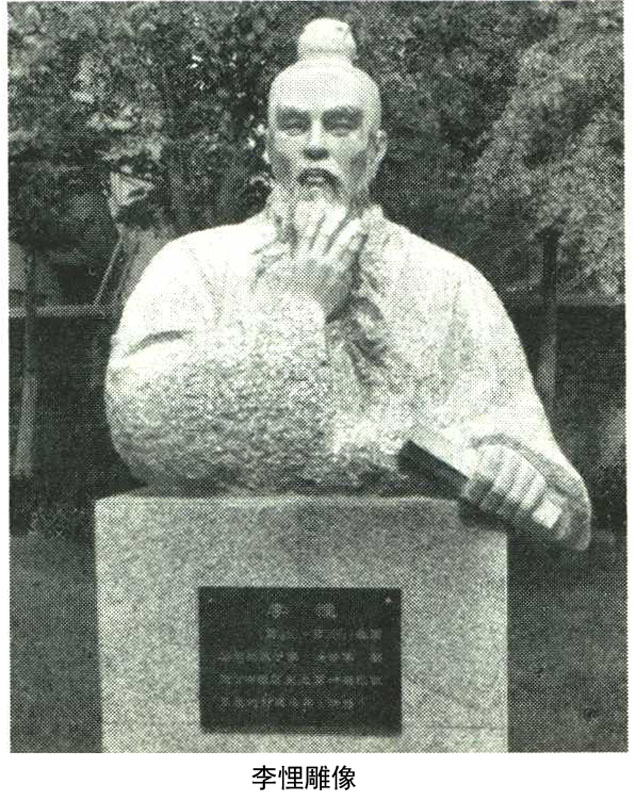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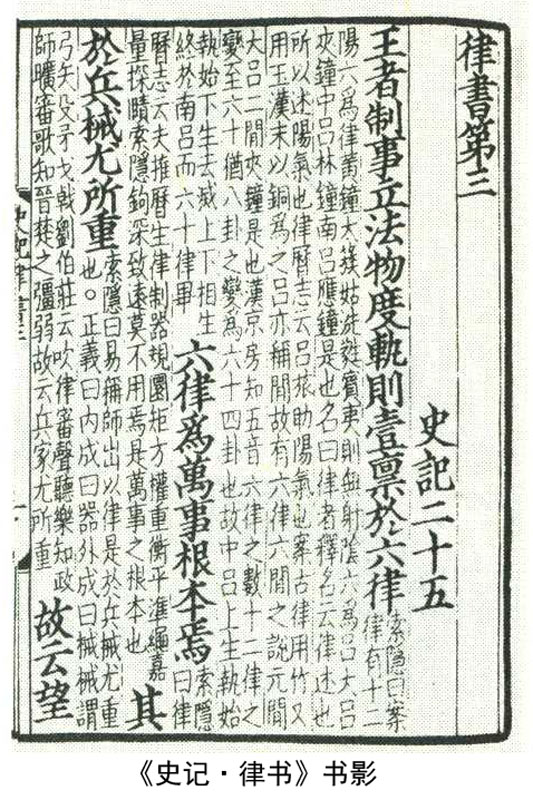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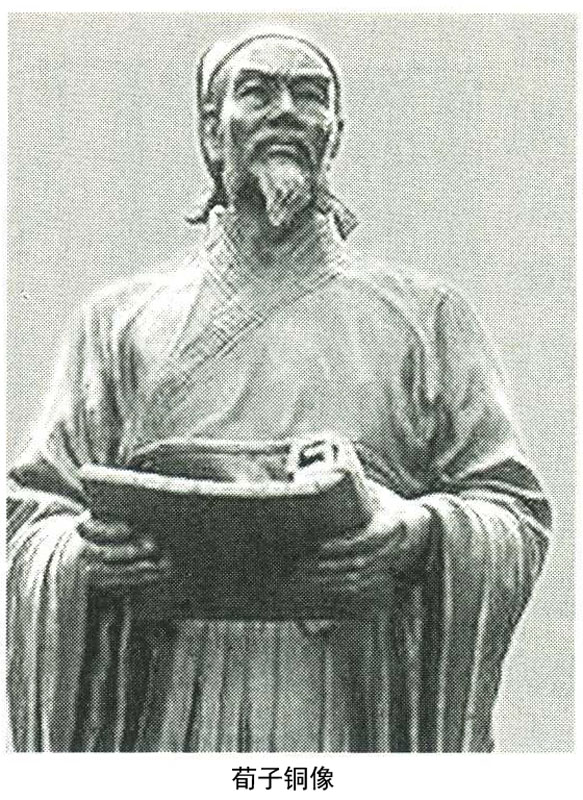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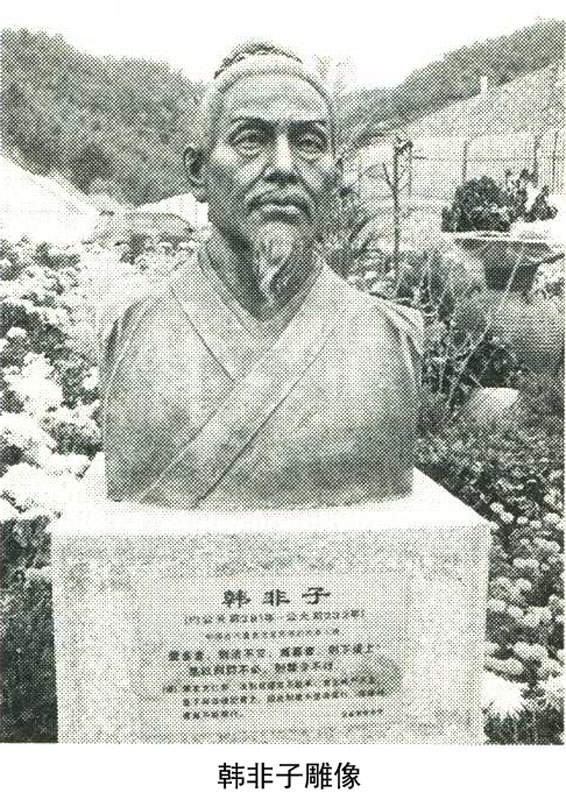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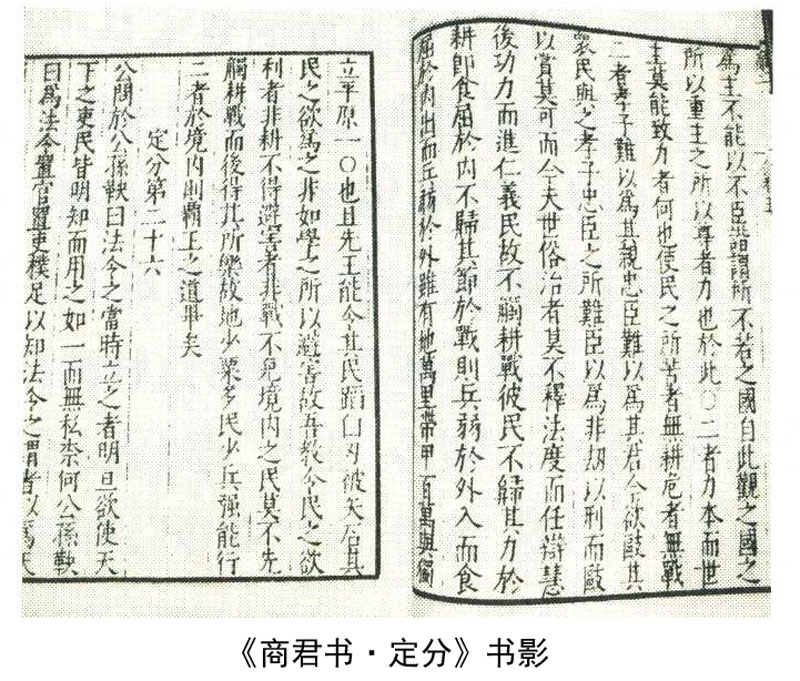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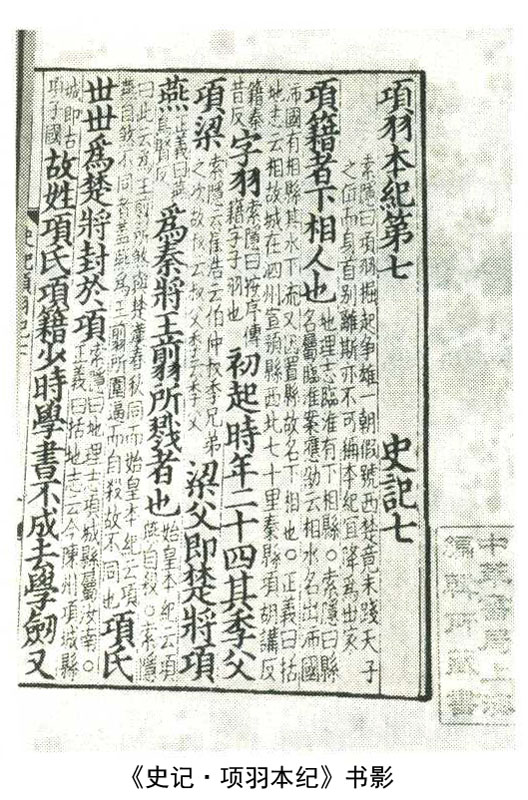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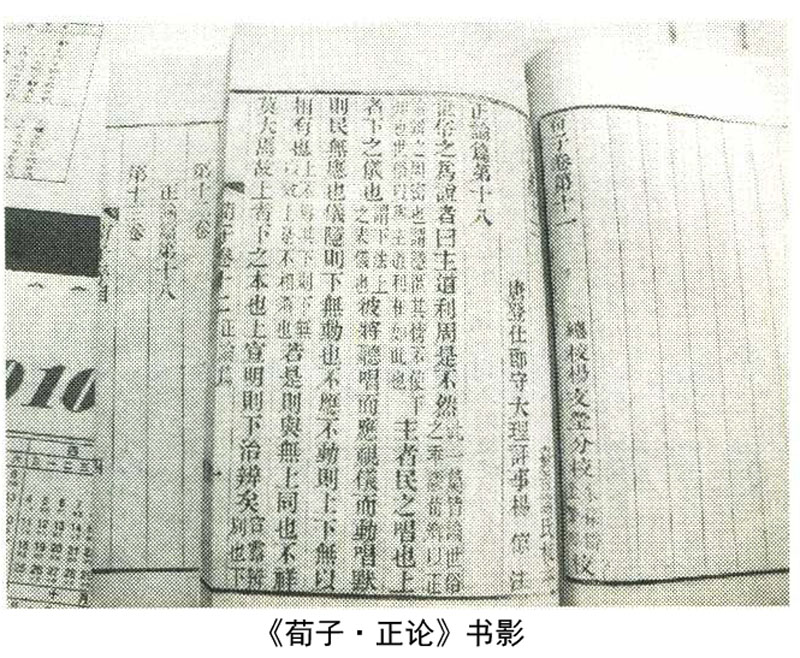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