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产生及发展——敦煌考古与敦煌艺术研究
作者:刘进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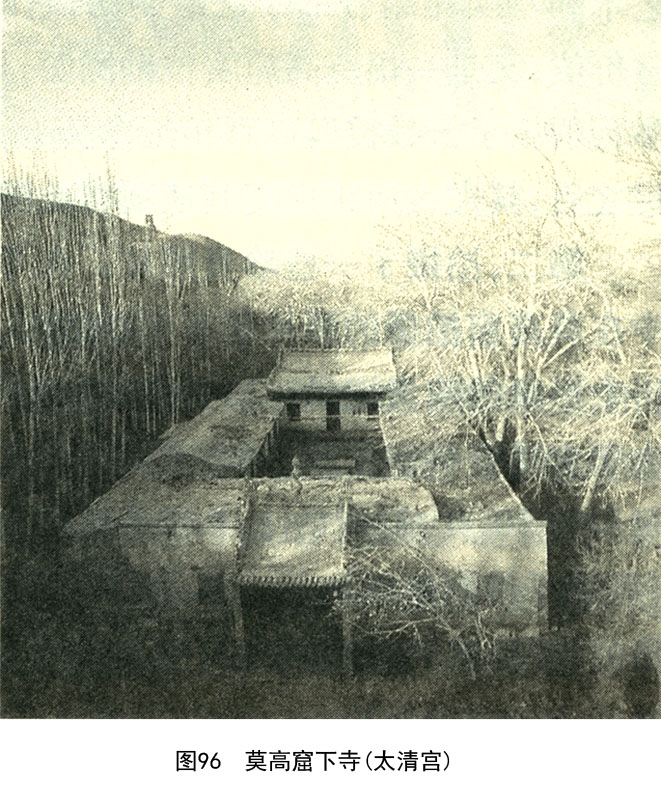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一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也在一步步后退,先是从南京退居武汉,后又从武汉进一步退居重庆。相应的,沦陷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纷纷转入西部,以前不大为人关注的西南则成了各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汇聚的宝地。随着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就成了抗战的大后方,自然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就成了时人关心的新课题。要开发西北、建设西北,首先就要了解西北,而要了解西北,就需要考察西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开赴西北。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敦煌的关注及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藏经洞文书。而这一阶段,不论是由官方组织的考察团,如“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还是官员、个人的考察、视察或朝圣,如于右任、张大千等,乃至奉命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及其追随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见长,他们关注的也主要是石窟保护和壁画艺术。
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及考察,尤其是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全国各地的展出,向世人宣传了敦煌,也使世人了解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而他们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临摹、展览、宣传,对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一、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抗战后方的建设,需对有关历史遗迹及边疆史地进行考察了解。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便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团考察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其中考古工作仅限于甘肃和宁夏地区的一部分。
据向达《西征小记》记述:“三十一年(1942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有西北史地考察团之组织。考察范围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时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①由此可见,当时的学术考察,也有一定的现实目的,在抗战的艰难时期,想开发大后方,为现实服务。
1942年4月中旬,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即在重庆组建: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炽任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兼领队,向达任历史组主任,李承三兼任地理组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吴静禅任植物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劳干为历史组组员兼文书,历史语言所的石璋如为历史组组员兼会计,地理所的周廷儒为地理组组员兼事务。5月4日,全团成员到达兰州后,各组分别进行工作。而向达先生由于当时正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并要赴重庆安排家属等,故迟至10月9日才到敦煌。正如《西征小记》所述:“余应研究院之约,奉校命参加考察。以滇西变起仓卒,交通艰阻,迟至八月方克入川。九月下旬自渝抵兰,十月初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以抵敦煌。”②
9日中午到达敦煌后,向达先生即于下午4时启程赴莫高窟,晚8时到达后住于中寺。从此在敦煌一带考察生活达九个多月。《西征小记》记其事曰:“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间者凡九阅月。中于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访阳关遗址,三十二年三月旬往游大方盘、小方盘,探玉关之胜迹,访河仓之旧城。其年四月复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访玉关,然后东行以归敦煌。五月至安西,礼万佛峡诸窟,历时一周,复返千佛洞。七月遂东归返川。以在敦煌历时稍久,见闻较多。”③
向达先生到达千佛洞的第二天(10日),就与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即王子云率领的考察团)成员以及张大千会面,并由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游览了莫高窟。
随后,向达就赴南湖一带考察,他考察了西千佛洞、寿昌城遗址、古董滩、阳关等地。23日回到莫高窟后,即潜心于洞窟考察,同时还做详细的记录。到了11月初,向达已对莫高窟的三分之一洞窟做了详细考察。有感于张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剥离壁画,他用三天的时间写成了在敦煌学和莫高窟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他将此文寄给傅斯年,请其推荐发表。该文经傅斯年推荐,以“方回”为笔名,在《大公报》1942年12月27~30日连载刊登。据向达先生1943年3月9日从莫高窟写给王重民先生的信中说:弟自去岁“十一月初,草《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长万余言。以客中乏书,因寄李庄曾小姐处,请其校阅一遍,由孟真先生介登渝《大公报》”④。
在撰写和寄送《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同时,向达还给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中央博物馆的曾昭燏写信,既汇报西行考察情况,又淡及张大千破坏壁画及千佛洞保护问题。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向达写道:“最近骝先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嘱暂留此,不必亟返,西北工作,尚待继续,正拟明年计划云云。达拟在此再留三月,将千佛洞逐窟作一详细记录,于每一窟之壁画塑像名目、保存情形、前人题记等一一备录,整理蒇事,往安西万佛峡一游,再访布隆吉遗存洞窟,然后东归酒泉,以待后命。”⑤在给李济、傅斯年的信中也说:“目前计划,拟普看三遍,将各窟壁画、塑像保存情形,供养人题识诸项,逐窟详予纪录。”⑥
随后,向达对莫高窟诸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又对敦煌周围各地如西北长城沿线的大方盘城(河仓城)、小方盘城(玉门关)等进行了考察,抄写了一些当时能在敦煌见到的文书。
7月初从敦煌东归,20日到兰州,26日赴重庆,结束了第一次敦煌考察。
向达的第一次敦煌考察,固然有巨大的成绩,但也有许多的无奈。在向达看来,他参加考察团,乃是代表北京大学,而考察的组织者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只有历史组是与北大合作,而北大也只有向达一人参加,再加上当时可能没有形成文字的协议,而向达又由于诸事迟到约四个月。在考察团及历史组诸位心中,就没有把向达看成考察团的成员,甚至没有给向达留下必需的经费。1943年3月5日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不幸者,西北史地考察团之组织,虽出自研究院与博物院,而历史组则为两者与北大合作之事业。而达之来,亦为代表学校,并非以个人资格参加,此种情形,最少北大方面、有此谅解。惜呼考察团自组织以至出发,于此点未尝正式声明;历史、考古两组中人,于此中经过,尤其未能明了。”⑦在3月9日给王重民先生的信中也说:弟已致函北大,如果还要我留此工作,“唯须将考察团历史考古方面与北大合作,先行议妥,声明在案,而以弟为代表参加工作,如此始可考虑。”⑧后来,向达在与历史所的同事谈到当年敦煌的考察时,也说“还有一些人事上的不愉快”⑨。
另外,当向达于1942年到达敦煌时,张大千一行和王子云率领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在千佛洞。张大千等人居住在莫高窟上寺,向达住在上寺隔壁的中寺,王子云一行则住在稍微远一些的下寺。
从现有资料看来,向达与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与张大千一行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其原因可能与前述向达对敦煌艺术的看法,尤其是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有关。
当傅斯年将向达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交《大公报》发表时,虽然用了“方回”的笔名,但从文章的内存,尤其是傅斯年在按语中所说“此君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的话中,人们不难知道作者是谁。当张大千得知此事后,双方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有的朋友甚至为向达的安全考虑。向达的文章发表不久,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在3月中下旬致电敦煌县长:“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⑩
194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又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这次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目的,和上次一样,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外,主要是为当时的西北建设服务,以考察“所得供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因此,除了历史考古组外,还有地理组、地质组、矿产组、动物组、植物组等。
早在第一次考察时,向达就曾极力推荐夏鼐为第二次敦煌考察的负责人,但“西北科学考察团”任命向达为考古组组长,夏鼐、阎文儒为成员。夏鼐虽然是考古学科班出身,但他对向达的道德文章非常敬佩,而阎文儒(述祖)又是向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三人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考察组原计划1943年9月出发,临行前由于夏鼐先生生病而不得不推迟了半年。1944年3月21日,向达由重庆飞抵兰州,夏鼐乘下一航班于4月4日抵兰(由于飞机座位有限的缘故),开始了考古组的工作。17日,向达、夏鼐即赴河西考察,5月12日,考察团另一成员阎文儒赶到,他们在酒泉汇合。14日,又从酒泉启程西行,经玉门到安西,19日早晨抵敦煌,22日参观千佛洞,30日移住佛爷庙工作站,31日开始发掘魏晋墓葬。
第二次敦煌考察,向达的时间更少,只有四个多月。当佛爷庙西区墓地的发掘工作结束后,向达即于10月19日启程东归。31日,夏鼐、阎文儒由敦煌前往西北汉长城遗址考察,发掘了小方盘城北的汉代遗址和大方盘城东南土台,获得汉代简牍若干及晋泰始十一年乐生题记石。12月6日,夏鼐、阎文儒赴安西、酒泉考察。1945年2月17日回到兰州,随后又曾到武威、民勤、张掖等地发掘考察。
第二次敦煌考察,除了对阳关、玉门关、河仓城等著名遗址的考察外,还在墓葬的发掘方面做出了成绩。敦煌附近除了故城遗址外,还有许多古墓,如罗盈达墓志铭、阴善雄墓志铭、索法律窟名等,均记其葬地。如能找到这些墓葬,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大收获。向达在《西征小记》中曾说:“三十一年冬始至敦煌,即闻人言佛爷庙至千佛洞中途戈壁上有砾石堆甚多,疑是古代墓葬遗址。其后数次往观,则自佛爷庙以东此种砾石堆累累皆是,迤东以至于新店子,长达三四十里。大都中为砾石堆成之小阜,高者及丈,低则几与地平,为数三五不等。”(11)“就其形式观之,与斯坦因、黄仲良(文弼)诸人在高昌所发掘之六朝以及隋、唐古墓绝相类似,则其为古代之墓葬群,盖无可疑也。”(12)在1943年1月13日致曾昭燏信中,向达先生说:”近在千佛洞至敦煌中途戈壁上,见到古代墓葬群百余,大都作长方形……达以为此是唐代沙州人墓地,毫无可疑。盖唐代沙州,距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其西北,适当今敦煌人称为佛爷庙之地,至今其地废基颓垣,弥望皆是,迤逦长达数里。按诸距千佛洞里数、方位,俱甚相合,而墓葬群即在古沙州东南约五里左右,南为鸣沙山,不能营葬地,则此必是墓地也。”(13)向达的这种推论被考古组1944年的发掘所证实。
1944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夏鼐、向达、阎文儒在敦煌城东约9公里的老爷庙发掘了一唐代墓葬,内容比较丰富。这个墓葬的墓门内两侧站立着一对高1.2米的武士像,他们都高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叉在腰间,威风凛凛,表示门禁的森严。武士像的雕塑艺术也很精良,脸部的表情威严而生动,可以和千佛洞盛唐洞窟中的武士像相媲美。在武士像稍后的右方,站立着一对骆驼,高达0.85米,各有一个驼夫牵引着。再向后便是放置木棺的平台,台前排立着大批的小陶俑,共41件。其中骑士俑16件跨着骏马,好像一队骑兵,排立在平台前的左边。旁边的空隙放置一匹大陶马,马首向外,姿态生动,其旁站立着三个马夫俑。做牵马的姿势。这些马夫和驼夫都身穿大翻领的狭袖短大衣,足穿长统的黑靴子。其中的两个不仅穿胡服,而且高鼻圆目,发辫盘在头上,可能血统也是胡人。此外,还有带金箔的铜片、开元通宝钱、玻璃细条和玻璃珠等。从其内容判断,它是盛唐时代的墓葬。(14)
1944年10月31日至11月15日,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敦煌驻军的一位营长陪同下,又对敦煌汉长城进行了考察与发掘。11月2日,他们赴古董滩考察,“滩在沙丘中,时露绳纹或刀削纹陶片、小榆荚钱和五铢钱,以及碎铁片等等。沙丘常因风吹而迁移,当地居民常拾到零星古物,所以叫古董滩,或叫古铜滩”(15)。
小方盘城就是汉代的玉门关。关城方形如盘,故叫小方盘城。”城垣每面二十六公尺二寸,高七公尺五寸。垣顶每面长二十四公尺八寸,宽三公尺八寸。开西、北二门,……城垣版筑,每层板痕约一公寸”(16)。
向达先生在《两关杂考》中指出,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南湖北之小方盘城。11月5日夏鼐先生率队对关城北疏勒河南土丘中的汉代垃圾堆(斯坦因编第14号墩)进行了发掘。他们用一天的时间,共掘得野麻绳、残木片、碎毡片、麻布片、白绢片、木栉等物,还有一些残木简,其中第三简有“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谓天囗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囗传(?)行(?)从事如律令”等文字,由此简更可证明为玉门关城址无疑。
11月7日,考察队发掘了大方盘城。掘出长方形石刻一块,上有“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乐生”等字,还有五铢钱、陶片及白绿残绢片等。这次发掘所获,最重要的是泰始十一年的刻石,由此刻石得知,晋时敦煌仍隶属于中央政府,并可以推证大方盘城兴废的时间和用途。
大方盘城即河仓城。S.5448《敦煌录》说:“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当时至大方盘城虽无确定的里数,但根据考察队来往路程推测,与《敦煌录》所记里数相符合。又大方盘城城墙上下有排列整齐的洞穴,“以今日关外清时军粮储藏的仓库遗迹来看,后墙为通风起见,也砌成洞穴,大方盘城的用途,可能是军储的遗址,与《敦煌录》所记的用途也相同”。从以上种种情况可知,“大方盘城的建筑,最晚当在泰始十一年(公元275年),或者是汉时的边城。城的用途,可能为军储的遗址,就是《敦煌录》中所记的河仓城了”(17)。
这次西北科学考察结束后,考察队成员利用历史考古所得撰写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向达先生的《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夏鼐先生的《新获之敦煌汉简》、《玉门关发掘新获的汉简》、《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大大丰富了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内容,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
二、王子云与艺术文物考察团
王子云(1897~1990年),安徽萧县人,生前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陕西美协名誉主席。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肄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底至1937年初在法国留学并游历欧洲。1937年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设计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工程无法继续。而由于日寇入侵,使沦陷区的古迹文物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王子云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呈报告,建议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奔赴西北,以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抢救收集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古代艺术文物。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因此被称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聘任王子云为团长,成员主要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和重庆国立艺专即将毕业的优秀生组成。考察团的任务是考察陕西西汉、唐帝陵及宗教寺院,甘肃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古代艺术品和社会民俗。由于该考察团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的陕、甘、青三省,因此又被称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团开始组建时,其考察对象虽然有敦煌石窟,但显然不是重点和首选。后来还是于右任的建议,才将敦煌列为主要的考察任务,正如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说:“1941年,于右任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对我们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艺术宝窟,藏有许多古代的壁画和彩塑珍品,要我们去看看,调查调查。于是由当时政府的有关单位主持,组织了一个共有十多个人参加的考察团,其中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团长。我们于1941年冬从西安出发,到敦煌时,张大千先生早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半年了。”(王子云的回忆,虽然时间上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当时实际的情况。)
考察团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初结束,历时近五年,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的大部分地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研究,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有12人,前后近五年。1941年10月到达敦煌莫高窟的只有3人,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其他的团员有的留在西安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有的留在兰州听候调遣。”(18)考察团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在莫高窟断断续续工作了两年半,有时是4人,有时则只有2人。
虽然考察团在敦煌的时间不长,人数又少,但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王子云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写生图。该图长5.5米,宽0.233米,是采用艺术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绘制的,它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1998年,在陕西省举行的王子云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上,向与会者展示了这件作品。王子云先生去世之后,其夫人何正璜遵其遗嘱将此图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
第二,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一路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就有120多张。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照片已成了莫高窟历史形象的珍贵记录。20世纪90年代,根据王子云先生生前提供的线索,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0辑,每辑1册,每册约50页,每页的上半部是粘贴的照片,下半部是文字说明。其中第7辑是《敦煌千佛洞壁画》,第8辑是《敦煌及其它壁画集》,收集敦煌照片83张。在第1辑的《史迹名胜集》中,还有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全景,由此使我们看到了月牙泉自然变迁的直观资料。
第三,撰写了莫高窟现状调查报告。考察团成员、王子云先生的夫人何正璜女士1942年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发表于1943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10期“西北专号”),是实地考察莫高窟,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它比较系统地对莫高窟的沿革历史及洞窟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粗分了洞窟的类型,探讨了石窟形制的特点和艺术风格。由于是第一个莫高窟内容总录,虽然还有不完备,甚至在今天看来不准确之处,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在“洞窟之编号”一节中说:“就莫高窟悬崖现存之佛窟,可分为南北二段,总计不下五六百窟,惟北段各窟除一二魏窟及元代欢喜佛洞以外,余多空无所有,因此历来调查者多仅就南段佛窟编号。”如伯希和、张大千都是如此。北区的编号是20世纪90年代考古的新收获。
另外,考察团还临摹了一部分壁画。由于考察团的经费紧张,使用的颜料、画布都不是太好(与当时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相比)。他们临摹壁画是从文物的角度出发,即壁画当时是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这也是与张大千相比,因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就与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将壁画上不大好的地方都能改好)。
考察团的成果很快就以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考察过程中,曾在1941~1944年分别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举办过展览,考察团成员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还举办过不同形式的个人展览。如完成敦煌的工作后,就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又于1943年1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由于参观者太多,拥挤得无法继续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周,有3万人参观。
敦煌的考察结束后,考察团又对甘肃河西走廊诸石窟、甘南拉卜楞寺、兰州、西安等地进行了考察。1944年,由于货币贬值,考察团经费实在困难,无法继续维持,便报请政府要求解散。1945年初,“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撤销。经协商,教育部指令由西北大学处理善后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徐朗秋(与王子云是师范学校同学)任西北大学教务长,而老乡刘季洪又是西北大学校长,萧一山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样,西北大学就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由王子云先生任主任并兼历史系教授,继续从事西北历史文物和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考察团收集的文物和资料也交给了西北大学。
三、张大千与敦煌艺术的临摹、创作
西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敦煌的艺术世界闻名。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方关注西北的浪潮中,敦煌也就为世人所瞩目。张大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赴敦煌的。
1941年5月,张大千带着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西赴敦煌。
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张大千义无反顾地去敦煌,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敦煌作为艺术宝库的吸引外,还有张大千个人要通过敦煌探求中国艺术的源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大千听从叶恭绰的建议,为改变画风去敦煌学习技法。叶恭绰素赏张大千的画,曾力劝张大千弃山水花竹专攻人物,以刷新我国人物画的颓风。
当时的西北、当时的河西、当时的敦煌,其自然、气候、交通、物产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差的,曾有“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之说。当1941年张大千一行到达嘉峪关时,曾对随行的人说:在成都出发以前,就有人介绍了西北的艰苦情况,还特别说到河西走廊和关外(嘉峪关以西),说路上吃的是凉水拌炒面,有时没有水喝,实在不行,还要啃西瓜皮,甚至喝马尿。我们现在的条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起码还不至于喝马尿,但要准备吃苦。《西游记》里的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西方取经,我们到敦煌来,也是为了取“经”,不过这是取艺术上的“经”。我们的条件比唐僧好多了,吃的苦也比唐僧差远了。
到达莫高窟的前三天,张大千一直陪同范振绪参观石窟。范振绪离开后,就开始了考察和记录。由于许多壁画需要拷贝把画稿描下来,因此,很多地方就要先搭上梯子,高处要用绳子把两架梯子连接在一起,有时还需要两幅梯子并排而立,一架梯子由张大千记录,一架由别人提着马灯照明。这样工作起来,既慢又危险,张大千就请来了两位油工师傅——窦占彪和李复(他们二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城里驻军的马团长也派来了几名士兵帮忙,这样就加快了速度。
记录工作进行了四五个月后,张大千对敦煌石窟已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时,他改变了原计划,不想马上回成都了,而且还请画家谢稚柳和学生刘力上、肖建初也来敦煌从事壁画的临摹。
在临摹壁画前,张大千还到青海请了藏族画师,并买了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同时为了记录的方便,还给洞窟重新编号。
在石窟里临摹壁画是比较困难的,当临摹大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要一手提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察,看清楚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而临摹洞窟底部的画面时,就要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这样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
敦煌的冬天特别寒冷,莫高窟的绝大多数洞窟都没有窟门,而一些小窟离洞外又很近,最冷的时候,会滴水成冰,而要临摹一幅壁画,就要在一堵墙壁的某一位置连续工作较长时间,尽管他们身穿老羊皮大衣,但仍然冻得非常难受。有时刚把颜色着在画布上,就被冻住了。张大千也常常是一头砂土,满身颜色,他曾打趣地说:“我们简直就跟犯人一样,跑到这里来受徒刑,而且还是心甘情愿!”
从1941年6月到敦煌,1943年10月离开,在两年多的时间,张大千除给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编号、记录,写了2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初稿)外,主要是临摹了敦煌壁画276幅,他为调查、临摹、保护、研究、宣传敦煌艺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无数的心血。正如叶浅予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序》中所说:“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近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
张大千在敦煌取得巨大的成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本人的艺术素养外,还有三个有利的条件,即人多,力量集中;有从青海请来的藏族画师协助;得到了西北各方面,尤其是敦煌各界的支持。
张大千选择了敦煌,敦煌也成就了张大千。由于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许多城市展出,使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了敦煌艺术。而张大千本人,也通过敦煌艺术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艺术高峰,成了中国画坛的领袖人物。
张大千对敦煌石窟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临摹了大批壁画,并在全国各地展出,宣传了敦煌艺术。张大千在敦煌前后居住了近三年,临摹了200多幅壁画,在重庆、成都、兰州、上海等地都举办过展览,使敦煌艺术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可以说,就是张大千开创了敦煌艺术的研究。因为在此之前,敦煌学研究重视的是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此后,敦煌艺术成了敦煌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在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于1944年1月21日专门写了《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以推崇: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19)
其次,张大千还注意学习敦煌艺术遗产,他不仅继承,而且还能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他除了临摹敦煌壁画外,还在临摹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手法从事绘画,如他用古代的绘画传统来表现现代题材,使人耳目一新,很受群众喜爱。正是通过敦煌壁画的临摹,使他的线描更加成熟了,在人物画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敦煌成就了张大千,敦煌壁画的临摹,使张大千成了一世界级的画家。
再次,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尤其是在各地的展出,不仅宣传了敦煌艺术,而且还带动了敦煌艺术的研究。如段文杰就是在重庆看了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另如1944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时,史苇湘还是四川艺专的一年级学生,正是看了画展,才使他对敦煌艺术产生了热爱,并义无反顾地去了敦煌。以段文杰、史苇湘为代表的一批以石窟艺术研究著称的敦煌学家,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如果没有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他们的人生道路可能就是另外的一条。
另外,张大千还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有促进作用。当洞窟编号开始不久,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在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视察河西走廊来到敦煌。由于张大千和于右任有深交,相互来往、交谈也就随便多了,有次吃饭时,张大千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莫高窟是国宝,斯坦因、伯希和把许多好东西都偷、抢去了,你是政府要员,你有责任为保护我们的国宝说几句话啊!”同时,张大千还向于右任建议,应该在莫高窟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于右任表示:回到重庆后就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设想。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8页,三联书店,1987。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8页,三联书店,1987。
③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45~346页,三联书店,1987。
④ 《向达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1943年)》,载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328页。
⑤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13页,1980(11~12)。
⑥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17页,1980(11~12)。
⑦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1980(11~12),35页。
⑧ 《向达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1943年)》,载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329~330页。
⑨ 萧良琼:《向达先生在历史所》,载沙知编:《向达学记》,198页,三联书店,2010。
⑩ 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又见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另见沙知编:《向达学记》。
(1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55页。
(1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56页。
(13)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24~25页,1980(11~12)。
(14)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载《考古通讯》,1955(2)。
(15)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4)。
(16)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4)。
(17)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4)。
(18)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51页,岳麓书社,2005。
(19) 原载《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4年4月)。此据陈寅恪:《讲义及杂稿》,446页,三联书店,2002。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刘进宝著.—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