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中的发现
作者:(英)斯坦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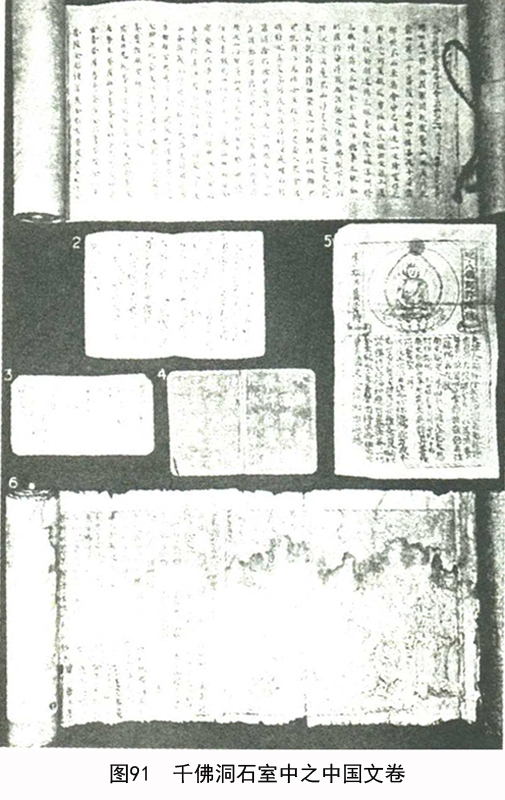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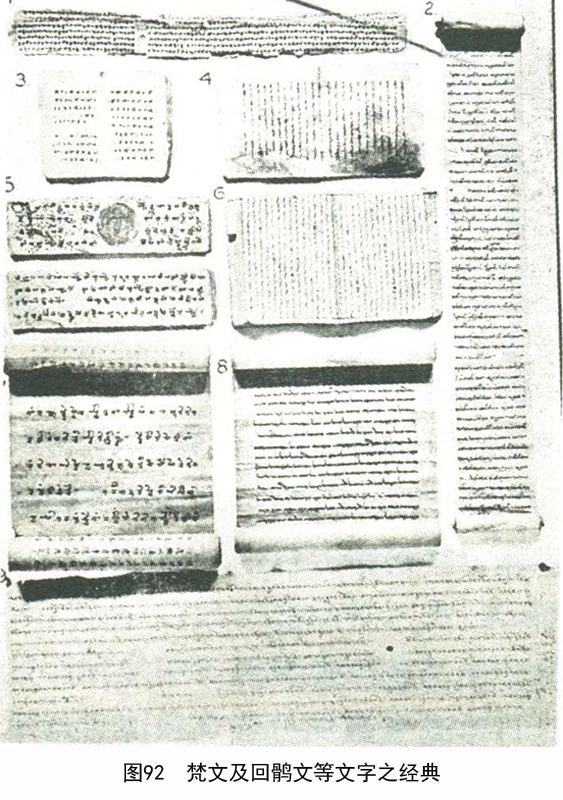
到末了王道士为我的话所动,答应于夜间将秘室所藏中文写本卷子悄悄地拿几卷交给我的热心的助手,以供我们的研究。这里又有一个很侥幸的机会来帮助我们。在道士看来,却是我的中国护法圣人在那里显圣了。我们将几卷写本仔细加以研究,证明那是几种中文佛经,原本出自印度,而经玄奘转梵为汉,于是连蒋师爷也为之愕然了。这岂不是那位圣洁的巡礼者在紧要关头自行显灵,把石室秘藏许多写本暴露出来,作为我在考古方面恰当的报酬么?
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的影响之下,道士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参看图86)。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方英尺。小室约有九英尺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
在这黑洞里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但是等到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把卷子内容急速展观一遍之后,这一座宝藏从各方面看来之重要,便就自行现出了。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高达一英尺左右,长在20码以上。第一卷打开就是一部中文佛经,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石室时无甚差异。
仔细考验之后,发现经尾书有年代,为时约在公元第5世纪的初年,就字体纸张以及形式看来,为时也是很古。在有一卷中文卷子卷背,有一大篇用印度婆罗迷字写成的文字,可见写这卷子时印度字以及梵文知识还流行于中亚佛教之中。像这种古代宗教同学术的遗物,闭于荒山石室之中,不受时间的影响,我觉得并不算奇。在这荒谷里,大气中即使含有若干水分,卷子深藏在石室中,也就与之隔断了。
由开始几小时愉快兴奋的研究,已经显出等待我们的开发的那种新奇遗物是如何的繁复。道士自被我们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他的热心之真假姑且不管,不过在卷子里面又发现许多吐蕃文写本,有长卷也有整包的散叶,都是吐蕃文的佛经。这些藏文经卷明明是吐蕃人占领中国这一部分边陲时期的东西,时代大约在第8世纪中叶到第9世纪中叶。石室封闭之时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从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一碑可以明白,此碑道士先移来嵌在壁上,其后又移到外边。
乱七八糟的中文同吐蕃文的卷子(参看图91)而外,还杂有无数用印度字写的各自不同的长方形纸片,有的是用梵文,有的是西域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参看图92)。就分量以及保存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提并论。
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种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里,打开之后,全是古画,大都画在绢或布上。其中杂有一些纸片,以及画得很美丽的印花绢之类,大约是作为发愿供养之用的。最初所得的画大多为长二三英尺的条幅。从三角形顶部和浮动的旒看来,可以立刻知道这是作为寺庙旗幡之用的。打开之后,绢幡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参看图87、图88)。
作幡用的一律是稀薄透光的细绢。后来我开合很大的绢画时候,才明明白白看出使用这种东西的危险。原来四边虽别有坚韧的材料以为衬托,然而因为在庙墙上挂得太久的缘故,大绢画也很受损害。加以收检的时候匆匆收起,折得太紧,以致破裂。
经了千百年的积压,当发现的时候,如要全行打开,难免没有损伤。但是随便挑阅一卷,都能看出所画的满是很好的人物。好几百幅画,运到不列颠博物院之后,打开修理,那些细微困难的工作,费了专家七年左右的工夫,真是不足为奇的。
那时实在没有时间去找寻供养的文辞,仔细研究绘画。我所最注意的只是从这种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我引以为惊异松快的是道士对于这些唐代美术最好的遗物竟看得很不算什么。所以在第一天匆匆寻访之中,我便能够把可以携取的最好的画选出放在一边,“留待细看”。
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得太过,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他显然是想牺牲这些,以转移我对于中国卷子的注意,于是把放在杂物堆底下的东西一捆一捆地很热心地找了出来。结果甚为满意;在那些残篇断简的中文书中,所得显然为世间性的文书愈来愈多,常常附著年代;纸画同雕版印刷品;印度字的小捆书页,残画丝织物等,明明白白都是发愿的供养品。因此蒋师爷同我自己在第一天一直工作到天黑,没有休息过。
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至于流言的畏惧心情除去。我很谨慎地告诉他说将来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但是他一方面惧怕与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于是常似徘徊于二者之间。到末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蒋师爷的谆谆劝谕,以及我之再三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之真诚信奉。
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所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道士约定,我未离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
经过这几天忙碌的工作,于是堆积在顶上的一切杂卷子全搜尽了,此外还选了一些非中国文的写本、文书、画以及其他有趣味的遗物。然后转向藏有中文写本卷子缚得很坚固的地方进攻。这种工作麻烦多端。仅仅把整个塞满了的屋子清除一番,便足以使结实大胆的人生畏,何况道士。这要好好地对付,给以相当的银钱,才能消减他因胆小而起的反对。
后来在这些堆积的最底下又发现一些各种各样捆扎的卷子,于是努力得到报酬了。因为上面压得过重,不免有破裂之处,我们在这些珍贵的遗物中又发现一幅很美的绣画(参看图89)和一些古代织物残片。把几百捆写本匆匆检察一过之后,又发现若干用印度字和中亚文字写成的写本,掺杂在中文卷子行列之中。不料道士忽然悔惧交集,于昨夜将石室所余宝物一切锁闭,跑到沙漠田去,于是我们这些搜寻便无法完成。但是那时候我们客客气气约定的那些“选出留待仔细研究”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安然运到我的临时仓库了。
所幸道士跑到沙漠田去,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友谊的关系并未引起当地施主们的愤怒,他的精神上的声誉也未受损失。他回来的时候,几乎立即承认我所作把这些幽闭在此因地方上不注意早晚会归散失的佛教文献以及美术遗物,救了出来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很虔诚的举动。因此我们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
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他那种和善的心情我后来又得到满意的证明,四个月后我回到敦煌附近,他还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吐蕃文写本,以供泰西学术上之需。16个月以后,所有满装写本的24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平安地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我到那时才真正地如释重负。
我从那位善良的道士不安全的保管之中得到很多的发现品,不得已而离开以后的经过,在此处应该简单表明一下。大约一年以后,法国有名的学者伯希和教授(Professor P.Pelliot)来访千佛洞。借了他那渊博的汉学知识,他诱导王道士允许他去把剩余的许多中国卷子匆匆考察一番。努力的结果,他从混乱的堆中选出一些不是中文的写本,此外还有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上考古学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道士显然是有了以前与我的经验,于是允许伯希和教授携去1500多卷他所选出来的书籍写本之类。
1909年,这位学者回到巴黎路过北京的时候,他带去许多重要中文写本的消息,传入当时京城中国学者的耳中,他们因此大为兴奋。后来遂由中央政府下命令,将石室全部藏书运到京城。1914年我率领第三次探险队重到敦煌,据所闻报告,得知京城命令实施时可痛可惨的那种特殊情状。
我回到那里,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据他说是我捐给庙中的一大笔钱,因为运送卷子到各衙门,完全在路上就此花完了。整个所藏的写本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问的。
1914年我第二次到那里,王道士曾乘便将他的账目给我看,上面载明我所有施给寺院的银钱总数。他很得意地指给我看,石窟寺前面的新寺院同香客住宿的房屋都是用我所捐的钱修建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珍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见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一定还有不少,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许我带去的还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自然,又得布施相当的数目。
这样地终结了我那一部分在千佛洞的道士故事。但是这丰富重要的材料平安运走以后,研究之余所生的结果,似乎也应该叙说一二。自我于1909年初回到英国以后不久立即开始研究,得到许多专家热心帮助,其中一大部分的结果已散见于我的《西域考古图记》同其他各处,不过仍然还有几种工作等待完成,是可以由这种事实推得它的范围的观念及变化无穷的趣味的。
自然,以前作为石窟装饰之用,或者因为供养而收藏起来的那许多佛教古画,更其足以引起一般公众的兴趣。所有那些美术遗物,数目近五百幅,零篇断简还不在内,已由不列颠博物院聘专家仔细修理,将来保存可以无忧。所有这些古画细目俱见于我所著的《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特别的标本选刊于《千佛洞图录》(The Thou-sand Buddhas)中,秉雍先生(Mr.Laurence Binyon)同我自己对此有详细的讨论与说明。所有这些绘画的详细情形,并见于不列颠博物院刊行的魏勒先生(Mr.A.Waley)著书中。绘画大概的情形略见下章。
在石室所得各种装饰用的丝织品,如地毡以外各色的人物画绢,绣品,以及印花织物之类(参看图90)此处因为限于篇幅不能加以叙述中国古代值得享盛名的织物美术中这些美丽的出品,说到数量同兴趣方面,真是大极了。但是关于这里所得写本内容的丰富,虽然不能详尽,我也得在此处略为指点指点。这对于解释从汉代以来,敦煌一隅之所以能成为各区域各民族以及各种信仰很重要的交流地方,不无裨补。至于这种扼要的叙述,大部分得力于多年来许多有名的东洋学专家辛勤的研究,那是毋庸赘述的了。
这许多中文写本(参看图91),足以证明千佛洞以及常为圣地的敦煌沙漠田的宗教生活,大都由中国僧侣主持。1907年我所带走的中国材料,计有完整无缺的卷子3000卷左右,其中有许多都是很长的,此外的文件以及残篇约有6000。伯希和教授起先曾打算编一目录,后来放弃,1914年遂由小翟理斯博士(Dr.L.Giles)从事编目,因为过于繁重,到如今才能竣事付印,那是不足为奇的。卷子的大部分都是中文佛经;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师(Rev.K.Yabuki)研究以后的指示,其中颇有不少为前人载籍所未著录以及失去的著作。
此外除未知者外,关于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中国学问的残篇,为以前所不知道的也还不少,有好几百篇文书对于当地的生活状态,寺院组织之类,可以显示若干光明,这一切的记录,自古以来实际上就没有留给我们。就卷尾以及文书中间所记载的正确年代,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5世纪的最初以迄于第10世纪的终了。研究所得的这些年代以外,再加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较,可知这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11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Tanguts)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
这一个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还得费许多年的辛勤钻研。我在此处所能说的只是欧洲同日本的学者已经工作过的一两件有趣味的发现。有一大卷雕版印的卷子,上面的年代是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是现在所知雕版书最古的一个标本。就本文同前面扉画所表现的完美的技术看来,可见印书者的手艺以前已是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的。
从另一个观点看,更重要的是中国式摩尼教经典的发现。这种经典的研究,可以使研究包含许多基督教成分奇怪的混合的摩尼教,增加其能得到的安全的系数。以前之于摩尼教,差不多只从反对的基督教书中以及吐鲁番发现的典籍得知一二。摩尼教最初在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站稳了脚,于是在几世纪间由此传布以迄于中亚。向西则竟及于地中海诸国家,在东欧的异教教派中,摩尼教的势力到中古末期,尚还存在。
吐蕃文卷子文书(参看图92),在性质和范围方面同中文材料大致不相上下。大部分也是佛经。但是渊博的牛津大学托玛斯教授(Professor F.W.Thomas)研究之后,曾指出从这些藏文遗献中,也可以得到第8世纪中叶到第9世纪中叶,此地以及西面的塔里木盆地统治于吐蕃人时候,关于当地历史以及其他的有趣味的资料。西藏式佛教之得植基于中亚即起于斯时,后来蒙古人起而信奉,声势因之浩大,至今还能控制亚洲的一大部分地方。
用印度婆罗迷字体写成的许多写本(参看图92),已由中亚语言学大师故霍恩尔教授(Professor Hoernle)的努力,完全做成目录,证明写本包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写本大部分属于佛经,医药方面也有一些。梵文写本中有一篇大贝叶本,就材料上证明,毫无疑义是来自印度的,应算现存最古的印度写本之一。其中有一种古代中亚语言,以前还不知道,现已定名为和阗语或塞伽语(Khotaness or Saka),大约贝叶本同卷子总有好几十种,其中最长的一卷在70英尺以上。另外一种古代语言的写本是龟茲语,一名吐火罗语(Kuchean or Tokhari),古来塔里木盆地北部以及吐鲁番一带大约都操此种语言。在亚洲所操的各种语言中,要以这一种为最近于印欧语族中的意大利语同斯拉夫语(Italic and Slavonic),所以特别有趣味。
就地理学上的意义而言,其足以表示古昔敦煌佛教传布交流错综的情形者,或者没有比在千佛洞发现的古代康居,即今撒马尔干同布哈剌地方,通行的伊朗语书籍更好的了。窣利字出于Ara-maic文,在有一些含有突厥文书籍中并还采用了同样变体的闪族(Semitic)语言。其中有一卷很好的卷子,上面是用突厥字写的摩尼教祈祷圣诗(参看图92)。
摩尼教唐代已入中国,在敦煌显然也有信徒。这里这一派的僧侣,同别处的一样,能同佛教徒住在一处和平无事,并且因为千佛洞为巡礼朝香的圣地,他们一定也有了好处。但是摩尼教曾行于此地的最奇特的证据大约要数那一部完全无缺的小书,上面所用的古突厥字体,同北欧通行的卢尼克(Runic)字母相似,称之为卢尼克突厥文。这是一本占卜用的故事书。故托汤姆生教授(Professor Thomsen)是有名的通解此种古文字的人,据他说这是流传至今最古的突厥文学遗物中“最了不起,最有涵蓄,而又保存得最好的”一篇。
东南西三方奇异的连锁在亚洲的交汇点即是敦煌。而我对于此事的简单叙述,也就以从黄海传布到亚得里亚海的一种民族和语言的奇异遗物作一个结束。
西域考古记/(英)斯坦因著,向达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亚洲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