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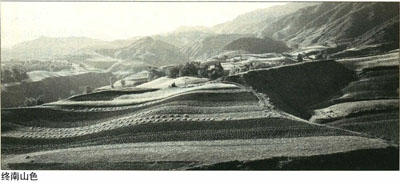
历史终于走到了现代。现代虽然包含时间性因素,但更决定于方法论与人文境界。秦岭的人文地理,其现代划分非常复杂。我们愿意提出三个要素作为参考:其一是科学性,现代人文地理必须吸纳现代科学成果;其二是现代人文的知识学立场;其三是多元的整合驾驭能力。现在看秦岭文化地理的当前语境:①以张国伟《秦岭造山带与大陆动力学》为代表的秦岭地质学研究;②以史念海《河山集》为代表的秦岭历史地理研究;③以贾平凹《商州三录》、叶广岑《老县城》为代表的秦岭文学表达。④以《秦岭探访》《大秦岭》为代表的秦岭影视作品;⑤以《西安自然地理》《陕西农业地理》等为代表的自然地理著述。
《大秦岭》是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主持的大型文化项目。它与终南山“入世”一起构成秦岭走向现代、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标志。在《秦岭探访》之后,《大秦岭》是一部影响广泛、高度成功的影视作品。《大秦岭》之“大”,不单指秦岭是一个巍峨广袤的“大”的自然地理实体,也不仅指秦岭是一个深邃悠久的“大”的历史文化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三秦儿女的大决心、大精神、大期待。秦岭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水平,至为关键!
贾平凹的《商州三录》,十五万言。它描绘了商州地理上的山明水秀,美丽富饶;它表现了商州文化上的野情趣味,神秘传奇。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从此走进了文学史;和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一样,把一个充满心灵寄托的故乡,推到了全国读者的面前,还有秦岭人文地理的研究者面前。《商州初录》写得饱满又色彩丰富,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关注。他不得不续写了第二篇《商州又录》,文字虽然灵气十足,但比起第一篇不论是功夫上还是耐心上,都减弱了很多。但是商州已经成为全国读者期待阅读的一个点。大概一年以后,他又一次重走了商州,又找到了写作的题材,就写了《商州再录》。这一次和第一次一样,充满了新的准备,经历过最初的灵动,他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思考。《商州三录》起步于1983年,是迄今为止表述秦岭文学的最好作品。
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现在出版了9卷。其中涉及秦岭的历史地理研究,精深厚博,内容丰富,和台湾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研究》第三卷《秦岭仇池地区》,为前辈先贤秦岭历史地理研究的双壁高峰。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秦岭现代人文地理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和可靠驿站。
《禹贡》《山海经》和《诗经》,是秦岭广义“历史地理”的三大经典和权威。广义秦岭,用去了《禹贡》2/3的篇幅;狭义秦岭,也用去了《禹贡》1/3的篇幅。其中,“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是对秦岭南坡的重要叙述和专题研究。“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是对秦岭北麓的重要叙述和专题研究。其中的“终南、惇物,至于鸟鼠”,是描述秦岭终南山的。“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是描述秦岭华山的。“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和“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是描述西秦岭的嶓冢山。从《禹贡》开端,中经《汉书地理志》到近代众多的《方舆纪要》,属于秦岭的历史地理传统研究。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对于秦岭文化地理而言,《西山经》最为重要。其中的“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是研究华山的经典名篇。“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鸟多尸鸠”,是研究终南山的经典名篇。对于秦岭文化地理,《山海经》最重要的是10多处对于昆仑之丘的论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自从汉武帝将《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钦定为西域新疆的昆仑山之后,古昆仑成为聚讼焦点。全国有接近20个地方,都被认做是古昆仑。但我们认为,古昆仑即西秦岭的宝鸡天台山。
《禹贡》是秦岭狭义“历史地理”的经典权威,其后继者以《汉书·地理志》为开端代表,我们归到“国脉秦岭”。《山海经》是秦岭神性地理的经典权威,其后继者《道德经》为开端经典,我们归到“道观秦岭”。《诗经》是秦岭人文地理的经典权威,其后继者以“诗唐南山”为经典代表,我们归到“诗品秦岭”。
秦岭在周朝《诗经》,被称之为“南山”和“终南山”。在汉唐时期,自班固《西都赋》“睎秦岭”之后,则“秦岭”与“南山”“终南山”共同使用,仍以后者为多。宋元各代,与唐朝基本相同。宋代的苏轼任职凤翔府时,在一首《壬寅二月……寄子由》诗中写道:“鸡岭云霞古,龙宫殿宇幽。南山连大散,归路走吾州。”明朝“前七子”的何景明写道:“名邑今重过,终南第一游。山中白云唱,天上彩云流。”到了清代,傅龙标的《牛首山怀古》写道:“南山高亘日苍苍,东流涓水时泱泱。”从汉唐到明清,大抵是“南山”“终南山”的名称使用占大多数,而“秦岭”一名居少数。在有唐一代的璀璨诗文天空中,“秦岭”一词不仅出现的次数少,且常常带有贬抑、消极色彩。明清之后,近代以来,无论“秦岭”还是“南山”,更是在文本的文明世界日趋式微,依稀渺茫;不多的涉猎者,多来自于科考性地理著述。正是在近代以来的科考地理著述中,“秦岭”的出现开始多于“南山”,成为这座巨大山脉的正式“学名”。
“秦岭”取代“南山”,历史用去了差不多三千年的沧桑岁月。《大秦岭》之“大”,乃是南山百代复兴之“梦”吧。“大”者,何谓?《孟子·尽心下》告知我们:“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秦岭之“大”,如欲梦想成真,就必须领悟南山的本真之美,就必须回到终南的原初之圣。
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高从宜,王小宁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