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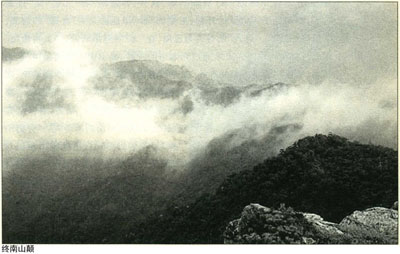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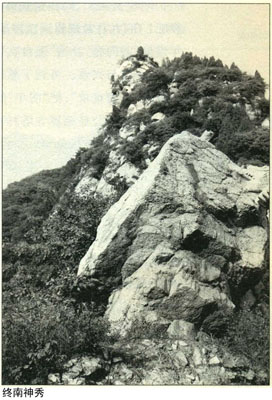
李白的《望终南山》,开首的“引领意无限”与结尾的“灭迹栖绝巘”,直接敞开了终南山的两大无限性:审美与宗教。而我们在李世民《望终南山》的王风御气里,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王风御气:“心中与之然”,而“托兴”的深与浅,各人还是尽力而为吧。还有王维的《终南山》,还有张乔的《终南山》!
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张乔《终南山》:“带雪复衔春,横天占半秦。势奇看不定,景变写难真。洞远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人。”
李白的《望终南山》写出了终南山审美与宗教的两种无限性,李世民的《望终南山》写出了山河社稷的双重王风御气,王维的《终南山》则写出了终南山的神圣与神妙感。以“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的起句,就透出神圣感情:“近天都”,还有比这更高、更神圣的山吗?现代人面对世界最高山喜玛拉雅山,会如“近高天”,而不会有“天都”概念。“天都”的概念,不仅是高度概念,而且是一种神圣感情。在这种神圣感情影响下,王维写终南山的广远,就用了一句“连山接海隅”,而张乔写的是“横天占半秦”。“占半秦”虽有夸张,仍是常识理性描述。“接海隅”则是神圣无限性感情。“白云”到“壑殊”,则是从神圣感过渡到神妙性描写:“回望合”“入看无”,写诗人被终南山的神妙性吸引住了——白云哪,刚才还飘逸两处,现在回望已经“相合”。“回望”表明对白云之“合”的期待意向,期待“白云”合成什么呢?白云现在又合成什么呢?白云现在合成的形象与诗人期待白云合成的意向,两者之间“相合”吗?
这是王维留给读者的最起码的阅读眼光。王维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即下句的“青霭入看无”。“青霭入看无”,首先让我们想到韩愈“草色遥看近却无”。王维的“青”更加高妙:其一,韩愈的“看”无论“遥”还是“近”,都还处于“草色”的外部;王维的“看”却是进入到“青霭”的内部,结果却是“无”。“进入”的行为与意向,在“无”的结果面前,不显得唐突、尴尬与自我否定吗?王维通过终南山的神妙,显示出人的幼稚性,这是韩愈《早春》“最是一年好春处”完全没有的。其二,在这种幼稚感里,回望白云的期待行为与意向,以及我们引发的追问也一并遇到“威胁”:那也许是人类的天性、本能,形象的构成与人自己的“看”相关,有什么客观绝对值得执著呢?人类的智能也许还无法面对山的神奇呢。“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直接以“变”“殊”给我们以多元自由的观山意识与觉悟。告别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首先是写出了诗人自身的变化:向樵夫讨自己的投宿处,他已经是“隔水问”了,在“入看无”的教训之后。就这样,王维的《终南山》先以“近天都”“接海隅”之宏大,写出人面对神圣者的空间距离;接着用“回首望”“入看无”,表达人面对神妙者的实际距离。至少在自然审美领域,有流传甚广的“距离说”。在“欲投人处宿”之际,王维保持了一种距离姿态与觉悟。这种距离化的“投宿”姿态,是神圣与神妙的终南山对人的精神馈赠,是领悟终南山神圣和神妙存在的妥当方式。
与王维《终南山》相比,张乔《终南山》要好读一些。尽管如此,张乔也以“势奇看不定,景变与难真”,表现着人面对终南山的渺小和局限性。张乔将人在终南山面前的渺小和局限性,更多倾向于认知表达能力范畴,不像王维那种整个精神的幼稚与唐突。张乔在终南山的山水中也仍然感悟到了“通岳”与“有神”。张乔在诗的结尾,与王维一样来到了樵夫面前:“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夫。”王维只是在投宿之际,有距离地“隔水问樵夫”。张乔在《终南山》干脆直接承认,王维的“白云回望合”的惆怅也罢,“云深不知处”的失败也罢,也只意味着一个结论:“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夫。”
也许是接受了张乔的结论与建议,祖泳、杜牧等更多的诗人,都选择在长安京城远望终南山:“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晓暮寒。”(祖泳)“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唯有茂陵多病客,每来高处望南山。”(张元宗)“标奇耸峻壮长安,影入千门万户寒。徒自倚天生气色,尘中谁为举头看。”(林宽《终南山》)
然而,“望”终南山,与“游”终南山终究是不一样的,与攀登终南山更有差别。一般而言,攀登终南山会找到自己的问题与差距,比如王维、张乔在《终南山》中所承认的与“樵人”的差距。“游”终南山也有“治疗”作用,司空图在《游南五台》写道:“苍松临砌偃,惊鹿蓦溪来。内殿评诗切,身回心未回。”在“内殿评诗”,司空图的“心”还在南五台呢。孟郊《游终南山》以“到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作了明确声明。而一旦在长安京城望终南山,情况就显得异常复杂起来。上述例中,祖咏与林宽的望终南山,感受到的是“寒”;张元宗是“病”与“清高感”;杜牧的感觉是“无一色”,将“望”的差别完全泯灭。就是同一个诗人,比方诗圣杜甫吧,亲自游秦岭和仅仅在城中远望,感觉和收获也有很大不同:
《九日蓝田崔氏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样是秋天,同样是登高,同样是望“秦山”,有无旷士怀就完全两样吧!在《九日蓝田崔氏庄》,虽然是“悲秋”“峰寒”,但一想到“老去”“明年谁健”的问题,杜甫“强自宽”而有了“旷士怀”,也有了“醉看终南山茱萸”的心情与兴致。可到了慈恩寺塔上,就既“忧”又“悲”且“哀”,就“秦山破碎,泾渭难求”,把“明年”的自己忘了,全无旷士怀了!
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俯视但一气”里,杜甫是“莫辨皇州”,看不到明朗的明天与希望。在《望终南山》的“镜天无一色”中,杜牧是“历历皇州”,充满明天与希望。杜甫的“一气”和杜牧的“一色”,多么不同啊!同样的秋天,同样的登高,杜甫的心情何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与差别呢?如果这是山与人有别的缘故,那么杜甫就应该多去终南山吧。同样的终南山,在长安仅仅“望”(《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和前去亲自“游”(《九日蓝田崔氏庄》),“旷士怀”一有一无,结果完全两样。李白的《望终南山》是两种无限性的丰富收获,李世民的《望终南山》弥漫着浩荡的王风御气。从《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看,杜甫的“望”效果明显不如前去游终南山。王维登上终南山,感受到了诸多神奇与神妙。杜甫的感悟力不在王维之下,倘能登上终南山,不仅会有同样的神圣与神奇感,更会收获李世民、李白之外的另一种王风御气吧。
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高从宜,王小宁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