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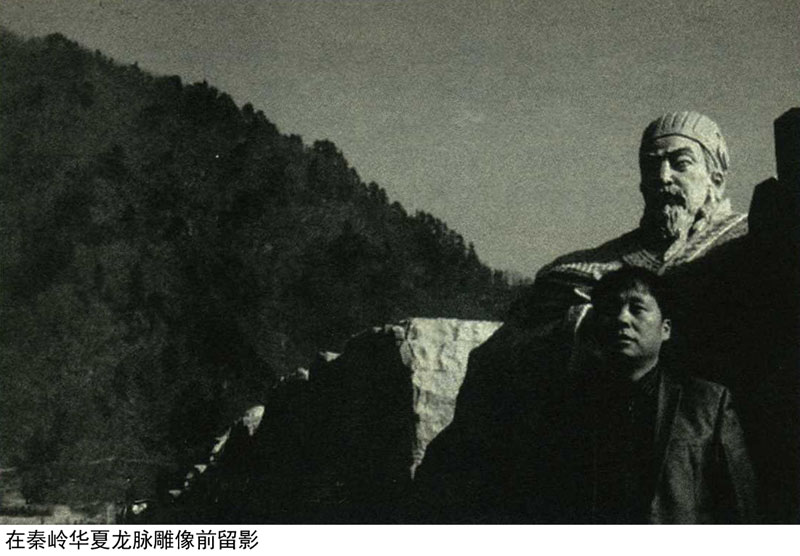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部的铁尺梁下,为秦岭西段重要关口,是红军长征由川入甘的必经之路。
从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以西的于都河出发开始长征后,到达西秦岭时,红军已走了11个多月,此时正值冬季,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已经饥寒交迫,伤痕累累,筋疲力尽。在这期间,红军一直在苦苦寻找落脚点,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红军到达腊子口时,甘肃军阀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已在腊子口层层构筑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还部署了三个团的兵力纵深把守腊子口山后的天险要道,企图堵死红军北上之路,将红军一举剿灭。
西秦岭的腊子口就成了红军命系一线的关键所在。1935年9月15日,毛泽东果断下达了“两天之内必须拿下腊子口”的命令。“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红军就得重回草地去。”
9月16日下午,战斗打响。唐进新回忆说,由于口子太窄,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十几次冲锋都没成功,“鲜血染红了湍急的腊子河水”。
半夜时分,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命令部队暂停进攻,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率领从正面夜袭,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强攻;另一路由团长率领,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的后方去。
战斗再次打响。关键时刻,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去,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爬上去。
“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当迂回的红军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密集的手榴弹砸向敌人碉堡时,正面强攻的战士也潮水般冲过木桥……秦岭,这个决定红军命运的关口,就这样被红军控制了。
“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老红军徐占权说:“夺取了腊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为在陕甘宁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样也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2013年,我走近腊子口时险峻依然,远远望去,山口呈一个巨大的“V”,仿佛是红军伸展双臂在欢呼胜利的定格。
1935年9月18日,红军突破腊子口后,翻越岷山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山——大拉山,冒雨进占了甘南的交通重镇,位于秦岭脊梁上的哈达铺。
经历了雪山草地漫长而艰苦的行军后,红军终于在哈达铺吃上了饱饭,也在这里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重大转折起源于几张旧报纸。”徐占权说,在先头部队抵达哈达铺时,红军在当地邮政所找到了一些旧报纸,并在上面发现了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师的消息。
于是,毛泽东决定向陕北进军。老红军徐占权和当时总指挥聂荣臻回忆说:“而就在哈达铺,红军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目的地——陕北。”
因之,秦岭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之岭。
时隔6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访问哈达铺后写道:“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
1936年12月12日,在秦岭余脉骊山下的华清池里又发生了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我国大片河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亡国亡家在即。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在秦岭山下华清池兵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击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最终将日本赶出了中国。
秦岭,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刻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曾一度选择西安为陪都,甚至成立了西京筹备处。日本侵略者止步于函谷关以东,说明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地理形势仍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秦岭在军事与政治地理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甚至在古代的行政区划方面留下了可供思索与研究的痕迹。如陕西的南部从经济文化上接近于巴蜀类型,但陕南却在行政区划上划归陕西。其目的就在于打开封闭地形的一个缺口,便于加强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清初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其论述颇有见地。《史记·高祖本纪》就说: “(秦中)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纵观秦岭上下五千年,多少王侯与将相,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民国与当今,其命运都与秦岭密不可分。因而,秦岭是王者之山。
华夏龙脉大秦岭/周吉灵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