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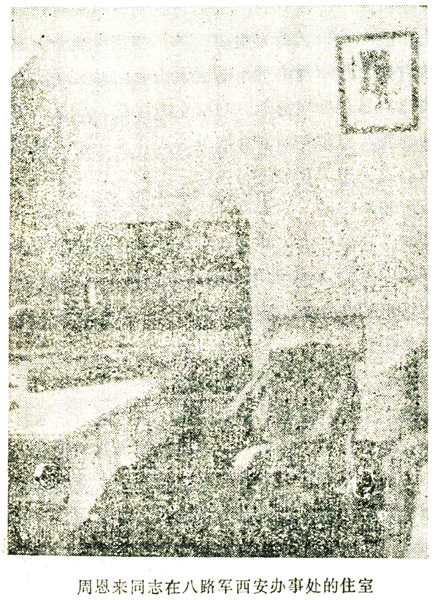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开会,研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问题。会议决定把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省霸占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表示同意,并且已经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群情愤激。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下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西安各校学生为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行动,先于五月七日停课一天。五月十日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立即罢课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阴谋。游行队伍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作断头鬼,不作亡国奴”等爱国口号,冲破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陈树蕃等人的重重阻挠,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陕西学生还曾推选屈武、李伍亭为代表,前往北京请愿,并与各地学生代表取得联系,从而把西安的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且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官职,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北洋军阀一样,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他命令张学良从东北率部队撤退到山海关以内,就这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几乎一枪不发地拱手把东三省让给了侵略者。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集中全力,不断“围剿”共产党开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安地区广大人民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
一九三五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奉命进驻西安一带。同年九月,蒋介石自任“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与原驻陕西省的杨虎城的西北军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地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在这一年的年初,由程子华、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在陕南给杨虎城军以沉重的打击,击溃了西北军的三个旅。但张学良还没有吃过苦头,他走马上任以后,立即组织大部队猛扑陕北解放区。刘志丹、徐海东等同志以仅有七、八千人的红十五军团进行反击,将东北军一一〇师全部歼灭,并歼灭其一〇七师一部,使东北军首次受到重创。
—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北上抗日,毛泽东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同年十一月,中央红军在富县西南直罗镇一举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活捉师长牛元锋,又歼灭东北军一〇六师一部。红军以辉煌的胜利,给党中央立足陕北举行了奠基礼。从此,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司令部、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由于陕北所处的重要地位,国民党反动派便把西安作为“反共”的前哨据点,使西安成为当时全国矛盾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地区之一。但在群众巨大的抗日热潮的压力下,特别是在进犯解放区中所受到的血的教训,迫使张、杨认识到工农红军是深受人民拥护的、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当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被日寇蹂躏的国土愈来愈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提到每个人面前的时候,张、杨二将军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又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志与李克农同志一道,去当时由东北军控制的延安,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了长谈,解除了张学良许多疑虑,更坚定了他走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
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中共中央委派叶剑英同志为常驻西安的红军代表。至此,终于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以抗日为目的的民族统一战线。“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响遍了古城西安和陕西原来的内战前线。
蒋介石过去对张、杨二人就非常怀疑,因而极力在西安安插他的亲信和特务。如“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西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兼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等,都是人人尽知的明牌特务头子。而“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和杨虎城负责的“西安绥靖公署”中的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则更是蒋介石暗中埋藏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军统特务。但由于当时西安群众普遍高涨的革命情绪和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比较坚定的抗日态度,使国民党特务不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
一九三六年三月,西安各界人民组成了“西北抗日救国会”,后来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接着,东北逃亡来陕的各界人士,组成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各学校也都组成了“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西安的群众抗日救国活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群众利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双十节”、“悼念鲁迅”等各种机会,组织大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批驳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谬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罪恶阴谋。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张学良请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宋黎,来西安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所犯下的罪行,并介绍北平等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进一步鼓舞西安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在西北大旅舍(位于今西安市东大街)逮捕了宋黎同志。他们走出旅舍时,恰巧碰上路过的西北军宪兵巡逻队,宋机警地大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宪兵把宋黎和特务一块带到西北军中。张学良闻讯接回宋黎,他疑心国民党省党部(故址位于今东大街)内还藏有有关特务抓人的名单和文件,因而当夜派人查抄了省党部的特务档案。事后,张学良向蒋介石发电报称:宋黎是“西北剿总”请来的工作人员,逮捕“剿总”的人,事先不通知他,使他今后难以工作,因而采取了这些鲁莽行动。最后,张学良请求给他处分,并请求将宋黎留在“西北剿总”处置,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回电:“应免置议”。
蒋介石感到西安的问题愈来愈加严重,因而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亲自出马来西安监督张、杨进攻解放区。但张、杨仍然极力主张一致抗日,反对内战。蒋介石见指挥不动东北军和西北军,便准备采用强硬手段解决。他中途到洛阳去调兵遣将,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督“剿”①。他准备一箭双雕,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一并解决。同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威逼张、杨进攻解放区,并暗示如若不然,就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外省。实际是想将他们调出后,借机各个消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由“西救”、“东救”、“学联”出面,发动群众举行了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议期间,中央宪兵部队和特务警察百般阻拦,多方刁难,包围会场,制造事端。当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时,东北军办的东望小学(故址在今西安东羊市街)一名小学生被宪警开枪打伤,更激怒了与会群众。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等处请愿;然后又整队出发,准备步行前往东距西安五十多里的临潼华清池,去向住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和惩办开枪打人的凶手。以学生为主干的群众大队走到城东十里铺时,蒋介石的马队排满街头,前边两侧的高地上架起了机关枪,并扣留了请愿大队的“交通员”,形势非常紧张。正相持间,张学良将军骑马赶到,劝学生回去,并诚恳地说:我并不反对你们救国,只是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在这里流血。一位东北女学生回答:“我们愿意为国流血,愿意为国牺牲,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她说毕痛哭流涕,其他人都跟着哭了起来,连路旁行人和张学良的马夫也都泣不成声。张学良大受感动,挥泪陈词:“我张学良小子不是不爱国的,我与日本鬼子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请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决不辜负。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准定用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群众这才列队折回西安。
张、杨苦苦劝说蒋介石改变主意毫无效果,便下了进行“兵谏”的决心。经过周密布置之后,他们开始联合行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时,东北军一百多名官兵进入华清池,准备乘蒋介石没有起床时,一举将他捉住。不料被守护华清池的蒋介石卫队发现,互相开枪打起来。经过短暂激战后,消灭了蒋的侍从卫队。但进入蒋介石住宿的五间厅时,里边却空无一人。蒋的衣帽还挂在衣架上,一副假牙仍泡在茶几上的杯子里,被褥尚有余温,院子里的汽车也不少一辆。从种种迹象判断,蒋介石肯定是刚刚徒步逃走,不会离开多远。在后围墙边又发现了蒋介石的一只鞋,指示了他逃走的方向。
原来蒋介石被枪声从梦中惊醒后,穿着睡衣就往后跑,由他的一名贴身侍卫帮着翻过墙去,落地时划破了小腿,摔伤了腰,掉了一只鞋。又由这个侍卫连背带推地帮他爬上山去。东北军找遍华清池后,开始搜山,在骊山山腰的一块峭立的巨石边,发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这个威风不可一世的人物,当时全身哆嗦,面色苍白,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被吓得走不成路,因而只得由人背下山来。蒋介石被押送回西安以后,先把他看管在新城大楼里。几天以后,为了管理和工作方便,又把他搬到离张学良公馆(今建国路陕西省人事局招待所)不远的高桂滋公馆(今建国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中。
当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张、杨又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商讨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和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西安,以达到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由他取而代之的目的。日本自然希望中国越乱越好,以便混水摸鱼,从中取利。日本外相几次声称:南京政府若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公然煽动国民党政府出兵讨伐西安。亲美派的宋子文等,则主张首先营救蒋介石,反对立即讨伐,唯恐亲日派篡夺了军政大权。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对“西安事变”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大规模内战。
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中共中央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制订了正确的方案: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等等。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同志与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西安。为了安全,他们开始被安排住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上。
周恩来同志到西安之后的当天晚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仔细向张学良询问了各种情况,高度评价了张、杨二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然后又耐心地向张、杨二人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说明只有防止内乱,才能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才有救,民族才有救,因而应该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周恩来等同志夜以继日地奔波交谈,召开了各种会议,做了大量工作,才使“西安事变”得以圆满解决。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深为周恩来同志的精辟见解,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不计较历史恩怨的行动所感动,同意了共产党的主张。蒋介石迫于全国的形势和他自己当时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得不承诺停止内战,接受一致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的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②
作为国共合作的标志之一,就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在西安北新街的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联络处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处理“西安事变”问题中作了大量工作。后来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也搬到这里来居住和接见来访的客人。
一九三七年九月,“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后来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占有七贤庄一、三、四、七号四个院落。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都曾先后担任办事处的党代表。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办事处的同志们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克服重重障碍,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给陕北根据地和前方部队采购药品和各类物资,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办事处经常输送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前往延安,为壮大我军力量,培养革命干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一九三八年的五至八月,就向延安送去了二千二百多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经由这里到达陕北的。
在艰苦的岁月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来西安办事处居住和指导工作。
八年抗战中,西安的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仍然以迫害进步人士、破坏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胡宗南数十万军队,不开赴前方抗击日本侵略者,却沿北山布防几百里,以封锁和破坏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对于全力以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国民党反动派更视为心腹大患,百般进行迫害。他们在办事处周围设置了二十余所特务哨所:有专设的哨棚,有特务开的小杂货店,连修鞋的、拾破烂的、拉人力车的中间,都安插有特务。我办事处的同志们,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依靠人民群众,通过英勇机智的斗争,战胜了敌人一个个的破坏活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又一次发动了全面内战,疯狂进攻解放区。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撤回延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东风扫残云,春雷震长空,西安获得了解放。解放后的西安古城,百废俱兴,人民政府也很快将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旧址进行了整修,在这里陈列了许多革命文物和图片,开辟为向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纪念馆。三十年来,很多革命老前辈来西安时,百忙中还常常要抽空到这里看一看。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下午,八十二岁高龄的叶剑英同志,冒着晚春的雨雪,又一次访问了四十三年前他工作过的这个地方。他询问了旧日的同志,参观了他当年在“西安事变”期间陪同周恩来同志接待各界来访朋友的小会客厅,参观了各位老同志和他自己住过的地方。触景生情,他又想起了那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已经逝去的战友,当场吟出一首意境深远,词语动人,题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雪后与明涛、尔重同志访办事处志感》的七言绝句: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
参观历时一个多钟头,临走时叶帅亲切地说:“同志们,再见!”汽车徐徐开动后,他老人家仍在依依不舍地向送行的纪念馆工作人员频频招手。
①参见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二十九页。
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九三八页。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