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追梦:风沙风沙漫天飞
作者:李广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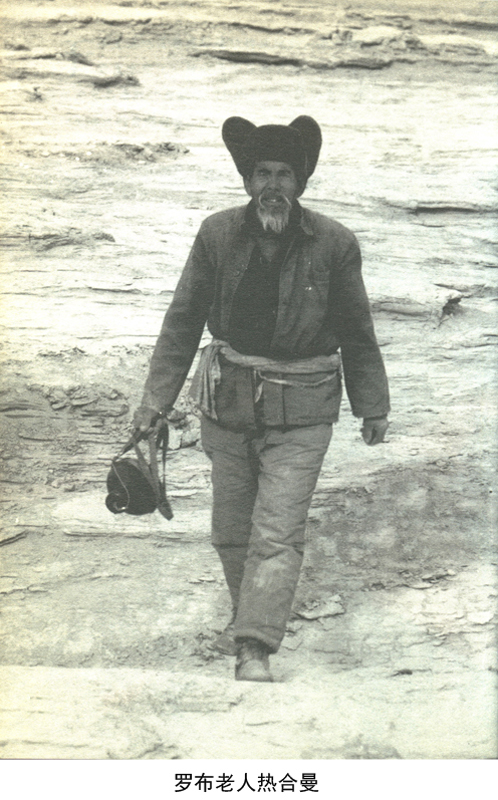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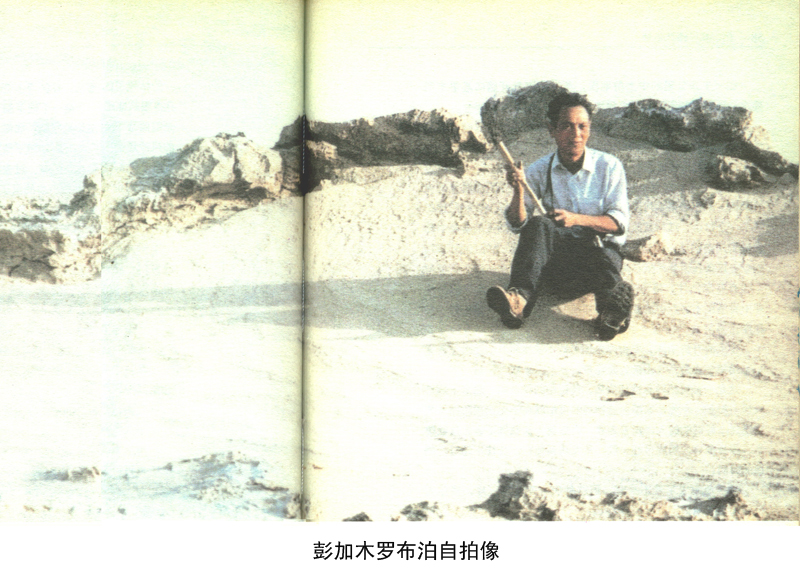
百年以后。
高昌文明开始兴起。
高昌城池坐落在火焰山下,面对大漠。在西汉以后的千余年漫长岁月中,西域大地上发生的任何政治、军事事件,都存在着或深或浅的联系,楼兰当然也不例外。
大约在公元200年以后,高昌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都会,古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繁荣一时,声名烜赫。在西域,高昌确实是一座大城。高达12米的城墙上,人来马往,旗帜飘扬,周围达5公里多的方形城墙,每面有2到3座城门,分别冠以“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不同名号。城门外面,还有曲折的瓮城。城内占地达220万平方米,街道纵横,商肆骈列,东来西往的使节、商旅,亚欧的特色名产,都在这里驻足、集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服装、语言各异,肤色、发式不同,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商会。
这就形成取代楼兰的必然趋势。
楼兰的出现和繁荣,是西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楼兰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中枢,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从西汉到东晋的历代中央政府,都在这里设官屯田。人类以其辛勤的劳动维持着楼兰地区的生态平衡,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楼兰地区的发展。“大田三年,积粟百万”,这在当时的西域,就是被“胡人称神”的奇迹了,更何况,这种屯田的规模还在逐年扩大,并持续了百年之久,楼兰在注宾河拦水筑坝之后的岁月里,其繁荣富饶可想而知。
同样道理,只有当楼兰在政治上丧失其地位,经济发展方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大自然的袭击造成的衰败才成为无可奈何。
当年,汉朝通往西方的道路,一出玉门关就分为两条道,即南道北道。南道路线比较稳定;北道则又分成两路,一路经吐鲁番(即古代的高昌),一路经楼兰。楼兰之路最为便捷,但沿途乏水草,多风沙,特别是要通过白龙堆和盐漠,比较艰难。经吐鲁番一路,靠近匈奴,而当时的匈奴在西域是最为强大的,时常在一夜之间,铁骑千乘,袭击高昌,形势动荡,故而这条路无法使用。在这种形势下,楼兰便担负起了“负水担粮,送迎汉使”的重任。为了保护这条通道,汉朝政府开始重点经营楼兰,设官筑城,屯田驻兵,带来了楼兰地区的繁荣。这个时候,楼兰的含义已经扩大,包括鄯善及至整个儿罗布淖尔。
随着高昌局势的稳定,中央政府重兵出击,把匈奴势力逐出了高昌地区,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于是,高昌成为西域的门户,高昌一路开始启用,经高昌直通焉耆的天山南麓道开始逐渐取代楼兰道。
道路的变化,使楼兰不知不觉丧失了中西交通中继站的地位,楼兰,开始由繁荣变为萧条。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一开始,楼兰人完全没有觉察,甚至还认为往来汉人的减少是一件好事。
先是,汉朝西域屯垦部队的最高指挥机关,戊己校尉府在高昌设立。楼兰人想,设立就设立吧,关我们什么事。戊己校尉又不是我们的王。但实际上,在汉朝廷的眼中,你就是10个楼兰王,也比不得这个“戊己校尉”的重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董卓吧,肩负过西域“戊己校尉”的汉朝重臣中,就有这个董卓。他是因为西域屯垦有功,才被召回洛阳就任中郎将的,镇压黄巾起义,他是总指挥。由此可见“戊己校尉”的地位。
自从汉朝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府以后,伊循垦区就再没有增加过汉朝兵士,甚至连流放的囚犯也没有过。不仅如此,楼兰地区的汉朝屯垦部队还不断地有人被调往高昌,开始是三三两两星星点点,后面就多了起来,整队整队奉命而去。
这期间,注宾河还发过一次洪水,阵势非常吓人。虽然鄯善国倾城而动,加固河堤,保住了大部分耕田,但毁坏了的支渠毛渠很快就被随后而来的狂风流沙所壅塞,渠水因堵塞面漫过渠堤,把大田冲击得七零八落。
鄯善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汉朝屯垦部队里,懂得治水的人大都调走了,留下的也想不出多少办法。即便想出办法,人力也成了大问题,这时的伊循垦区,要想从邻近国家调集兵力已经没有号召力了,西域诸国以及分散在西域各国的汉朝屯垦部队,只认高昌戊己校尉府,而视其他为平起平坐之“友邻单位”。
鄯善人头一次感到了高昌给他们造成的威胁。
但更大的威胁还在后头。
公元327年,前凉王朝张骏正式在吐鲁番设置高昌郡,成为割据一方、统领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
大约就在这一年,汉朝在鄯善地区的屯垦官兵全部撤走,仅剩下一些不愿回返的囚犯和来往不定的商人。
现在,土著的楼兰人就要开始独自面对汉朝屯垦之后留下的一盘残局。
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自然环境对人的奴役就增加。
干旱荒漠地区自然环境结构很脆弱,某一种因素发生变化,特别是水分的变化,便极容易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大破坏,从而引起环境的大改变。面对一次浩大的自然灾害,人类往往束手无策,既无能力及时地进行治理,又得不到别的神奇力量的救助,于是,惊恐的人类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沙化。
人类的惟一选择只有逃亡。
楼兰的死亡,就是在古丝道路线改变之后,楼兰失去人类保护,受到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水分减少,气候奇热,瘟疫流行,盐碱日积愈甚,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楼兰人也促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尽管他们至死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科学家已经测定,沙漠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科学家还提醒人类,楼兰之死仅仅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一张黄牌警告。楼兰的死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弄不好,也许就在某一个夜晚,一场沙暴突袭而来,一些城镇就再也不能从沉睡中苏醒——当代文明长埋沙海而为后人提供最新的历史遗存。
这真让人心惊肉颤。
但绝非危言耸听。
还是回到公元4世纪来目睹这艰难而悲壮的一幕。
连续10来年,罗布淖尔地区居然没有下过一场雨,也没有落过一场雪。当然有那么几次,突然间浓云密布,电闪雷动,罗布人真真切切地看到斜倾的雨帘在急促地往下泻,都欣喜若狂地张开手臂以迎接这来自天上的甘霖。
然而,这雨在离地面还有十来米的距离时就蒸发消失了。
时间不长,云去日出,又是火辣辣的天气。
地面好像着了火,升腾着泛红的烟尘。
开始几年,罗布人还没有特别在意,天气炎热,他们可以钻进水里去,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了潜在的不妙:罗布淖尔,这在他们看来是永不会枯竭的大泽,居然在可怕地年复一年消退。
大泽周围的小海子在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彻底干涸而只留下龟裂的泽底,继而又泛起白花花的鱼鳞一般闪亮的盐碱来。
过去,波浪一般起伏摇摆的芦苇丛,也开始一片接一片地死去,枯黄的干得捏一把就能变成粉末的苇秆,在热风中发出令人揪心的沙沙拉拉的声音来。
世世代代活跃在罗布淖尔的各类飞禽走兽开始明显地减少而不知去向。猎人悲哀地说,两三年了,再没有见到那色彩斑斓的罗布虎,也没有见到那成群结伙的野骆驼。而猎人见不到虎是会发疯的。
罗布淖尔的中心大湖的水位也明显地降低了。靠近大湖在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只“卡盆儿”,一柄木桨,吹着芦笛,唱着渔歌,晃晃悠悠地就进入了水波浩淼的大潮之中,黑色的大头鱼就追着你的“卡盆儿”往外跃,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载而归。如今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你得拖着“卡盆儿”,穿过一片接一片的枯死了的芦苇丛,你的身上会留下横一道竖一道的血痕;你还得艰难地蹚过一个接一个地干涸了的海子,白花花的盐碱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刺伤你的眼睛;如果起风,那么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风沙还会叫你睁不开眼睛辨不清方向。高大的胡杨林里,每一片叶子上都泛着白花花的碱,过去凉风徐徐的林子里,如今却成了虫子的世界,数也数不清的虫子拖着长长的丝从树上垂下来,织就成一张张动荡不定的网,你如果贸然地闯进去,你就会很快地陷入“网”中而浑身上下裹满蠕动的叫你恶心和恐惧的花虫子。
汉人汉兵一走,耕地是完全地荒芜了。罗布人不知道如何应付这年复一年的干旱局面。各种各样的堤坝渠道还在,可就是里面没有水。注宾河是完全干涸了,罗布人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一条好端端的大河,怎么可能说消失就消失了呢?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残酷的现实逼迫楼兰人不得不收缩开支,艰难度日。
楼兰士兵的口粮,这原本最先保障充足供应的一部分,也开始减少。
开始,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量是黑粟一斗二升。
不久就减至一斗。
再后来就成了八升。
再再后来就成了六升。
而之所以一减再减,节约之钟频频敲响,目的就是为了“宜渐节省使相周接”。可见问题已相当严重。
在这种形势下,楼兰人也开始意识到了树木的重要和不可或缺。
在这方面,楼兰的法规开始变得严厉起来。
法规规定,如果树还活着,不允许任何人砍伐。如若违犯,砍断树根罚款为壮马一匹,即便砍断树枝,也要罚母牛一头。
这大约是我们所见到的古西域最古老的保护森林树木的法规了。
然而,正所谓天火着了,毛毛雨是救不了的道理一样,楼兰人所有的努力已为时太晚,也相当乏力,楼兰的末日一天紧似一天地逼近。气温一年胜似一年的上升,罗布淖尔变成了一盘大火炉。
风沙开始变得毫无节制。
常常是在夜里,暴雨般的流沙就急促地撒下来,持续而又密集,非常像落雨,沙沙拉拉,把楼兰人从梦中唤醒来。年迈的人唱起了忧郁的歌,年轻人气愤无比地推开柳编的柴门,指天戳地地骂。
但这是毫无意义的。
每一场风沙过后,楼兰城包括城内的所有住房便都要矮上那么一截。城外的村落,总会有那么几户完全被流沙所掩埋。
这些人家从流沙中挣扎着爬出来,犹如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活鬼,叫人触目惊心。
最让楼兰人绝望的是,浩大的塔里木河开始变得有气无力,河面越来越窄,沿岸的胡杨林开始大片大片地死亡,光秃秃的黑色枝干造型古怪而难看。
塔里木河的水到哪里去了?
气候干旱肯定是原因之一。
冰川萎缩也可能是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还是人类自身。
当年注宾河截流,好多国家的人都是参加了的。这使他们开窍,也让他们学到了治河用水的经验。一回到本国,他们也就照着汉朝神人的样子干起来。
这种做法很快漫及西域全境。
楼兰在塔里木河的终端。
而塔里木河的全长是1321公里,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二大内陆河。
在一千多公里的中上游地段,西域诸国都开始向塔里木河要水。他们挖开河岸,引水灌地。
塔里木河流在沙质的松软河床上,极易摇摆,故有“游荡性河流”之称,又有“脱缰的野马”之说。河岸低缓坡度较小,扒个口子就能引出水来。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乌斯曼的牧民,为了浇灌他的一片草场,就在塔里木河岸用坎土曼(一种类似*(左钅右矍)头的农具)随便扒开了一个口子,结果就流成了一条新的河流。乌斯曼的草场当然变成了泽国水域,但这条新的河流却得以以乌斯曼的名字命名。如今,这条乌斯曼河依然流淌在新疆的大地上。
有专家估计,塔里木河三分之二的水就是这么流失的。从空中看塔里木河,中游地段河汊如网,湖沼遍布,沙漠中的一片汪洋。
中上游开口引水,罗布淖尔还可能不缺水吗?
给楼兰人最后一击的,是瘟疫。
这是一种可怕的急性传染病。传说中的说法叫“热窝子病”,一病一村子,一死一家子。这种病的可怕就在于无法预防而又死亡迅速,好端端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就一头栽倒下去,口吐黄水,浑身颤抖,缩成弓虾一般,从发病到死亡,往往不超过一顿饭的时间。
楼兰原本人丁就不兴旺,但这种病一死就是一片,楼兰人是确确实实地怕了。
流传的谣词是这么讲的,借用一下汉族人的称谓,就成了这样的句子:
李四早上埋张三,
晚上李四又归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同赴鬼门关。
于是,楼兰人选择了逃亡。
逃亡的命令是楼兰王当众宣布的,王换上了平民的衣服,泪流满面,苍老得如同枯死了的胡杨树。
他说楼兰国瓦解了,这里也就没有什么王,而只有楼兰人,要活命,就沿着塔里木河走吧,哪里能活命,就往哪里去,能活几个是几个。如果能活,如果有办法,就来看看这里的太阳墓地,那里面埋着咱们的先人呐……
楼兰人失声痛哭,如雷轰响。
这般时节,天色突然昏暗,风沙,风沙,漫天的风沙,搅得楼兰天昏地暗,跌跌撞撞丢魂落魄的楼兰人于飞沙走石之中轰然而散……
接下去的惨景悲情,笔者已经不忍心写下去了。
归总一句话:楼兰死了。无论是早先的楼兰城还是后来的鄯善城抑或汉兵修筑起来的伊循城,都被无情的风沙所掩埋,千年以降,这一片原本“水鸟群飞,鱼跃兽奔”的大泽之地,成了风沙的王国。
逃亡的楼兰人一代接一代地做着楼兰复活重返家园的梦。但梦只能是梦。楼兰人追到的,只是古城消亡家园破碎的残梦。
西域古城探秘/李广智著.-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楼兰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