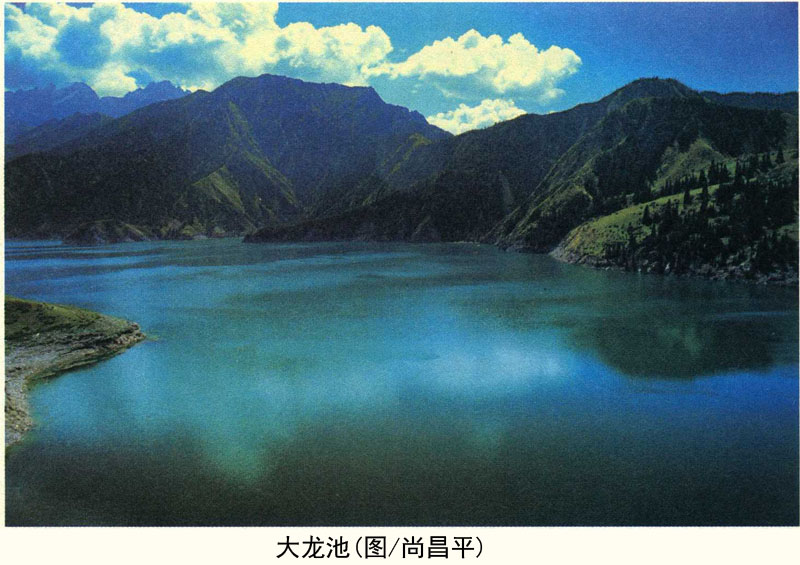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原拥有了工艺成熟的制陶工艺,龟兹学习中原的制陶技术并建立了自己的制陶业。他们的制陶业在西域众多的城邦之国中,属于上流水平。在龟兹石窟中,艺人将制陶的过程绘成了优美的壁画。
陶器在龟兹人民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原始社会尤为突出。195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库车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发掘出了彩陶片、粗砂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可知在新石器时代龟兹已掌握制陶技术,能制作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这里出土了两代陶器,从粗砂红陶器皿到大陶缸,证明龟兹古国经历了历史的演变与飞跃。
龟兹辖境内的轮台群巴克古墓葬距今已有2500~3000年左右的历史,这里出土的均为原始社会时期文物,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等,而以陶器数量最多,主要是夹砂红褐陶,也有少量夹砂黑陶。“均手制,基本上都是素面,仅有个别的饰有凸弦纹或划纹。有的表面打磨光滑,有的则敷一层红色陶衣。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彩处敷黄白色陶衣,其上绘黑色或红色彩绘,以黑彩为多,花纹主要是内填平行斜张的正倒三角纹,也有少量的网格纹,器形以带流罐和单耳罐为最多;另外还有双耳罐、单耳罐、杯、钵、碟、纺轮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陶器的彩绘花纹主要是正倒斜线的正倒三角纹,这与后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图案的形成有渊源关系。
从出土的陶器来看,不仅陶衣色彩均匀、亮丽,而且所饰花纹精致美观,彩陶文化的演变充分显示龟兹制陶工匠高超的审美意识与艺术才华。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于龟兹王都附近的一处高台墩——维语称为买里买契特(即高大寺)——下面发现一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该陶管为红陶细质,只残存下部,尚高4O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略粗为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捏压指头印,约为公元4~5世纪时的产物,埋藏在几米深的红色土层内。可见,到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龟兹的制陶技术已大有提高,能制造大型的、坚实的地下陶管。从黄文弼教授于龟兹王城内的哈拉墩发掘出的33个大型陶缸,更能看出龟兹制陶技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步伐。
在一件出土的佉卢文书中专门提到娑伽莫味,“耶夫村□社土著居民,是陶工遮姆者之子”。说明龟兹古国已拥有自己专业的制陶工匠,有较高制陶工艺水平,否则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外表光平、口径50厘米、高度达85厘米的大型陶缸是制作不出来的。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促进了龟兹制陶业水平的提高,主要反映在:轮制陶中模制工艺技术的出现,新的陶器种类的增加,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以及绿色玻璃釉陶和三彩陶器普遍地应用于家庭生活、佛教寺院和城市建筑等龟兹社会的各个领域。彩陶文化在龟兹民间大放光彩。
这个时期的陶器生产已掌握了选择纯净的陶土、掺和细砂以及和泥、润泥、经轮制或模制的陶坯阴晾干后而入窑的工艺过程。窑炉虽然有大有小,但形制基本相同,主要由窑门、火膛、窑底、窑床、烟道、窑口等部分组成,这种直烟窑的烧制方法是用柴火直接在火膛里烧,通过自然风把火力喷升到窑床而流到坯件,又从陶坯体空隙经烟道排出窑外,所产陶器制品有较高技术含量。大型窑体底径2~3米,通高2~3米,能烧制高达120厘米以上的大型陶瓮或陶缸,小型窑则烧制罐、壶、瓶、杯、碗、盘以及小到几厘米高的微型香料壶和各类动物偶像的玩具艺术品等。
在传统的绘画、刻画、堆塑等装饰纹样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量的模制成形的粘贴、雕塑、镂孔等装饰新工艺。其中,外来的如西亚或波斯的艺术纹样和以浓厚的佛教文化内涵为题材的陶器制品,构思精巧,造型新颖,装饰典雅。其中人物和动物的写实造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玻璃釉陶、三彩陶以及釉陶的砖、瓦普遍出现,展示着龟兹制陶业的卓越成就。
釉陶的釉与玻璃同源,所以古代称彩色的釉陶为琉璃陶。龟兹的釉陶主要是一种低温色釉的陶器制品。釉彩主要是一种单色釉,以绿色、翠绿色为主,少数为蓝色或黄绿色。色釉的主要着色剂是铜或铁,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就其釉色化学组成而言,属于“铅釉”陶系列。龟兹很早就已掌握了铜、铁、铅的金属冶炼技术,石英砂、石灰石、碱的原料又是龟兹分布甚广的矿物,在传统制陶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引进或接受外来的玻璃制造工艺而生产釉陶是顺理成章的。
龟兹釉陶的胎质为陶土,细砂红色,表面釉色光泽清澈而凝厚,有釉陶的罐、盆、杯、盘、壶、豆、灯、砖、瓦当等,其中有的釉陶制品的肩或腹部还贴塑有模制的莲花、忍冬、卷草、联珠、人或动物头像等裁饰图案,显示出龟兹釉陶造型古朴、美观、实用的风格。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王功恪,王建林编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