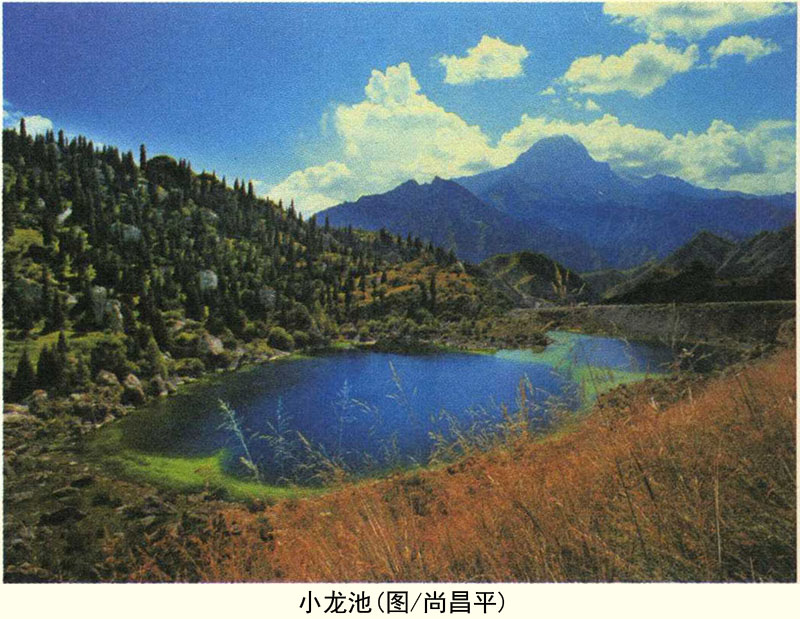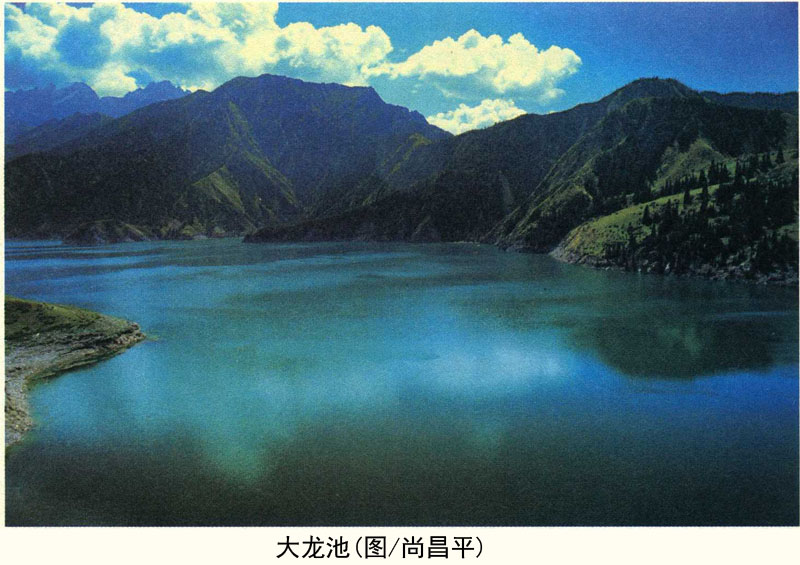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夏朝,最早开创了养蚕和纺织生产技术。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古代史书早有记载。
《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出细毡皮、氍毹。”
《隋书·西域传》载:“龟兹国……烧皮、氍毹。”
《新唐书·西域传》载:“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
由此可知,龟兹凭借农牧区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并且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了距今2500~30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各种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有不同,如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O.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有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O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有26根。为了适应美观的需要,纬线给予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呈纬向彩条。而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厘米,每平方厘米约有4根;纬线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有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颜色多样、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则出土了自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地毯、斜纹组织的斜毯和栽绒组织的地毯。特别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永,工艺精湛,显示了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对于毛织手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托库孜沙来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毯、平纹粗毛毯,以及一些毛布残片等。这些织物基本上都是用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捻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周,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
还有北朝庙址中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Zilak])。其织造方法是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纬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即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拴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扎。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绒,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在菱形内显四个对称的小菱纹。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纺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知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又较多的是通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毛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迄今均色泽鲜艳。考察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所以色泽协调,经久不变。如属于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两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为4根/厘米;纬线直径约O.8毫米,密度为1.2根/厘米。纬线可分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及花蕊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凡是用这种通经断纬方式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隙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古代“施之以墙”的“壁”或称“壁衣”的一种。
这些已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捻,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纬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密度分别为12根/厘米和11根/厘米,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14根/厘米。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承受不同的拉力,从而使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了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的丰姿,显示了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综观这些在龟兹辖区内出土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然色彩鲜艳。这是龟兹民族对中华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原蚕桑传入龟兹以后,龟兹人民又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哈喇和卓88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第阿奴举锦券》记载:“阿奴以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兹中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三十日,偿锦一张半,若过期不偿,胜行布三张。”这里的承平五年为公元447年,“丘兹”即“龟兹”异写。由于三年后,阿奴无力偿还,只好以婢绍女抵偿,因而在同墓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中称:“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兹锦三张半。”并说“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返悔者罚丘兹锦七张”。从这里可知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丘兹锦,不仅流行于龟兹境内,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被认为是名贵产品,价格昂贵。这就可知从汉族地区的织锦技艺传入龟兹,到为当地人民学习和掌握,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最终形成具有龟兹风格的艺术特色,更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出土丘兹锦的文物虽属5世纪中叶,而丘兹锦的最初织出时间必然早于5世纪,最迟在4世纪已经出现。这种绚丽多彩的丘兹锦的产生,既丰富了我国历代的丝绸织品,又活跃和充实了国际丝绸市场。
考古已于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少来遗址出土了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为7~8圈/厘米,纬线较松,平均6圈/厘米。经密25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经线分为交织经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色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母,是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用以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的字母,这种语言文字即被人们称作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
在巴楚托库孜沙来晚唐房屋遗址中还出土了滴珠鹿纹锦,经纬线也均为“Z”向加捻,经线平均4圈/厘米,纬线2圈/厘米。经密2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这是一种平纹双层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互相转换,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这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表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可知龟兹锦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丝绸市场上享有盛誉,就是依靠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点缀在锦面的一些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了它的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
由于龟兹地区的棉花种植较中原早得多,并已在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中原地区则于宋代以后才开始植棉,生产棉布,所以在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中曾出土较多的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大大早于中原做出的一项创造。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5~6圈/厘米,纬线为5圈/厘米。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为经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5圈/厘米,纬线4圈/厘米,经捻大于纬捻。另在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以3/1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它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泽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都是以“Z”向加捻,平均7圈/厘米。这些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往往大于纬线。这与上节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总之,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继承了原有毛纺织的传统,是织绵行业历史上的创举。
从龟兹贵族到农牧民都喜爱的丝绸织物,史籍对此记载甚多:
《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
《旧唐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其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可见,丝绸织物是龟兹王室贵族用以炫耀自己身份地位的贵重衣饰,是很受青睐的一类织物。
此外,龟兹自远古起就开始种麻,在棉布未普及以前,到一千四五百年前,麻布是人们制作衣物的主要面料。龟兹人开始种植棉花,并用棉纤维纺织,在托库孜浙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和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织品,同时还发现了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鉴定为来自非洲的草棉种子,可以作为龟兹接受西方文明的物证。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王功恪,王建林编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