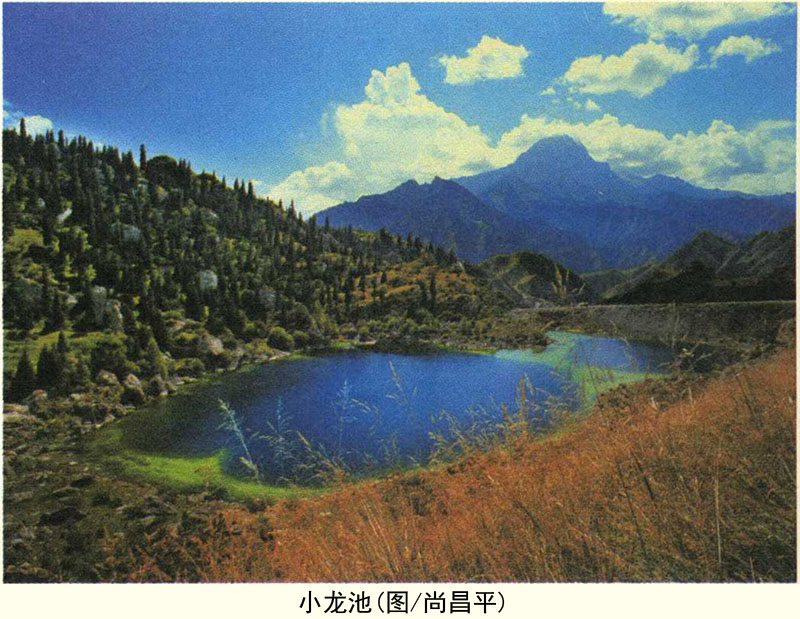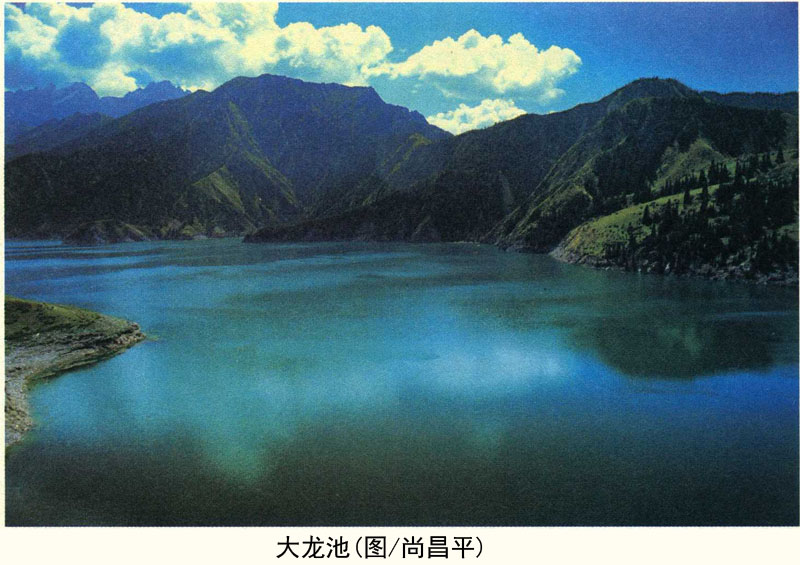语言离不开人种,谁是操吐火罗语的龟兹人的祖先,是一个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一直苦苦追索、悬而未决的难题,是一个人类起源史上巨大而神秘莫测的谜团。在龟兹,由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激流所形成的旋涡至今还在旋转不停,世界上无数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为此殚精竭虑,寝食难安。这将引起求知欲望强烈的来龟兹的旅游者们的分外关注。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龟兹人的祖先是被张骞驱逐过的大月氏人,是一群远古的流浪汉。
月氏又称吐火罗人,或称禺氏,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出现过,经常与“玉”相提并论,《管子》中有四篇提到“玉起于禺氏”。在中国发现的、具有印欧白种人体质特征的骨架和头像,属于吐火罗人,也就是先秦文献中的月氏人。从语言学角度,吐火罗人可分为龟兹、焉耆、楼兰和月氏四大支系,他们在民族大迁徙中各得其所,形成了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塔里木盆地周边发现了大量长颅、高鼻、深目、薄唇、窄脸、头戴护耳光帽的吐火罗人形象。
大约300O年前,吐火罗人集团在塔里木盆地北支向东发展时,受到了蒙古利亚人种群西向发展的遏制。他们在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停留下来,建立自己新的家园,在这里结束流浪生涯,逐渐完成了从游牧经济向安居的绿洲农业经济方式的转变,并与当地土著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民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近10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外来的文化进行了两次大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第一次是向西推进的蒙古人种群体与东进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种群体发生接触与融合,形成两种文化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察吾乎沟口墓地遗存类文化——青铜文化,东起和静县,西到温宿,已发现察吾乎沟口墓葬、轮台县群巴克墓葬和温宿县包孜东墓葬。在稍后的第二次,是由东来的蒙古人、北来的原始欧洲人、西来的中亚的两河类型人和地中海东支类型人,在天山中部地区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接触,形成了四种文化成分的混合类型文化——鱼尔沟墓地遗存类文化,这一交融过程大约经历了近1000年,比丝绸之路开辟时间约早3OO~400年。
经过了1000年相对独立的发展,龟兹、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在库车绿洲和焉耆盆地自然与人种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绿洲文化经济。随着佛教东传,他们又借用了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拼写自己的语言——吐火罗语,并为后人留下了他们历史活动的文化遗产——吐火罗语文书。这些已经由吐火罗人演变成新的民族的“焉耆人”和“龟兹人”使用的语言被称为焉耆语和龟兹语(国际上称甲种吐火罗语和乙种吐火罗语)。比较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吐火罗语是当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欧语言,它暗示着操吐火罗语的古代库车(龟兹)、焉耆、吐鲁番的早期居民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原始印欧人。另一支由塔里木盆地南缘向东发展的吐火罗人,他们一度到中国北部某些地区,成了山陕北部以养马著名的游牧民族,战国时被齐、秦霸主击败,迁到河西走廊。《史记·大宛列传》中曾记载:“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公元前177—前176年,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一带,后又被乌孙与匈奴联军击败,于公元前141年前后越过阿姆河,在巴克特里亚,结束了希腊人长达两个世纪左右的统治,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吐火罗人统治的国家,称吐火罗斯坦。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地为“都货罗国故地”。公元558年前后被波斯占领,沦为萨珊王朝的附庸。大约在568年前,西突厥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吐火罗斯坦,使其成为了一个隶属西突厥的贵霜国,后来发展成曾在东西亚文明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贵霜王朝。
西迁后占据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和焉耆、龟兹的吐火罗人在此后一段历史时期中,彼此之间早已完全失去联系,各自分道扬镳,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几个互不相干的活动中心。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在民族特征上的各种差异不断增加,形成了看似很不相同的民族群体。生活在龟兹、焉耆的吐火罗人已成为龟兹人、焉耆人,不仅保持了更多原始印欧人的特征,而且拥有了能表明他们祖先民族渊源的吐火罗语文献;而在吐火罗民族故乡巴克特里亚活动的吐火罗人,反而不能用语言与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与谱系。这种吐火罗人与所谓吐火罗语在时间与空间上出现互不相关、互相脱离的现象,成了人类语言史上一桩奇案。以致东西方各种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记录如坠云里雾中,或明或暗,语焉不详,矛盾抵牾之处比比皆是,令中外学者感到困惑,称之为世界上又一个诱人的“斯芬克斯之谜”。现在龟兹、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成了对研究印欧文明起源、东西民族文化交流和中亚西域文明以及破解西域文化东西合璧之谜具有巨大学术含量的珍贵文献。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王功恪,王建林编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