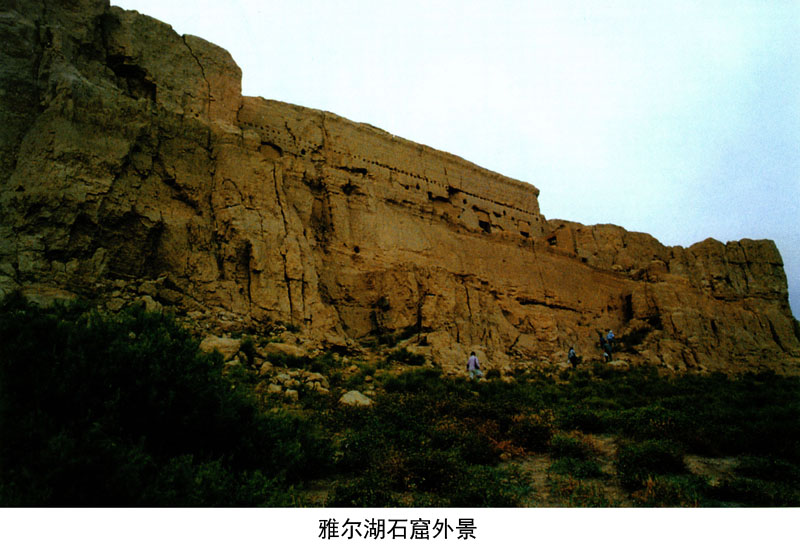“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意气风发的诗篇。他沐浴着春风,踏青而归,已是尽兴却又走入酒店,大笑之时与西域少女相遇又迎来了更高的兴致。据学者们考证,李白的出生地是在中亚,他的祖父辈可能是往返于丝绸之路的富商,他喜与西域少女欢歌笑语是很自然的。他有许多诗篇写这样的内容,说明他喜欢西域的乐舞,如《前有撙酒行》:“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又如《醉后赠王历阳》:“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其实,在唐代喜欢西域乐舞早已是风靡天下的时尚。著名诗人王建就有诗句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其实,不只是唐朝,在唐之前中原就已敞开胸怀欢迎西域乐舞了。早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他就带回了一批西域的乐舞艺人和西域乐器“横吹”、西域乐曲“摩诃兜勒”。
在西域的乐舞中,对中原影响最大的是龟兹乐舞,“摩诃兜勒”就是流行于龟兹国的乐曲,汉武帝非常喜欢,命宠臣李延年加以改造编成了二十八首乐曲供军队使用,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横吹曲”。南北朝时期,前秦大将吕光征服了龟兹后,当地的富庶经济和奇妙的“饶乐”竟然使他“有留焉之志”,不想东归了,后来还是名僧鸠摩罗什和他的部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他放弃了留下来的想法,但他走时动用了两万多头骆驼把当地的“珍宝及奇伎异戏”带了回来。这“奇伎异戏”就是龟兹的乐舞。从这样大的规模而言,龟兹乐舞必然是收罗尽致了,史学上将此称为龟兹乐舞传入中原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是北周武帝时,武帝与突厥公主联姻,突厥将以龟兹乐舞为主体的西域乐舞再一次随嫁带入了中原。这次高潮影响之大,直至到了隋初,还有些大臣提出要以龟兹音乐来改造“雅乐”。以乐治国是儒家的政治主张,龟兹音乐被提出来改造“雅乐”,其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一次虽然没有成功,但隋之后的唐代,“雅乐”还是被喜爱龟兹音乐的君臣们进行了改造,具有浓郁龟兹风格的《秦王破阵乐》在唐初就由李世民下令正式列入宫廷“雅乐”。唐玄宗时,“胡部新声”与“法曲”合并,包括龟兹音乐的西域歌舞名称一律改为了汉名。著名诗人元稹描写宫廷里龟兹音乐的演奏盛况是“色色龟兹轰录续”
龟兹乐舞不仅在中原受到欢迎,唐王朝还将龟兹乐舞作为丰厚的礼物向外赠送。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嫁吐蕃,随嫁的嫁妆中有一部“龟兹乐”。唐玄宗时,玄宗赐给来长安朝贺的南诏王阁罗风的礼物中也有“龟兹部”。
唐以后,龟兹乐舞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四川前蜀王建在他石棺上所刻的24个乐舞雕像中,龟兹乐舞的造型和乐器样式至今还是清晰可辨。到了宋代,由于中原政权的弱小,与西域的交通受阻,龟兹乐舞才在中原漫漫消失。
由于龟兹乐舞曾在中原广泛流行,我国史书上的记载极为丰富,遗憾的是有关的文物却是凤毛麟角,极为稀少。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特别是伎乐壁画中却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翩翩起舞的少女,尽情弹唱的乐手,一幅幅图画,将曾伴李白高歌、曾使唐玄宗倾倒的龟兹乐舞直观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从中找到乐队伴群舞这样的画面。通过学者们的比较,我们发现龟兹石窟的伎乐壁画比印度、阿富汗巴米扬的伎乐壁画还要丰富,这显然是佛教龟兹化的结果。比如,佛教“降魔变”的故事,在印度阿旃陀1号窟前室的壁画里,魔女没有舞蹈动作,而在克孜尔第76窟壁画中,魔女有了舞蹈动作,这就大大增加了魔女的诱惑力。
龟兹石窟壁画中,乐舞的场面往往都很大,造型也比较丰富,这可能与龟兹国全民喜乐爱舞的民风有关。据史料记载,当地有一种大型乐舞活动,名叫“苏幕遮”,这是一个群众性的乐舞活动,每年七八月间举行,盛况空前。乐舞到了高潮时,舞者、观者相互泼水,还用绳索套勾行人,狂欢不已,昼夜难分。也有学者认为“苏幕遮”是在每年十一月举行,意为“乞寒舞”,是为了祈求上天多降雨水,期望来年丰收。20世纪初在库车出土的一具舍利盒,盒周围有一幅乐舞图,许多学者认为就是“苏幕遮”的表演形式。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双人舞的形象显得非常突出。在《旧唐书》的记载中,西域各乐部内舞者均是二人,惟龟兹乐中的舞者是四人。但在龟兹壁画中多为双人造型,可能四人舞是有了中原改造后的成分。龟兹壁画中,或双人共舞,或一舞一乐,这在其他佛教石窟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克孜尔千佛洞第38窟的“伎乐图”是一幅著名的双人歌舞图,可以作为龟兹这类壁画的代表,其中一组,一人击鼓,一人侧身相舞,你迎我送,情意绵绵,生动无比。
由于有舞蹈成分的进入,龟兹壁画中的人物线条都非常流畅,这对壁画的整体效果是很重要的。龟兹壁画的色彩比较重,而且是大色块地运用,这难免会使画面有一种滞重感,可是在与具有动态感的人物相互融合后,滞重感全无。相反,动静互补,相得益彰,画面出现的既有佛教庄严肃穆又有生活浓郁气息的流动韵味,构成了龟兹壁画的一个艺术特色。克孜尔石窟第84窟壁画《吉祥慧裸体女像》就是这一特色的代表。吉祥慧女身体上的用色都是大色块,她舞蹈时的身材匀称硕美,当她右腿微抬、双臂联动而有着修长手指的双手反向轻压时,画面的流动美扑面而来,美不胜收。再如克孜尔石窟第205窟《龟兹贵族供养人像》,许多人只注意画中人物面部采用高反差对比色的特点,其实此画面上人物的造型也是龟兹壁画特色的代表。画面中两供养人下身比较直,而腰身以上开始向右倾斜,至头部又微微向左倾斜,一个浅浅的“S”造型呈现在画面上,有着明显的舞蹈者动作的痕迹。
龟兹国人喜乐舞的民风在壁画中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那就是画面中所出现的乐器。据对克孜尔壁画中伎乐形象的统计,有18种乐器在画面里出现。根据有关史料和乐理的整理,这些乐器大致可以分出三个大类:
第一大类是弦鸣乐器,有竖箜篌、弓型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直项阮咸、曲项阮咸;
第二大类是吹奏乐器,筚篥、横笛、排箫、贝;
第三大类是打击乐器,有大鼓、羯鼓、腰鼓、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鸡娄鼓、铜钹。
如此众多的乐器出现在画面中,真可谓是琳琅满目。乐器题材进入画面,可以作为识别佛教人物的标志,有时也是故事情节不可缺少的因素。对画面而言,也是增加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而且,这一现象不仅是龟兹国人喜爱乐舞民风的反映,也是具有众多文化相互交融特色的龟兹文化的反映。排箫和阮咸来自于中原,弓型箜篌和五弦琴来自于印度,竖箜篌和琵琶来自于波斯。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些乐器,就如同在观看着一场国际文化大交流的交响乐。克孜尔第38窟主室两侧面的天宫伎乐图,画有十余种乐器,伴着乐器还有独舞、双人舞等造型,画面全景俨然是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盛会。
龟兹石窟壁画中乐舞画面的描写。是为宣传佛教教义这一主题服务的,比如克孜尔石窟壁画“伎乐天”和“飞天图”中表现最多的是佛涅槃画面。在佛教中,涅槃是“解脱与快乐”,因此佛涅槃形象显得十分安详。第114窟“焚棺图”旁,就有三个乐伎出现在画面上。
龟兹石窟有关乐舞内容的壁画,生长于龟兹全民喜爱乐舞的文化沃土之中,是民族文化的阳光雨露滋润了龟兹壁画,使千姿百态的龟兹佛教艺术又增添了一朵艳丽的艺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