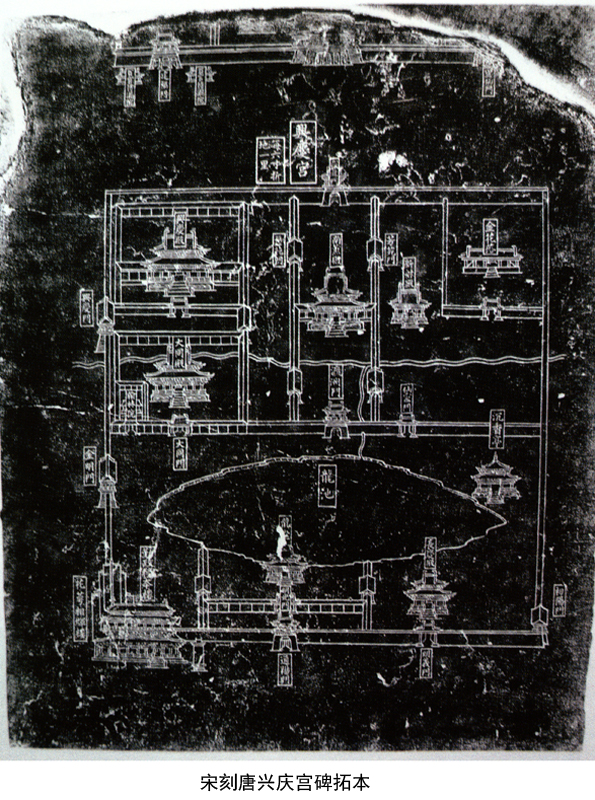在滔滔黄河的中下游,伊洛平原如同恬静酣睡的婴儿,紧紧地依偎在黄河母亲的南岸。“九朝都会”的帝都洛阳,就坐落在伊洛平原的腹地核心。分峙南北的邙山、伊阙,见证了帝王冠冕的翻覆起落;悠悠五千余年的河洛文明,在这里续写出最伟大的历史篇章!
关于洛阳的地理形势,张华的《博物志》称其:“左控函谷,右握虎牢,面对伊阕,背靠邙山”,诚为“四险之国”,有“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之美誉。所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值华夏之邦刚刚迈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时候,洛阳一带就已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域。夏代以后,洛阳先后迎来了九个王朝在此建都的辉煌岁月。作为“九朝故都”,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建都历史中,洛阳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创造了无数“彩练当空舞”的神话。有鉴于此,当崛起于塞北高原的拓跋鲜卑决意入主中原,一统山河的治国方略甫才确定之际,雄踞中原的故都洛阳便立即成为北魏皇室安身立邦、迁都易俗的首选之地。
伴随着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洛阳成为当时东方最伟大的形胜都会;而随着洛阳都会地位的确立,随着汉化政策的逐步推行,崇尚佛教的北魏王朝也不失时机地将旧都平城云冈石窟的雕造余绪,一概移接到新都洛阳以南的伊阙龙门。
应当看到,承接云冈石窟雕造余绪的龙门石窟,大胆继承了云冈石窟的主流风韵,又紧密地同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相结合,渐次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可以看到,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渐,横贯云冈、龙门两大石窟接踵雕造的历史过程,也是它逐步趋于中国化、世俗化,最终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漫漫衍传过程。在这里,如果说云冈石窟的雕造尚保留有明显的域外特色的话,那么,继往开来的龙门石窟则别开生面,完全走上了民族化、世俗化的康庄大道。
南北朝时,南朝汉文化曾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正统。雄踞北方的北朝各代,一直将那里的衣冠制度、礼乐文化,视为自己效仿膜拜的目标,北齐王高欢因此说,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①。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下,东晋、南朝士大夫北上中原方才受到北朝统治者极高的礼遇,从习凿齿、王肃到王褒、庾信,南士入北,无一不受到信赖重用。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自恃为中原正朔所在的南朝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直接影响着北朝各割据政权。而孔武强悍的北朝各政权也不断地以大规模的锐意改革来调整自身并适时接受融合南朝的先进文化。众所周知,北魏拓跋氏在迁都洛阳之前尚是一个处于特殊阶段的先封建国家,保留着浓郁的家长奴隶制制度,而当他进入中原,君临万邦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建立一个相对先进的封建国家,以适应急骤变化的政治形势。拓跋政权明白,要建立相对先进的封建国家,首先需要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太和九年(485)北魏政权所颁布的均田法,正是其改革调整落后生产关系的有力举措。毫无疑问,这一举措解决了长期困惑北魏政权的“土地”、“农民”问题,为加速其向先进封建国家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北魏政权大规模的迁都、汉化以及崇佛方略的推展实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以皇权的威力强制实行大规模的汉化制度。这些汉化制度包括:易鲜卑服装为汉服;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迁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汉姓,定门第等级等等。毋庸讳言,这些汉化措施会遭到落后势力的强力抵制,但落后势力毕竟无法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对抗。在先进的汉文化熏陶下,世世代代习惯草原牧马生活的鲜卑民族终于义无返顾地开始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大步靠拢。窄袖紧身的马背胡服改易为宽袍大袖的汉式着装,自由率意的盘足坐式开始接受严肃规范的汉家风范。在云冈第二期以及龙门石窟中频繁出现的“褒衣博带”以及“秀骨清像”风格,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汉化风潮的产物。
从汉代以降直至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已达三百余年。经过长期与中国儒学以及道家学说既相互渗透借鉴、又相互排斥的碰撞与融合,推崇“游方”、看重“教化”的“天竺佛教”,已逐渐衍化为具有浓郁中国宗教色彩的佛教文化。
西晋末年以来,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天灾、战乱的蹂躏和破坏。史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人民“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连绵接踵的天灾人祸,将无数生民百姓无情地推向灾难深重的苦海之中,满眼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给后来的文人骚客留下了感叹不尽的历史话题。
在这场灾难之中,出身贵胄的世家大族以及崇尚清谈的优秀士人一概被卷入战乱的旋涡,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等才华横溢的诗人都为时所累,惨遭杀戮。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一类哀婉绝伦的凄惨史实,正是那个动荡、灾难、血污时代的缩影。而“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等凄惨诗句所流露的诗人内心的无边慨叹与巨大忧惧,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乱文学激昂不朽的苍茫主题。远避山林的可怜自慰,黄冠袈裟的无奈认同,由是便成为寂寥文士麻醉自己、企求解脱的最佳选择。
与北朝佛教相比,南朝佛教“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其流弊所及,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②。梁武帝时,西域高僧菩提达摩不惜辗转千里,深入中土传播禅宗。那种“一超直入如来地”的禅宗修行方式一经植入信徒心田,立刻激起层层浪花。异军突起的云烟禅宗,迅速成为左右江南佛陀袈裟的风云教派,迫使那个曾经禁锢束缚无数信徒、侈谈累世苦修的小乘佛教不得不自惭形秽,寂然隐退。随着禅宗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惯以空谈为能事的南朝士大夫投其所好,更别出心裁地将中国的“义理”之学与之融合。“禅理并兴”的绝佳匹配,旋即成为南朝佛教的主要特点。而隔江遥望南朝烟雨的北朝佛教,此时“则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及,在乎好刊,而堕于私欲”③。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事佛如狂的北朝各代竞相开窟造像,虽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们的动机,“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④,“甚者贪婪自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⑤。由此可见,侈谈礼佛的虔诚信徒竭尽家珍去开窟造像,并非一概只为“值闻佛法”,更多的是为家消灾、为己求福,在利己思想的支配下,追求“富贵利益”,获取人生享受,才是其隐藏在心中的真实目的。
斗转星移,随着佛教经义在南北朝时代的广泛传播,佛教艺术也逐渐走上了中国化道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中原流韵先是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中初露端倪,接着又衍传至龙门石窟。这种曾被无数学者青睐的佛教像制,在帝王贵胄以及袈裟信徒的极力推崇下,得到了横无际涯的弥漫流溢,并接踵对北方其他地区的石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龙门石窟中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以及弥勒、三世佛、十方菩萨等造像形式的出现,各种雕技自由洒脱的和谐融会,正是这一时期佛教艺术逐次中国化的形象证明。
注释:
①《北齐书·杜弼传》
②③④⑤汤用彤:《汉魏南北朝佛教史》。
竹林七贤画像砖
● 南朝名士放荡不羁,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方式,他们宽衣博带,饮酒服药,看似潇洒,实为躲避统治者迫害的一种方式。此图刻画的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名士,因与竹林七贤同属不羁之士,故作为同时刻画的题材。南北朝佛教艺术一度以南朝士人样貌为参考,创造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