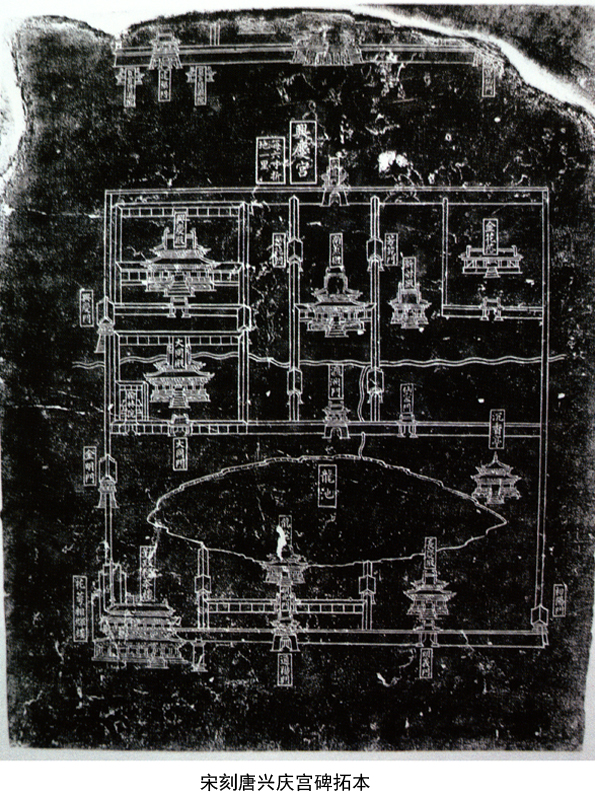在龙门石窟中倘佯游览,卢舍那大佛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处胜景。走过梦幻一般的宾阳三洞,卢舍那大佛就微笑着向你颔首致意。这是一位慈祥美丽的佛界至尊,也是龙门石窟中最高最大的一尊雕像。她位于西山石窟寺群的“正朔”之位,正含情脉脉地高高俯瞰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左右拥立着弟子、菩萨与金刚、神王。静静的伊水,茫茫的东山,仿佛都在她的脚下顶礼膜拜……
贞观之治(627—649)以后,唐代的经济发达,国力强盛,迅速进入巅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高宗李治孱弱多病,使得出身低微、野心勃勃的昭仪武媚娘有机会厕身宫闱,参与朝政。她以狡诈的手段、机敏的应对,逐步扫清前进的障碍,一步步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宝座,进而又跃跃欲试,觊觎天下极尊的“九五之位”。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就是在这样一种微妙特殊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关于卢舍那大佛以及两旁弟子、菩萨与金刚、神王等造像的雕凿经过,历史文献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参考的记载。最重要的依据,惟开元十年(722)十二月补刻于大佛下部北侧的《大卢舍那佛龛记》。其文记道:佛为“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672)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两万贯”。其毕工时间,当在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三十日,而参与造像的高僧大德以及支料的匠工,则依次有善导、惠暕、韦机、樊元则、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数十人之多。
面对这则有名的碑记,面对左右中国历史将近半个世纪的一代女皇武则天,人们兴趣大发,热忱萌生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想象与猜测。
有人根据碑文所谓“大唐高宗天皇大帝”建造大佛与武后“助脂粉钱两万贯”的记载,以及后来唐代皇室在其旁敕建“奉先寺”的示例,认为她是高宗、武后夫妇为太宗李世民祈福所雕。另有人依据同样文献记载以及武后推重武氏家族与其母杨氏崇信佛法的现实,断然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大佛不当系高宗夫妇为太宗李世民祈福所雕,而应改作高宗夫妇为武后之母杨氏雕造较为合适。而更多的人则根据上述同样的文献记载以及武则天弄权朝野并亲率群臣参加开光仪式等史实,很自然地将其与权倾天下的女皇武则天联系起来,并进而参照史书描述所谓“方额广颐”的武则天相貌特征,判定她就是武则天的神秘化身……
众多的学术观点与不绝如缕的猜测想象,使得原本扑朔迷离的卢舍那大佛又蒙上重重迷雾。真正的事实到底如何?哪一种观点更贴近不朽的历史?限于种种缘由,我们一时的确难以甄别判定。但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根据大佛旁侧的碑文记载以及深受皇室信赖的高僧善导、善暕与曾任大使、司农寺兼领将作、少府要职的韦机等人尽皆参与雕造大佛的事实,将其认定为高宗、武后夫妇所合力倡引的皇家造像,则是不致产生错讹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皇家意志的影响与参与,由于众多高僧以及显宦名匠的着意经营,方才使卢舍那大佛以及两侧胁侍的雕造位置、体量规模、造型风格等交相辉映,呈现出恢弘壮观的气势与高贵华美的韵致。
铺像的位置,选定在龙门西山发育最好的崖石壁面上。根据造像环境推测,当年设计者在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进展之前,似先经过侈糜浩大的斩山凿崖以及壁面整修工程,历经艰辛,最后方才得以推出作漏天窟室之制、总体造像呈环状分布、南北宽33米、东西进深38米的壮阔场景。
主尊之位的卢舍那大佛,雕造于环状崖壁的正中,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叠涩式莲座上。座高4.2米,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其头顶饰有波状纹的高肉髻,面相丰满,嘴带微笑,双目下视,颈有三道蚕节纹,身著波浪纹褶皱的通肩式袈裟。大佛之后,有三层圆形头光。最外层饰有火焰纹,其余两层则满饰莲瓣,中层并补饰七佛造像,每佛造像俱各有两身胁侍菩萨。头光之后,复接宽博繁丽的椭圆形背光,自佛座底层直接窟顶。在佛座束腰部位,雕刻有十三身神王,均足踩饿鬼、振臂奋挥。佛座之转角部位,复雕有千佛十一排,每排计十三身。于台座两侧上层,再雕覆莲三层,每一莲瓣,均雕坐佛一尊。在主尊卢舍那大佛两侧,分别雕有阿难、迦叶二弟子与文殊、普贤二菩萨。其间补刻诸多小龛,内雕坐佛、立佛以及胁侍弟子。与主尊相比,弟子像高在10.3米以上,菩萨像则高达13.25米。其中菩萨头戴宝冠,面如满月,温馨恬静地注视着下方。宝冠之后,饰有硕大的桃形火焰纹头光,气韵风格一概雷同于主尊之头光、背光。丰腴秀美的肢体上斜披帛带,繁细的颈饰与交环串接的璎珞以及层层递结的羊肠下裳,尽行凸现出其凝练庄重、雍容华贵的典雅气质,与主尊造像挺拔高耸、凌空俯瞰的博大气势形成极其和谐的反差对比。在对称伫立的菩萨内侧,尚雕刻有阿难、迦叶两弟子。虽迦叶已残,阿难又相对矮小,但其稚嫩的面庞以及圆形头光与微微上提的褶皱袈裟,仍使人隐隐吮吸到雕像本身所折射出来的青春气息。
除了正壁雕刻的五尊造像以外,在环状崖壁的南北两侧,还对称雕有天王、力士以及供养人像。其中天王手托宝塔,高10.5米。力士怒目奋臂,高9.75米。旁侧供养人像虔诚恭顺,亦高6米以上。它们分作两组,遥相对视,成为正壁造像最佳的补充画面。
不管是正壁雕刻的五尊造像以及南北两壁对称雕刻的天王、力士以及供养人像,均相濡以沫,和睦共处。各像的高度,由主尊、菩萨、天王、弟子以至力士,逐次形成明显的递补级差。它们通过环状崖壁的广阔视角,将胁侍、菩萨以及金刚、神王等造像均匀对称地布列于略呈扇形的构图两侧,集中烘托主尊卢舍那大佛的高耸、伟岸以及无上至尊,形成了一幅错落有致、昂扬起伏的壮美画面,充分显示了唐代匠工睿智深邃的设计创意以及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尽管整组造像尚有主尊手残、佛座圮毁、迦叶失形、崖壁漶泐等诸般遗憾,但斑驳的石痕以及岁月的沧桑终究无损总体场景奔涌而出的恢弘气势。极目远望,大唐盛世的赫赫气度以及帝王之家的煌煌丰姿,于此一概缤纷灿烂、挥发无遗!
对视以卢舍那大佛领衔布陈的这组稀世雕刻,无数的人发出过种种的感慨与赞叹,俊美的言辞以及睿智的评介,也不知多少次频繁出现在报刊、著述以及影视画面上,流韵所至,合奏出一曲震耳欲聋的雄壮交响。梁思成扼腕感慨:“此像不惟为龙门数万造像中最伟大最优秀者,抑亦唐代宗教艺术之极作也!”①王伯敏的《中国美术通史》则宣称:“唐代的佛像有许多杰出的创造,然而像奉先寺卢舍那佛这样的作品,却体现了最高的水平”,“通过这尊佛像的创造,集中了多少崇高、美好的生活感受,从而体现着那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强烈愿望、要求和道德、审美的高尚理想,使一具宗教的礼拜偶像成为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辉、不朽的艺术典范”。王逊的《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一文②在历数了卢舍那大佛无尽风姿后,则盛赞:“无论就内容或形式上看,卢舍那大佛的面型的创造都是中国雕刻艺术史上伟大的典型之一”。一位学者更出语惊人:“巨大的卢舍那大佛代表的是当之无愧的峰巅,这个峰巅,不仅是盛唐的,不仅是佛教的,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③。
盛唐之际,国家的强盛与文化的互流已经有机和谐地融会在一起,为佛教宗派的整合分流以及石窟艺术的立异标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体现华严宗教义精髓的卢舍那大佛造像遂开始横溢于丝绸之路的各大石窟之中,在这场浩荡奔涌的文化洪流中,代表最高技艺水平的龙门卢舍那大佛的纵刀雕就,无疑将盛唐石窟艺术的雄壮旋律,婉转抛上了时代的峰巅!
在释解华严宗教义的浩瀚经典中,卢舍那之本意一向被译作“光明”、“净满”,集中表现至尊佛陀的无边智慧,意即通常所谓的“就智为报身”。《翻译名义集》故称:“以诸恶都尽故云净,众德悉备故云满”。关于卢舍那佛宣讲佛法时的情形,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在其所译的《梵纲经》中曾饶有情趣地说道:“我今卢舍那,方坐莲花台,周匝花上,复现千释迦,一花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各坐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千百亿释迦,各接微尘众”。经文中神奇莫测、花团锦簇的壮丽画面,力图把人们带进一个梦幻一般的天堂世界,从而对法力无边,光明净满的卢舍那佛产生极强的敬畏心理,心甘情愿地匍匐于下,诚惶诚恐地接受佛祖至尊的洗礼教化。龙门石窟卢舍那佛的创意雕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宗教基础,竭力欲将人间君主与天堂佛祖对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教化苍生,治国安邦的最终目的。如此独具匠心的创意设计,反映了当时纷纭流行的宗教理念,给人以无限广阔的遐想空间。以至有人突发奇想,将其与武则天为自己取名曰“曌”,希望等同“大慈大悲,如日如月”天堂佛祖的勃勃野心联系在一起,再次倡呼武氏即佛,卢舍那佛即为武氏化身的论断。
调露元年(679)八月十五日,距离卢舍那大佛雕造完工尚不足五年,踌躇满志的高宗、武后再次妇唱夫随,于卢舍那大佛南侧敕命修建规模宏大的“奉先寺”,堂而皇之的祀奉起九泉之下的帝室先人,并将风云一时的卢舍那大佛纳入奉先寺管辖范围,共同接受皇亲国戚的顶礼膜拜。有趣的是,帝后的“奉先”之意,当时的达官贵人似乎并未领会,而千余年后风烟翻滚,关于奉先寺与卢舍那的创制动机困惑了无数多事遐想的文人骚客,使得原本互无干系的大佛、寺院,竟然云遮雾绕地纠缠一起,平添了诸多惆怅、迷茫!
尽管卢舍那大佛受到了人们的多种猜测,但不意并归奉先寺院的历史误会,却使得大佛、寺院从此珠联璧合,联袂受到无数海内外宾朋以及好奇游子的瞩目与想往。从悲愤诗人杜工部,到赵宋哲人文彦博,感慨吟诵大佛、寺院的诗词文赋缤纷迭出,撩拨起其后千余年诗坛文苑的层层浪花。众多的人开始激情满怀地走向洛阳,走向龙门;无数的崇敬、疑问、感叹、困惑开始纷纷扬扬地投向伊水、投向卢舍那……
当清风云烟梦一样飘渺地掠过茫茫丝绸之路以及巍巍石窟寺院的时候,伊水、龙门便起舞人间,诉说沧桑。回首梵音袅袅的岁月,难道你不想再一次地倘佯龙门、再一次地回眸卢舍那吗?
注释:
①梁思成:《中国雕塑史》。
②王逊:《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张健:《卢舍那大佛》,《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18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