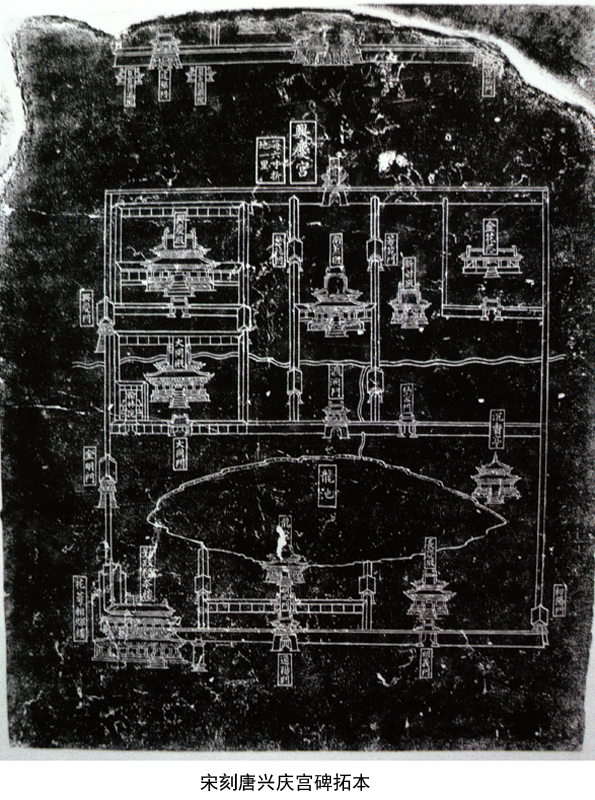北朝时期的帝都洛阳,是丝绸之路上最伟大的国际都会之一,容涵了许多委婉绮丽的动人传说;北朝时期的伊阙龙门,有依附于帝都洛阳之旁最为壮观的石窟群体,留下了两千多个大小窟龛以及十万余尊精美的摩崖雕像。
去过龙门的人,无不为这座艺术宝库的恢弘气势与浪漫风韵所惊愕震颤,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及龙门之外的石窟艺术,提及曾与帝都洛阳荣辱与共、血脉相连的无数座州、郡石窟!
“纷纷洛阳道,南通伊川阙”①。那些仿照龙门模式所相继开凿的州、郡石窟到底有多少座?隐伏在哪一处独占胜景的灵山秀水之旁?它们与帝都洛阳、伊阙龙门有着怎样的血肉情结?每一座州、郡石窟之内,究竟又有多少值得留恋回味的不朽话题?
带着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从唐代著名诗人李峤到清代大书法家王铎,从法国、日本、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沙畹、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阿斯瓦德·西兰到中国学者关伯益、石璋如、阎文儒以至宿白……在艰辛迷茫的历史岁月里,无数贤良俊杰曾经为此做出过不懈的努力。沙畹的《北支那考古图谱》、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关野贞、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阿斯瓦德·西兰的《支那雕刻》以及宿白的《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于是便通过不同的研究层面,集中演绎了北朝时期洛阳之外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较为深刻地解析考证了京畿内外石窟艺术的勾连关系、风格特点以及开凿年代,为世界艺术史章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份遗产。
说起北朝时期洛阳之外石窟寺院的分布、内涵,不能不首先关注洛阳附周的地理环境、人文特征。
从邙山之巅俯瞰洛阳,回望偃师,伊、洛二河宛如一对孪生的姐妹,紧紧依偎在母亲黄河的旁边,而串接黄河以及伊、洛二河的座座灵山、条条清溪,则不啻筋骨、血脉,支撑起故都洛阳的雄浑身姿!
毋庸讳言,这是一片苍茫厚重而又柔情似水的中原大地。这片土地滋润造就了绵亘千余年之久的“九朝故都”,这块土地也生成养育了无数座梦幻一般的石窟寺院。
在曲折蜿蜒的洛阳川纵横环视,许多绝顶佳胜的山崖壁面上,都可以寻觅到北朝时期肇始开凿的石窟遗迹。连绵的战火,岁月的磨泐,曾经湮没了许多石窟的鼎盛辉煌,毁损了无数精美雕像的绰约风姿,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廓清其原本的丰富内涵以及活跃多变的表现形式,然而根据考古工作者近年来陆续公布的最新资料,我们却仍旧有信心大胆宣示:隐伏在洛阳周围横亘百公里山川原野之内的大小石窟,至少有八处之多。它们是:雄踞于邙山东端大力士南麓、坐看蜿蜒洛水的巩县大力士石窟;位于今义马市东南,北依白鹿山、南临南涧河的渑池鸿庆寺石窟;附着在偃师境内寇店村南万安山断崖上,怀抱一脉沙河的水泉石窟;开凿于青要山崖,俯视滔滔黄河的新安县西沃石窟;依山傍水、号称“万佛”的孟县万佛山石窟;镌刻在孟津县谢庄东南峭壁之上,小溪作带,白云当帽的谢庄石窟;营构在嵩县铺沟村南小丘崖壁、收揽伊水的铺沟石窟以及威震虎付山、北眺洛河的虎头寺石窟……
饶有趣味的是,这八座石窟,都紧紧环绕在故都洛阳的周围,盘根错节,首尾相应,作有规律的放射状。距离洛阳最近者只有20余公里,最远者亦不过90公里。它们构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血肉相连、别有一番韵致的石窟艺术环圈,对于留恋关注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的专家学者来说,无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查勘了八座石窟的规模、形制以及造像特征与相关资料,每一个人都惊奇地发现,这八座石窟的始凿年代,全部集中在北魏孝明皇帝之母胡太后执掌朝政的延昌、正光年间(515—520),基本为近似方形的殿堂窟,内部布局又率多摹仿地面兴建的寺院佛殿样式,竟然没有一座比龙门开凿时间更早的石窟,甚至也没有一座与龙门石窟同样开凿在宣武时期(499—515)。
翻开《魏书·食货志》的一页记载,那种所谓“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的由衷感叹,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北魏王朝所醉心希冀的融融盛世;展阅《洛阳伽蓝记》所刻意缕述的些许篇章,胡太后所倡领朝野大造佛寺、“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的恢弘场景,又依稀使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所崇尚流行的无边奢靡之风。
皇权的威严显赫、宗教的强大魔力,将故都洛阳的佞佛狂潮纵情推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得环绕洛阳的京畿之地迅速崛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摩天石窟,也使得后来的人们有能力对这些石窟相继开凿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迷茫宗教氛围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胡太后弄权朝野、炙手可热的五年之间,正是北魏佛教走向极盛的巅峰时期,在这一巅峰时期于京畿之外竞相开凿的大批石窟,不意构成了一个近乎统一规范的石窟群体,它们共同遵守显赫皇权所一手缔造的特定模式,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京畿附周石窟艺术的绝妙风姿!
不可否认,在八座石窟中,除了洛水之滨的巩县石窟之外,其他各窟的规模都体量狭小,无法与号称“帝王之窟”的龙门石窟相提并论。这种外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内在铺像布局以及造像风格的保守拘谨,使得此类小型石窟亦步亦趋、循规蹈矩,紧紧跟随龙门石窟所底定的模式规范,绝不敢随心所欲,放肆大胆地越雷池一步。相比之下,倒是大中型石窟得风气先,率意洒脱,在窟室规模、铺像组合以及造像风格上均独具匠心,呈现出毫无羁绊的勃勃生气。这里,只需择出龙门、巩县两处石窟中主要的造像以做比较,那酷似云冈、典雅宁静、不同于龙门石窟造像清癯消瘦风格的鲜明特征,便足以昭示京畿之外大中型石窟所毅然凸现的倔强意匠。是眷恋旧日平城大漠荒沙的苍凉悲壮,还是要显示自己不同凡响的贵族身份?世事茫茫,寒烟依旧。一切都只能去由好奇的人们猜测想象了!
廓清八座石窟的渊源同异,需要认真地检视一下其中的真实原委。当我们洞悉大中型石窟的开凿者大多是出身贵胄、声名显赫的一代显宦,而小型石窟的开凿者仅仅只是地位低下的比丘、官佐以及可怜生民的时候,一股强烈的震撼瞬时涌上我们的心头。权贵的骄奢、愚民的惨烈,一并渗入拯救苦难的弥陀世界,天上人间一脉相通的森严等级与残酷压迫,于此达到了淋漓尽致的挥发阐释,它所带给漫漫历史长河的,竟是这样一种痛苦、压抑的沉重思考?
步入最为壮阔的巩县石窟,在高大雄浑的五座窟龛中,繁丽的造像与精湛的雕技每每使人为之赞叹,为之留恋。在北魏一代的三处大型石窟中,这座渗透着云冈、龙门雕刻遗风的大型石窟,曾被美术考古工作者视为北魏后期石窟艺术的杰出典范。高大规整的方形中心塔柱,稳稳矗立在洞窟的中央。每一面塔柱的龛饰,都雕造有绚丽的宝帐帷幕,每一处宝帐帷幕,都流淌着轻松活泼的韵律。豪奢的共性与不同韵致的鲜明个性,有机地勾连融会在一起,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它们与窟顶典雅规范的方格装饰以及窟室四壁所精心配置的铺像组合补缀连接,烘托出一幅壮美和谐的动人画面,即便是独领龙门一代风骚的宾阳三洞,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叹为观止!
胡太后执政的喧嚣岁月中,佞佛的滚滚热浪曾经横肆泛溢于京畿内外的千里原野,亲诣伊阙、“躬登(永宁寺)九层佛图”的显赫铺排,倡引带动了疯狂的开窟造寺活动。人间帝后骄奢淫逸的生活场景,地面佛寺殿堂的传真布局,由是便被无数佚名工匠鬼使神差般地带进悬崖峭壁之上的石窟寺院,一线贯通了尘世、佛国之间原本遥远的飘渺距离。巩县第五窟以及鸿庆寺第二、四、五窟独具特色的盝顶式窟顶,无疑是地面殿堂佛龛的再现。此外,地面寺塔中心塔柱以及屋顶平*(上其下朩)的程式做法,也频繁出现在巩县石窟的中心柱窟(塔庙窟)内。而水泉石窟内二佛并立的铺像组合形式、鸿庆寺第一窟壁面与中心柱上部浮雕佛传故事以及许多龛面上广为流行的繁缛装饰图案,都尽可以在寺院殿堂壁画以及雕饰中找到实例与证据。众多的例证与不争的事实,引发了一个幽默含蓄的活泼话题:八处石窟,都是一个特定时代不意并出的呱呱婴儿,它们共同的温床以及赖以滋养的土壤,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北魏王朝以及号称“帝王之窟”伊阙龙门!
太和十七年(493)以后,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逐步推展了大规模的汉化方略,举凡都城的规划设计、舆服的范式制度,无不紧跟“正朔所在”的烟雨南朝。弥漫全国的汉化风潮,回旋在黄河之北的广袤疆土之上,同时也渗透进“脱离红尘”的佛国世界。浸润着胡太后骄奢淫威的永宁寺塔基中所出土的大量秀媚恬静的泥塑佛像与俊美侍者、巩县石窟中精美绚丽的中心柱飞天、平棋藻井以及栩栩如生的礼佛浮雕与雕刻成直平阶梯状、倾覆佛座、状如悬瀑的衣袂下摆,八处石窟内所有造像的清癯面庞、微笑神姿与宽绰衣带,水泉石窟内引人注目的翼形龛面以及形形色色的天人、狮子与装饰花纹,无一例外地荡溢着来自江南的清漪晨风。文化的碰撞、民族的融合,犹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横无际涯地越过帝王人主用钢刀、战马所强制设定的重重封锁,流淌在大江南北的万里疆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石窟艺术,呈现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没有去过龙门的人,在其一生的审美情趣中,必然缺少一节弥足重要的艺术链条;去过龙门而没有光顾环绕在它周围的八处石窟,更难以享受诸多缤纷灿烂的美的洗礼。似水流年的岁月里,古老的丝路与斑驳的石窟常常会默默回顾那些已经悄然隐去的历史陈迹。遥望滔滔东去的伊、洛、黄河,细数洛阳周围满目苍凉的窟龛雕像,千余年不竭吹来的浩荡雄风,每每会撩拨萦绕你勃勃跳动的胸襟心脏,晓风残月里,不知你是否想起了灰飞烟灭的一个王朝,想起了竭诚凿刻了八座石窟的无数佚名工匠的不朽魂魄!
注释:
①唐李峤《清明日龙门游泛》,《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