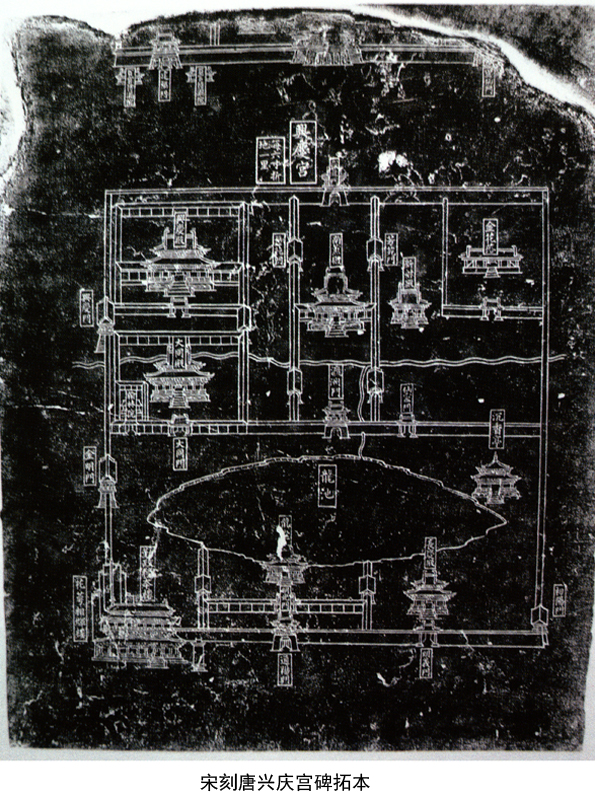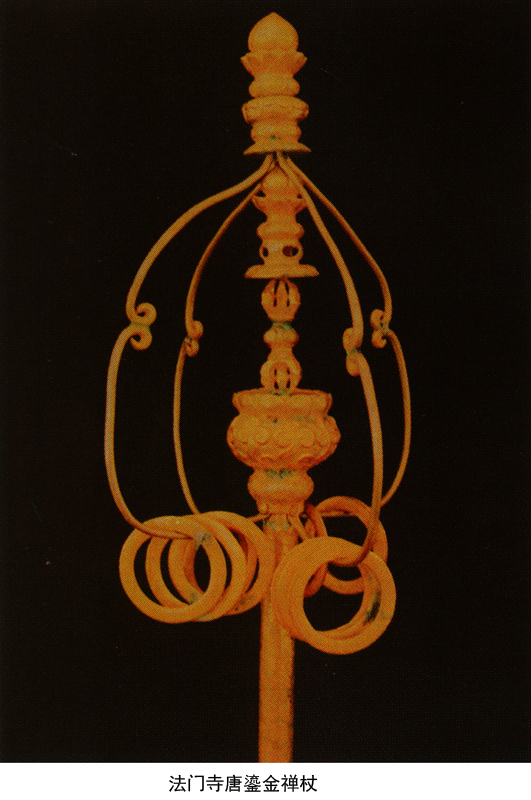公元577年,仅仅只延续了26年的北齐王朝,在宇文北周以及江南陈朝的合力夹击之下,宣告覆灭!
曾经喧嚣一时的上都邺城、下都晋阳,伴随着北齐王朝的倾覆瓦解以及北周王朝铁血废佛政策的强制推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沟通上、下两都的漫漫太行御道,违心辞别了旧日帝王的仪卫旌旗、车马冠盖;当年经声蔽日、袈裟如云的南、北响堂山以及天龙山石窟寺院,悄然半掩了通向极乐世界的朱红大门。
从577年北齐灭亡,到581年隋代建立,在“一片痴情万仞墙”的落寞寂寥之中,失去了国都地位的邺城与晋阳,遥望河洛,环顾幽燕,苦苦等待了整整三年。
“周氏德衰,隋国建号”。是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大倡佛教的微妙国策,为落魄无奈的废都袈裟,注入了一缕欢跃、亢奋的活力。
衔怨含怒达七年之久的天龙山石窟,再次撞响了启迪“解脱之门”的悠悠晨钟!开皇四年(584)震动旷野的石窟开凿之声,惊飞了栖息在这里的寒雁、野凫!一如前代的中心柱开龛造像形式,衣薄贴体的“曹家样”服饰雕刻……刀刀凿痕之中,凝结着眷恋故国的一片真情。大隋弥陀的豪壮之音,裹胁了太多太多的前朝旧韵……
天龙山石窟所遥相呼应的是郁郁寡居在潇潇风雨之中的南、北响堂山石窟。
王朝更迭的板荡风云,沙门荣辱的恩恩怨怨,灰暗冷淡了鼓山之巅的无边林木。开皇元年(581)至开皇十三年(593),当长安城中倡导佛教、“修复周武所毁佛像遗经”的连篇诏书蓦然走进滏阳河谷地的时候,曾经蒙受过浩荡龙恩的一川袈裟,洒下了悲喜的泪水。重扫寺门枯叶,再烧殿前香火。当年沐浴过无限风光的一脉鼓山崖壁之上,再次迎来开龛凿窟的伎作工匠以及求佑祈福的捐赀施主;而镌刻在响堂山石窟崖壁之上的《滏山石窟之碑》,则永远留下隋文帝杨坚献媚佛教的证据……
在天龙山东、西两峰隋唐所开凿的所有石窟之中,始凿于开皇四年(584)的东峰第8窟与开凿于盛唐时期的西峰第9窟,代表了隋代复法以后天龙山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也许是首先浸润大隋开国昌隆气韵的缘故吧!姗姗迟到的东峰第8窟,雄大的规模赫然跃居了东峰石窟的首位。窟室的正面,雕凿有列柱式的窟檐,将北齐时期仿地面建筑的独特手法更加准确、逼真地表现出来,似乎是想在激烈动荡的国体变更之后,决然抛弃虚幻的遐想与无谓的空灵。窟内的中心塔柱,虽然继承了北齐时期四面开龛,简约、明快的雕凿技艺以及已趋程式化的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铺像组合,但细腻繁冗的四面天幕、精密艳丽的图案纹样,却已经明晰地昭示世人,这万像林立的佛国世界,再也不是前朝旧代那样高不可攀的一片神圣。晨钟暮鼓的虔诚礼拜过后,不管是至高无上的佛界弥陀,还是日食斗米的芸芸众生,需要弥补的,应该是这斑斑点点、来之不易的“人间烟火”!
步接隋代石窟开凿的主流风韵,位于西峰的第9窟是整个天龙山唐代石窟一枝耀眼的奇葩。
精确无误的堪舆意匠,促使它稳稳荣膺了天龙山石窟的中心位置。顾盼两翼大大小小的各代窟龛,得风气先的大唐气概,要的就是这样包容一切、敢于扛鼎的泱泱风范。三重密檐的巍巍高阁,朱白晕染、斗牙勾结,俨然是都邑宫阙之内的建筑翻版;上、下两层壁面间雕高达8米的倚坐弥勒以及錾崖5米的十一面观音,左揽乘象普贤菩萨、右拥骑狮文殊菩萨,挟云游雾、妍丽丰腴,独占了人间天堂的无尽风流!
在北响堂山大小重叠的9座石窟之中,隋唐以降陆续开凿的窟室就有6座。先不要说窟形的样式如何简洁、明快,造像的风格如何繁丽精细,铺像的集结又是如何比例匀称、井然有序……单单远远对视一下9座石窟的排列组合,就兀自会让你产生不同凡响的特殊感觉。
与北齐时代3座石窟的定位意匠相同,隋唐石窟窟址的选择确定,都是结构最好的石崖壁面,计算精密,细致考究,决不贸然从事。它们和北齐3窟毗邻作伴,形成了一组相濡以沫、错落有致的石窟寺群。不管从哪个视角审视北响堂山石窟,都找不到生硬、干涩的感觉。
面对如此和谐壮美的悠悠画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是如何仆仆风尘地往来穿梭在这陡峭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勾画出拙滞厚重的笔笔窟形墨线?然而,我们却完全有理由大胆地推测,那最后给予响堂山留下千古不朽石窟艺术的定格者,就是曾经参与北齐响堂山石窟设计的僧人、工匠以及有关官吏。
伴随着响堂山、天龙山袅袅梵音的和谐旋律,崇尚“符咒”的冠服道教,也同样迎来云开雾散的隋唐盛世。
开凿于盛唐时期的太原晋祠龙山石窟,是中国道教石窟中最杰出的典范之一。袍服冠冕的元始天尊,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两侧的金童玉女,亭亭站立在肥硕饱满的覆莲台上。窟形的确立、像式的仪则,虽说有越轨抄袭佛教制度的诸多嫌疑,但雍容的气度,娴熟的雕技,却绝不逊色于荣辱相伴的沙门“伙伴”。
浸润着隋唐盛世的开放襟度,远离太原的“鄙邑”吉县、深藏于太行山中的小城平顺……也相继开凿、兴建了形式各异的寺院与石窟。
号称“七院”的平顺宝岩寺,每院都有形形色色的大小窟龛,每窟都有仿木构建筑的庑殿式前檐。窟龛的形制,造像的气韵,保持了浓郁的“响堂山、天龙山样式”风格。斗转星移,王朝更换。响堂山、天龙山石窟的每一次新潮涌起,都会使宝岩寺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16世纪初期,这种愈演愈烈的仿木结构石窟建筑形制,仍隐隐散发出从太行山迢迢山道流淌而来的旧都余韵。
劫灰已尽,魂魄不灭。历史饱享了隋唐盛世的无限风韵,历史也看惯了隋唐盛世之后的残风败月!
离开天龙山石窟的主体位置,攀登北坡走向山谷一侧的史家峪,去光顾古老苍凉的福慧寺。保存在这里的3座唐窟,窟室与壁龛狭小、简陋,造像与样式低矮、猥琐,已经不堪与大唐盛世的优秀典范所相提并论了。
与北坡遥遥相对的南坡柳子沟滩地悬崖上,还有五代至元、明时期的5座石窟。纵目一线狭小简陋的石窟形制,我们确实不忍欣赏这里拘谨刻板,呆滞麻木的可怜造像。盛唐之后的州郡石窟,竟然是这样的僵硬、孱弱,它所无意为世人标示的,该将是怎样一个苦涩难言的无奈结尾!
也许在五代以后决策设计雕造石窟的时候,倡导者尚煞费苦心地去辗转“劝化”、摇唇鼓舌,希望递接天龙山一带的龙脉风水,求得千古不竭的宝车、布施与缕缕香火。
也许觉得錾崖作窟已经不能超越前代古人所创立的样式、风范,于是就重起炉灶,寻求建造寺庙、经幢这样的方式来寄托自己对佛国世界的坚贞、痴情,希望响堂山永远声名远扬,不要被湮没、沉沦。
毕竟已是车马稀少,路人罕见的深山佛门了。毕竟不再是帝都龙恩笼罩之下的皇家寺院了!
“抽尽万家资,难补壁间佛”。那些竭力依靠“慷慨捐纳”与“减割家珍”所集聚起来的施主资财,只能雕造小型的石窟、低矮的佛像。虽说部分雕像尚出手不俗,刀工技艺还算犀利流畅,但窟龛的装饰、造像的配置却远远无法与昔日典雅尊贵、豪奢华丽的皇家气魄相比拟。
“拍遍旧宫墙,何处听春箫”。放眼废都之地凿建的数十处石窟、寺院,除了能在题材、形式上稍加修改外,没有一处敢于与当年高齐的石窟艺术抗衡媲美。滚滚红尘弥漫下的州郡小邑石窟艺术,能够夸口迸发出风情万般的世俗旋律,却抱愧不能追逐帝王贵胄所率意操纵的宏壮交响!
“晋阳西山何茏葱,蜿蜒磅礴真天龙。白道之南贺六浑,赤光紫气生英雄”。迷茫的岁月更迭到了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诗人陆以谦还在自己那首《高欢避暑宫》的七言长诗中,仰天赞颂横刀立马、底定高齐千秋基业的“鲜卑小儿”①“贺六浑”②。
短短氤氲26年的北齐王气,竟然“流芳”了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除了凿刻在青山崖壁之上的无数佛陀造像以外,还有谁敢于出面为不可一世的枭雄高欢作刻骨铭心的“功过”评说?
漳河与汾河裹挟着历史的尘灰泥沙,日夜不息地向黄河流去,似乎是想送回留待在这里太久太久的拓跋魂灵。
天龙山、响堂山畅开沉寂已久的皇家御道,年复一年地翘首盼望,似乎是想招回流浪在外太多太多的两都血脉。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太行儿女走出大山,去寻根问祖,去浪迹天涯。
于是,一队又一队的游历、探险者来到这里,要拜谒旧都废墟上的残垣断壁,要叩击两京石窟寺内的晨钟暮鼓。
“折戟沉砂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在晋阳、邺城无边落寞的袅袅烟云之中,哪里是北齐朝野冠盖出行,红尘慰佛的喧嚣之处?
“残灯败寺埋荒草,一柱高香无处烧”。在天龙山、响堂山饱经沧桑的巍巍崖窟之内,哪里是高氏父子皇辇落地、祈福求佑的足迹所在?
龙盘凤翔的晋阳、邺城,愁煞了多少叹流年往事、“发思古之幽”的文人才子?
丰姿绰约的天龙山、响堂山石窟造像,吸引了无数探极乐之路,寻解脱之门的施主、香客以及游人!
有人慷慨发愿,欲除百年薄产,捐助佛寺修葺,达到功果圆满……
也有人暗自盘算,欲藉荒年乱月,盗凿錾崖佛像,牟取不义之财……
从此,天龙山与响堂山在罪恶的魔手袭击之下,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在浩劫之中,响堂山是最早被盗贼光顾的石窟寺群之一。据有关方面统计,最晚从清代开始,前来这里的盗凿者就有数百起之多。
在浩劫之中,天龙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石窟寺群之一。其中最优秀的第14号窟唐代作品,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盗凿。原本富丽堂皇的一座艺术宝库,已是盗痕斑斑,宝去窟空!侥幸遗留的东壁菩萨,首断肢离,奄奄一息,无力再作可怜的哭泣。
被称为天龙山石窟之最的西峰第9窟,精美绝伦的胁侍菩萨,被盗凿者锤敲斧击,断头残臂、遍体鳞伤,令人不忍卒视……
曾经兴盛一时、为无数游人赞不绝口的圣寿寺内,生动传神的泥塑金刚力士被割去头颅,截断双臂,只留下顾影自怜的残缺身形,犹自在作愤怒的呐喊……
野蛮残酷的盗凿,使数以百计的精美造像,瞬息之间被凿离崖壁,流失域外,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面对疯狂的盗凿活动,中外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1931年5月,山西铭贤学校外籍教师威尔逊博士愤而致函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称其“春假内,往游天龙,见其洞内石形人物,大半被人盗取,所余者多不完全。甚至洞内石顶,亦由古董商人以暴力套取。现在石形人物之碎片,仍多散地上”,思之令人心伤,“深望政府设法保护,免致再遭蹂躏”。对于非法之徒为牟暴利,“贩运出口者,均应一律严禁”,以儆效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收回被盗造像、古物,威尔逊博士甚至慷慨表示:“至修理收买之费,如须向外国劝募,甚愿助力”③!
与威尔逊博士的慷慨陈词相呼应,同年5月16日,上海《申报》特在显要位置刊登太原通讯,揭露河北商人“王赞亭贿通天龙山看守人,将造像凿取,运出晋境”的卑劣行径,呼吁当局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以遏止野蛮盗凿之狂潮!
为惩治犯罪,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国民党行政院遂于1931年6月发出训令,要求“内政、教育两部妥拟实施保存及追回失物办法”,并“通行各省、市政府切实办理”。复令“山西省政府转饬地方官署切实保护,以免再有遗失”!
在国民党政府的严令追究下,坐镇山西的阎锡山匆匆于1932年成立“太原县保存古迹委员会”,并下令该会妥善保护天龙山古迹,“励精求治”,“毋再使珍贵、优秀的千年古物,失之一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阎锡山成立组织,连下命令的同时,天龙山又再次发生野蛮残酷的大规模盗凿活动!疯狂的盗凿者不仅盗凿了造型优美、价值连城的佛教造像,甚至连石窟之内的飞天、柱头等细小装饰雕刻也不放过,一并刀砍斧凿,席卷出境!
北京城内散发着清幽墨香的琉璃厂书肆,迎来了如约前来购买天龙山佛头造像的日本商人。祖国的文化,民族的气节,在毫无廉耻的败类面前,显得是这样的惨淡苦涩、苍白无力!
寡居在英国维多利亚·亚伯特博物馆内的持莲菩萨、瑞典远东博物馆内的菩萨头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以及宾州大学博物馆内的持炉罗汉与声闻立像,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痛抚伤痕,嘤嘤哭泣。
流浪在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学院、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内的伎乐飞天以及供养人像,幽居深宫、隔海望乡,日夜盼望能够回到生它、养它的晋阳、邺城,饱饮一口清澈透亮的汾河河水!
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徐炳昶等人鉴于响堂山石窟屡遭破坏,急需准确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来制订保护方案,遂派何士骥、刘厚滋等人对该石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察活动。全部资料后结集成《南北响堂山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文公开发表,成为中国学者最早对响堂山石窟进行科学调查的嚆矢。
步中国学者的后尘,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派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队对响堂山石窟进行了勘测调查。他们的成果《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文,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有关刊物杂志上,产生过一定的效应。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当时正对中国北方实施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使得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的所谓考察,波诡云谲,至今仍留下诸多令人疑惑不解的阴影。
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响堂山、天龙山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以及维修活动。1961年后,国务院先后正式公布响堂山、天龙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划拨巨款对两地石窟实施维修。
饱经忧患的响堂山、天龙山石窟,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当德高望重的古稀老人谢觉哉奋力登上天龙山最高峰巅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已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天龙山石窟。抚今追昔,这位风尘一生的革命者禁不住热血沸腾,欣然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游天龙山》诗篇:“天龙石窟比云冈,塑制较精名稍隐。海盗劫取佛像首,廿一石窟无完整。悬崖瞻视难上下,矮松如龙凤凄紧。古迹修复新余事,记取此时游者影”。
这是一首多么感人肺腑的诗篇啊!它揭示了响堂山、天龙山过去千年不朽的历史画面,又昭示了未来岁月中响堂山、天龙山的美好前景,给人的感慨是永久而又沉重的。
“记取六朝伤心事,隔江不唱后庭花”。漳河与汾河裹挟着历史的尘灰泥沙,依旧在日夜不息地向黄河流去,然而,通向天龙山、响堂山的千里皇家御道,还须再作年复一年的翘首盼望么?
“吟罢两都乘风去,还将余绪付河滨”。当黄河之水再一次勾连萦绕茫茫无垠的丝绸之路的时节,新的世纪便赫然揭开了历史的全新篇章。极目远望,它已不是高齐王朝随心所欲统领邺城与晋阳的时候了!
注释:
①《北齐书·神武帝记》。
②高欢鲜卑名。
③1931年行政院关于切实保护太原天龙山石造佛像免遭毁损事致教育部第2741号训令。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参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