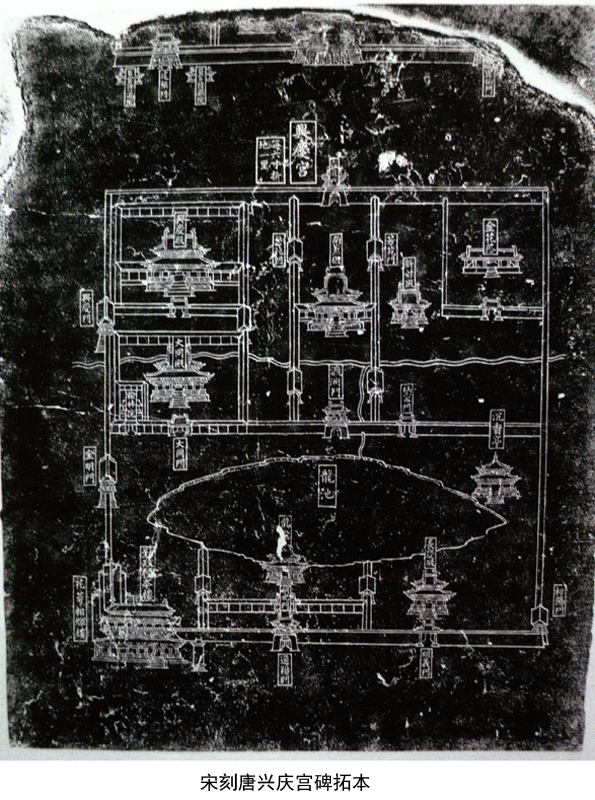独揽大权的宇文氏随着西魏国力的与日俱增,乃至抗衡于东魏,他不再需要西魏元氏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招牌,557年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北周时期的石窟造像步西魏之后尘,以小石窟的开凿和造像碑为主。关中北部宜君县的麦洛安石窟、花石崖石窟、陕北高原榆林县开光城下的6个小石窟,以及神木县虎头峁的两个摩崖造像龛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石窟。窟中造像方拙短壮,头大颈粗,雕刻疏简,明显地由北魏后期造像面容的瘦削清癯,转向面容的宽肥圆硕,具有北朝晚期向唐代过渡风格的特征。与北周石窟造像的演变相一致,北周石刻造像雕造粗略,大多是除主尊、胁侍和供养像外别无其他雕饰,显得粗放简朴。
代表东魏、北齐造像最高水平的是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中的造像,一反北魏后期的“秀骨清像”模式,体态由修长转为匀称、健硕,面相由清秀转向浑圆、丰颐,长颈削肩变为短颈宽肩,面貌神情由清俊灵彻显为朴实敦厚,服饰由“褒衣博带”式袈裟转而多用敷搭双肩式袈裟,一派强劲、敦实、厚重的北方风范。天龙山石窟的东魏、北齐时期造像,较多地保留着龙门、麦积山北魏后期的特点。这两处石窟雕造精细,衣裙褶襞富有装饰性,造像周围的雕刻趋于繁缛。
北周与北齐在造像风格上虽然都有向丰圆、敦厚发展,脱去北魏相式轨范的共同特点,但一个粗疏,一个精细,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北齐本身的造像也存在着遵循和背离“龙门模式”的差异。这些趋同和差异实际上与上层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齐由高氏军人集团执政,他们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川六镇”,由于长期边疆地区的驻扎,深处拓跋鲜卑的文化氛围中,意识已经鲜卑化,尽管他们出自不同的民族,但他们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鲜卑。虽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但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六镇已不受时局重视,几乎是文化孤岛,鲜卑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思想的主流,这使他们更向鲜卑文化靠拢,被目为“鲜卑”也就不足为奇,所谓“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①当他们由鲜卑文化单一色调的北方走向汉文化绚丽多彩的中原时,他们必然倾倒于汉文化的无穷魅力。此外,高欢起兵据邺时,完全可以自立为主,但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难凭一己之力号令诸侯,只得推孝静帝为主,是为东魏。为了能安国顺民,壮大力量,高欢高氏集团不可能推翻北魏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思想而改弦易辙,这样高欢高氏集团,不管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东魏,还是禅代东魏政权之后的北齐,都遵从北魏正统,接受学习汉文化,正如《隋书·音乐志》所说:“齐神武霸迹启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东魏、北齐一如前朝继续提倡佛教,中落的洛阳属于东魏版图,它直接对东魏产生影响,佛教文化势必以北魏后期为规范,因此这时期开凿的晋阳天龙山石窟保持了龙门的造像特点,佛、菩萨身躯修长,衣裙宽大,温文尔雅。然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方民族气质已经融入高氏集团的血液之中,“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清丽难以销蚀豪放粗犷的北方民族性格,在压抑中蓄积太久的鲜卑文化能量终究要找到释放展示的舞台,于是那些“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②的造像出现在响堂山石窟中,那些面形浑圆、眉梢低下、身躯粗壮、下肢略短的造像,似乎就是北方民族的身形,而供养人的普遍胡服装扮,则无疑反映出鲜卑文化习俗的卷土重来。
同样,北周宇文氏出身于六镇军人集团,没有经受过孝文帝改制的洗礼,拓跋鲜卑的思想文化在他身上可谓根深蒂固。他把北魏的灭亡归罪于汉化改革,因此便“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以为心”,回复到孝文帝改制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政治局面。当时北周长孙俭曾出使后梁萧察,“大为鲜卑语”,令南人不知所措,“惶恐不敢仰视”③。在宇文氏“摈落魏晋”的皇家意志驱策下,人们的审美风尚也发生了转变,由对清秀文弱的阴柔之美的崇尚,转为对雄浑刚健的阳刚之美的追求。于是,那些身粗短、面丰圆的造像就出现了。
北周与北齐造像沿着共同的趋势发展,却产生了粗疏和精细不同的风格。究其原因,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开凿在东魏、北齐的两个政治中心也即佛教中心上都邺城和下都晋阳,当时这里云集了洛阳的沙门和工巧,它们的开凿承接了龙门的皇家水准,更何况,它们本身就是由皇家出资建造的,自然具有皇家端庄华美的气度。而以关中为主要控制地的北周,地狭民贫,石窟石刻多由县令和太守以下的地方官吏及乡邑民间投资建造。由于力量单薄,加上关中地区传统的雕刻手法,故大多雕造粗略,显示出拙朴粗放的民间造像特征。这种特征虽然在关中具有普遍性,但随着北周发展壮大,国土日渐扩张,东面楔入洛阳,西南拥有川蜀,南北交通趋频,外来的影响使它产生潜在的变化。四川成都万佛寺北周时期的造像,衣褶密垂,璎珞满身,雕刻精致,这对于北周都城长安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安在当时出现了一批汉白玉造像,制作精良,雕造细致,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造像水准和京城最高宗教集团的审美意趣。
从来“模式”、“典范”就意味着一种创作的极致和规范,它束缚创作,更束缚创新。它带来的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以千篇一律的面目出现,而缺少勃勃的生机。东魏、北齐由于“咸遵魏典”,处于龙门模式皇家典范的追随之中,缺少率性而为的自由。西魏、北周虽处在凉州、云冈和龙门三大模式的交叉辐射地带,但相对封闭的地域使它没有受制于其中的某一种模式,从而拥有创作的自主权。那些分布于乡间山峁细流间的小石窟和挺立在道口路旁的造像碑,因疏离了“模式”、“典范”的羁绊和皇家意志的干预,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活泼的创造力,由此成就了它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强烈的汉文化色彩、兼容互渗的不同宗教、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它如同一位素面粗服的乡村姑娘,粗糙的外表下,却有着最天然淳朴的本质。自然、随意的造像,古拙、质朴的雕刻,耐人咀嚼,令人回味。它以原始的生命律动镌刻着我们永久的回眸,它造就了永远的长安!
注释:
①《北齐书》。
②阮元:《鲁颜公“争坐位帖”跋》。
③《周书·长孙俭传》。
北周宇文泰墓
● 宇文泰(507—556),西魏大臣,曾拥立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大权在握,炙手可热,可惜如今已是黄土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