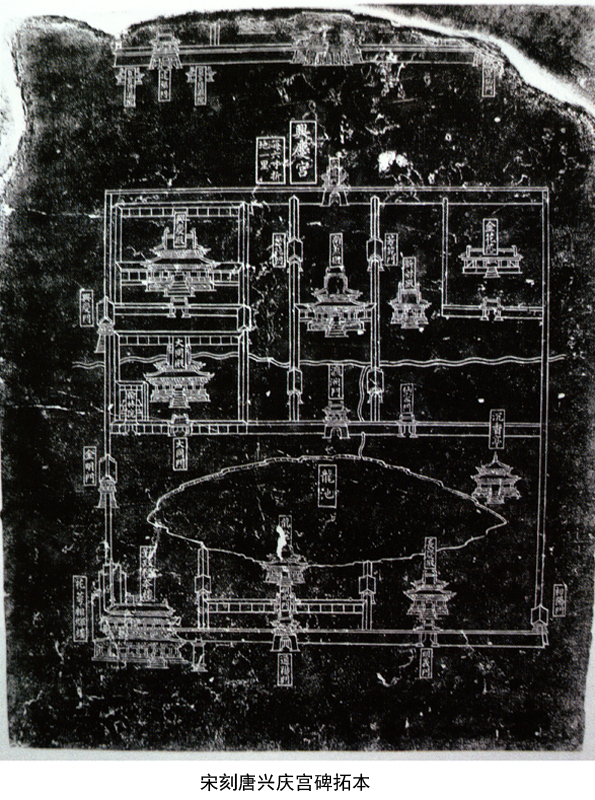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如此包容几千年来两个不同宗教既斗争、又融合,忽而亲同兄弟,忽而干戈相向,恩怨不绝的艰难成长过程;历史上也没有哪一处地方这样荣幸地承受了三次佛道“法难”从酝酿到发生,从流血到和解,时而和风细雨,时而雷电交加,高潮迭出的争斗洗礼。
在中国宗教历史上,佛、道是两大最具风采、最有活力、最富世俗韵味的不朽宗教;而在世界范围内的王朝历史中,长安则是一个建都时间最长、人文最为繁盛、遭受磨难最多的忧患城市。
打开中国任何一部历史典籍,谁都会清楚地发现这两条滞重风趣的历史轨迹:
公元446年、574年以及845年,在这三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及唐武宗李炎相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毁佛灭法”运动,斗争的起点,都是从长安一地发难展开!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65)以及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经过这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佛与道这两个最大的王牌宗教,在不断斗争、不断融合的微妙关系中,终于顺利地到达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理想阶段。融合的终点,又最后归结到了长安!
多么残酷而又风趣幽默的历史轨迹!多么坚强而又柔情似水的帝王之都!它所带给今人的,该是怎样的感慨?怎样的沉思?
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传统道教尽情沐浴着“神仙”的光芒,悠然沉浸在吟诵《道德经》所带来的无限陶醉的时候,一个外来的佛教却悄悄“举着中国神仙的旗帜”①,沿着各条孔道,川流不息地进入到了中国的腹地。“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两千年来残酷斗争,不断融合的恩怨佛、道,就是这样温文尔雅地共同拉开了走向辉煌的绵绵序幕。
争斗的战场,首先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相继展开。
西晋永宁元年(301)以后,一个名叫张轨的凉州刺史,别有用心地开始了自己容纳佛教,教化百姓,以图割据的宏伟计划。
羌笛悠悠、黄沙滚滚的千里河西走廊,奏起了沙门遮道、伽蓝不绝的雄壮交响!
音响惊醒了正在长安城中“焚香、发符”,集众“奉道悔过”的长安道士刘弘隐。他气急败坏地率领徒众奔赴凉州,在佛寺林立的天梯山旁,赫然燃灯悬镜施放“光明”,以“惑众”千余人的宏大场面,公开向佛教发起了凌厉的攻势。
一百年后,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当选“佛”还是选“道”的强国之策还在朝野谋士手中辗转交替的时候,另一个长安道士寇谦之就迫不及待地携经北上,在平城东南的旷野中侈建天师道场,用弥漫着鬼神之气的“老君”咒法,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北魏道武帝所恩准赐予的“天师”尊号。“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一个满浸着“道德”符水的“太平真君”年号,由是便把数万长安沙门以及数十万“佛图形象(以)及胡经”②,一齐推向了死亡的火海!佛道争斗的第一个回合,以道教志得意满、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钢刀与鲜血构成的无情威赫,迫使佛教不得不收敛形迹,违心地脱去希腊式长衫,乖巧地改换上中国士大夫引以为荣的“褒衣博带”,扬起了期盼“和平”的净瓶、柳枝;而剑拔弩张的一场对抗,也教会了道教管测方向、“乃学佛家”③的生存绝技。滞重传统的汉土袍服道冠,却也要遵照西域传来的佛家手印,正襟危坐在混沌神秘的须弥座上,念咒炼丹,而且还要征用两菩萨左右侍立;持扇挂须,并不妨孳生头、项之光。一如佛像仪轨的道像雕造狂潮,裹胁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可抑止地首先在长安一地得到了横肆泛滥。始凿于正始二年(505)的魏文朗造像碑,成窟于西魏大统元年(535)佛道混一的陕西宜君福地石窟以及散漫在长安附近的无数座佛、道造像碑,便是在一场血斗之后由佛道两家所联袂演出的微妙颂歌!
使人惋惜的是,不待这一曲微妙颂歌的最后一个音符彻底奏完,又一场血与火的争斗却早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酝酿、准备。
争斗的内因,根源于各自企图独霸天下的最终目的;争斗的外因,则起始于“卧榻之下,安有饿虎”的相互指责。
对于道教来说,它不能容忍一个外来的异教如此堂而皇之地在自己土生土长的领地内,肆无忌惮地“以像传法”、“以法传像”!
对于佛教来说,它更不能容忍一个只懂得“奉道悔过,用符水咒法治病”④惑人的“黄老之教”竟敢亦步亦趋地追随自己的造像仪轨,持扇扶轼,背放光明,赫然结跏趺坐在了大千世界的须弥座上!
斗争的双方,都在积极寻求当政帝王的全力支持,而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却决不轻易赐予任何一方没有回报的“浩荡龙恩”。“超凡脱俗”的佛、道两教以及“赐福于民”的统治阶级,在信誓旦旦的说教声中,毫无顾忌地展开了赤裸裸的讨价还价。
574年,酝酿已久的政、教争斗交易,终于在千呼万唤声中浮出了水面。交易的结果,是以无数经像毁之一旦,四万以上的佛道寺庙赐予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伽蓝沙弥还俗作贫民的惨重代价,赢得了北周王朝百万赀产的巨大收入以及七年有余的稳定统治。冠冕堂皇的北周人主,为了自己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撕心裂肺的巨大痛苦,随心所欲地送给了两败俱伤的佛、道宗教!
令北周统治集团所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大的既得利益后面,竟然隐藏着最大的致命祸害。仅仅七年过后,一个曾几何时自恃为无坚不摧的宇文王朝,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就是那个曾经为佛道两教所争相拥护并被宇文王朝视为社稷“柱国”的外戚杨坚!
以强权武力僭越“皇位”的大柱国将军杨坚,亲眼目睹了记忆犹新的“毁佛灭法”狂潮。为了迎合支撑大隋政权“关陇集团”的一片欢心,他毅然决然地首先选择了与“关陇集团”有着藕断丝连情结关系的冠服道教。一个采自道书经典的“开皇”年号,正是大隋王朝所无私给予“关陇集团”上层人物的慷慨许诺。
当朝天子旗帜鲜明的“崇道”政策,使得含恨七年的屈辱道教,依稀看到了迷茫上空中的一片蓝天。不待太极宫内的皇家诏书传出长安城垣,弘扬道教“符水咒法”的天尊刻石,立刻如雨后春笋,纷纷在全国各地的宫观庙宇、摩崖石窟内开刀凿就。“所以雕铸灵相,图写其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⑤。渐次独立规范的道教造像仪轨,终于得到扬眉吐气的尽情发挥。
当袍服道冠的天尊弟子感激涕零地坐在宽敞明亮的宫观庙宇内,念咒画符为大隋王朝企求平安的时候,老谋深算的隋文帝杨坚,却一头扎进了与“道冠”势不两立的黄冠袈裟的怀抱。七诣佛门,三下诏书,建造佛塔113座,整治新老佛像20万尊。铁打一般的客观现实,赢得了30万沙弥以及近百万信徒伏地跪求大隋皇祚万世长存的喃喃发愿。大“道”朝天,佛“法”无边,隋王朝兼顾佛、道,平分秋色的巧妙调和,终于为长达34年的佛道融合历史,画上了一个温馨圆满的漂亮句号。
应当感谢大隋王朝的这一巧妙调和,它使接踵而来的大唐王朝看到了佛道融合的强大威力,也使刚刚弥合了历史伤痕的佛道两教,再次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在百官朝贺声中,开始了李唐王朝289年历史的漫长统治。相同的统治基础,共同的统治目标,把新开皇祚的大唐王朝,牢牢地拴在了佛道共存的战车之上。自认为老子后裔,却又称帝即如来,先下诏为太祖元皇帝(李渊父李昺)和元贞皇太后造等身佛像,复下诏钦定道、儒、佛三教先后次序,瞻前顾后、惟用而取的圆滑国策,迷惑了神仙世界的各教各派,也迷惑了人间世界的芸芸众生。综观初唐两朝的三十二年岁月,基本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佛道同乐”。
融和的颂歌唱到了打开盛唐富丽之门的永徽一朝,一个尔后左右大唐王朝铁打江山五十余年的铁腕女人便随之脱颖而出。
门阀林立的大唐王朝,使得出身低微的武昭仪为取得女界至尊的皇后地位,付出了刻骨铭心的惨重代价,而一旦取得皇后地位的太原武氏,却并不满足凤随龙舞的阴阳人生。以周代唐的勃勃野心,促使她努力去寻找把握一切可能出现的转瞬之机。于是,弘扬弥勒信仰的法相之宗,便成了这个女人通向胜利之门的关键法宝;于是,蓄谋已久的伪刻之经《大云经》,也终于把这个女人推上了“慈氏越古金轮圣皇帝”的巍巍宝座。
炙手可热的法相之宗,风靡全国的弥勒造像,终于完全成为则天大皇帝所给予袈裟佛教的最大回报!盛唐的天下,造就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则天皇帝;野心勃勃的则天皇帝,也把盛唐石窟艺术的浪漫之乐,弹奏到“花好月圆”的极致。
风起潮涌,从盛唐开始达到鼎盛的中国石窟寺艺术,终于在晚唐之际走到了峰巅。对视845年凄然发生的“会昌法难”,那是历史所无私回报给恩怨佛道的最后一个鲜血与烈火酿就的成功“涅槃”。
云开云合,盛况空前的中国石窟寺艺术,终于又无可奈何地从峰巅上滑落下来。检点960年以后迅速出现在万里丝路之上的五代以至宋金元明的无数大窟小龛,那是中华民族所慷慨奉献给人类世界的又一个精气与灵魂铸就的艺术宝库。
盛唐的太阳落了,赵宋的一轮新月又徐徐出现在遥远的天际。
峰巅的艺术去了,崭新的另一次艺术峰巅又在酝酿生成。
再一次地巡视绵亘两千余年的漫漫丝绸之路,胸中便奔涌起天地人间的无限感慨。昨夜今朝,数以万计的巍巍石刻之窟,顽强标写的该是怎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符号?
再一次地倘佯滚滚不竭的绵绵石窟艺术长河,眼前总浮现出道尊佛陀的无限风姿。今朝明天,数以万计的巍巍石刻之窟,永远有诵不完的道德经典,听不断的弥陀之音!
注释:
①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②《魏书·释老志》。
③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④罗竹风:《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⑤《隋书·高帝纪》。
福地石窟
● 此尊福地石窟造像肉髻高耸,面相清癯,眉目低垂,后面有莲瓣形背光,为陕西宜君福地石窟造像之中的奇葩。20世纪90年代初期搬迁至宜君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