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 交通路线
- 长安与丝绸之路
- 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路全程探行纪实上
- 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路全程探行纪实下
- 海上丝路史话
- 丝绸之路史研究
-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
- 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
- 中西丝路文化史
- 沧桑大美丝绸之路
- 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
- 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
- 世界的中国——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寻找失落的世界遗产
- 丝绸之路2000年
- 丝绸之路——从西安至帕米尔
- 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
-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 丝绸之路——神秘古国
-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
- 丝绸之路在中国
- 丝路景观
- 丝路起点长安
- 丝路文化新聚焦
- 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
-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
- 中华文明史话-敦煌史话
-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 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新史
- 西域考古文存
- 丝绸之路的起源
第四节 西方人对华夏民族的初步认识
作者:孟昭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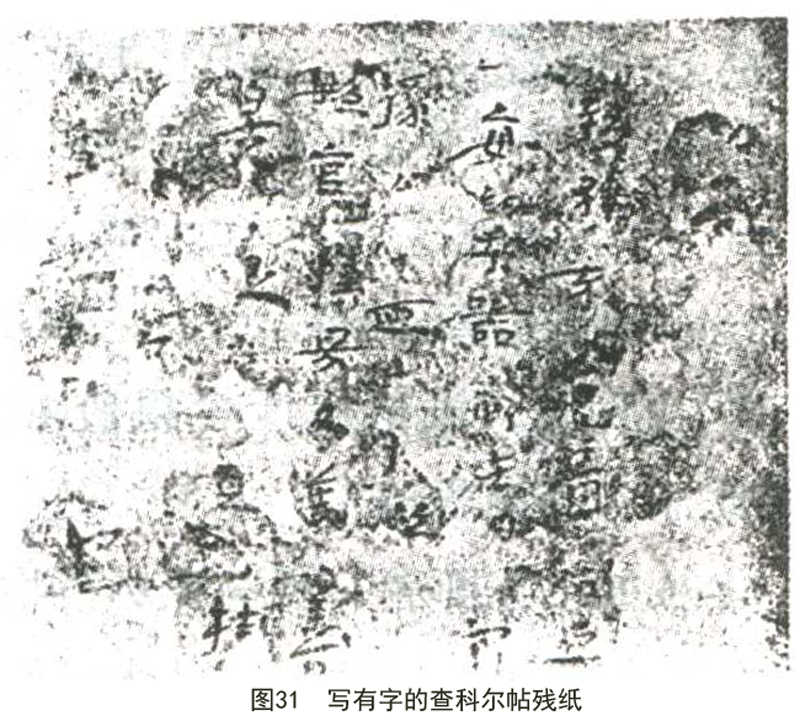


一、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
西方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呢?确切时间难以考证。今天只能从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与描述中来推测,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最早是从丝绸开始的。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则证实并加深了西方对中国——丝国的认知。
1.希罗多德与克特西亚斯称述的中国
古希腊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正如李约瑟所说的:“Seres(丝国)这个名字起源于‘丝’,传到欧洲成为希腊字(Serconp),因此,这个名字大约始于丝绸贸易开始的时期。”(39)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4)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春秋之世,著有《史记》九卷。其中记有阿尔其贝衣人即中国人。但也有学者认为以希罗多德的知识,不可能到达这么远。之后对中国有所描述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克特西亚斯。克特西亚斯(Ctésias)曾在波斯王宫当过御医,并在此接触了中国的丝绸制品,著有《旅行记》、《印度记》。他对中国有过这样一段话:“赛里斯人(Seres)与北方印度人,身躯魁梧,男高十三骨尺(Cubits,由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在格忒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人与兽相似,皮如河马,箭不能入。”(40)尽管这段描述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它开启了西方对中国人称谓一个比较早的系统:赛里斯、赛里加(Serice)系统,它传自陆路。
2.支那名称的起源
欧洲人称中国,英文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文作Gina……其源皆起于拉丁文的Sina,寻常用复数,作Sinae,单数读作“希那”,复数为“希内”。最早出现在公元150年之际,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书,有Sinae及Seres两名。此后,亚美尼亚、叙利亚、阿拉伯、波斯无不以此称中国。(41)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支尼”,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文献。在费尔瓦丁神的颂歌辞中,写作Cini,或者Sāini,古代波斯文有的写作Cin,或Cinistan、Cinastan,与粟特文中的Cyn相近。这个名称可能是通过东伊朗语传去的。(42)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居鲁士攻灭米底国,建立波斯帝国。后来居鲁士及其子,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征,把波斯帝国的东北疆域扩大到中亚的锡尔河流域,与葱岭以西塞人游牧地区接壤。大大促进了波斯人对中国的了解。
古印度最早称中国为“支那”(Cina)。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有这个名称。这两大史诗起源很早,成书过程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所以不能确定这一名称形成的确切时间。而公元前4世纪的考底里耶的《政事论》成书年代可考,其中也载有Cina之名。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丝衣服)等,都有Cina(支那)这个字根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43)因此,Gina可能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丝绸的称谓,后来又转而指称中国。
3.秦
有学者认为“支那”一名为“秦”的译音。最早提出此说法,是在明永历九年(1655),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刊印中华新图时,首先发表,近代很多人持此说法。在1世纪的时候,欧洲文字上出现了最早称中国为Thinae(秦国)的记载:《厄立特利亚海航行指南》(80年):“过克利斯国(Chryse),又到了最北部,海止于秦国(Thinae),在其国内部,有一极大的城,名秦尼(Thinae或Thinai),那地方出丝、丝线和绸绢(Serikon)。”这是西方称谓中国的另一个系统:秦(Sin、Thin)、秦尼(Sinai、Thinai)系统。春秋时代秦国处于西北,后来秦朝统一全国,开展了对外交通,秦之威名通过西域各民族的商贩传入中亚、南亚和西亚,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就称中国为秦,直至汉代匈奴人仍称为中国人为“秦人”。根据张星烺说:“秦穆公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勋业灿然,史无详文。尽于《左传》中一二处,略见其范围之远近而已。”“其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九十二国所占区域,穷若何之广,亦无从知。鄙意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惜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44)
4.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
古希腊文献中与中国有关的论述,最早的大概是希罗多德 (Herodotus)的历史著作。在他的巨著《历史》中有一卷记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族,代表了当时的希腊人对于东方的认识。《历史》的第四卷中指出:……东南行,沿阿尔泰山麓前进,至准噶尔地区,再前行至伊·塞顿人居地,再至独目人、守护黄金的格立芬,直至“北风以外的人”,这便到了海边。“北风以外的人”是什么人呢?有的研究者认为,“北风以外的人”指的应该是生活在中亚严冬达不到的地方,享有温暖气候的汉族人。
早期罗马文献的记载反映出罗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很模糊。中国在哪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丝绸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些问题都困惑着当时的罗马人,中国在他们的眼中也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爱底奥比亚人的丛林里怎么会产生细软洁白的羊毛?塞里斯人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维吉尔《田园诗》)
怎么?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至不敢梳妆,如像肌肤黝黑的塞里斯人的面纱一样。(奥维德《恋情》。)
塞里斯人居住的东方,眼看着意大利(火山)的灰烬漂白了他们长满了羊毛的树林。天哪!这真是蔚为奇观!(西流士·伊塔利库斯《惩罚战争》)
而然,有人声称塞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Musicaniens)还要长寿。(斯特拉波《地理书》)
这些都是罗马人笔下神秘的塞里斯人,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人笔下更具体地记述了塞里斯国和塞里斯人,内容更加丰富,材料也较为翔实。罗马地理学家梅拉(Pomponms Mela),在《地理志》中写道:“亚细亚极东有印度人、塞里斯人、西徐亚人。印度人处于极南,西徐亚人处极北,而赛里斯人则差不多占有东方的中部。”他是西方最早较确切指明中国人居住点的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说:“然后又是一片猛兽出没的空旷地带,一直到达俯瞰大海的塔比斯山(Tabis);在辽远处便是高耸入云的陶鲁斯山脉。两山之间的空隙地带居住有塞里斯人。塞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十分出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45)。这段话记录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还谈到了中国人的民族品格。
马利诺斯(Marinos)是2世纪前期的地理学家,在《地理学知识》中,他第一次把中国的位置标在世界地图上,当然并不准确。大概也是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对中国人的直接记载。在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Florus,1世纪末)的《史记》中写道:“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国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见罗马人而生敬心……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据其人自云,居地远离罗马,须行四年之久,方能达也。视其人之貌,亦知为另一世界之人。”(46)同样,在2世纪时候,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és)在《希腊游记》(174年)中才指出蚕丝是一种类似于蜘蛛的虫子吐出的:“(赛里斯)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Ser,即蚕),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而则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47)虽不确切,但较丝是从树丛中采摘而来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进步。
诸多文献还对于中国社会风气、道德风范进行了描述。公元2世纪末和3世纪初盛名远播的叙利亚天文学家和作家巴尔德萨纳斯(Bardesanes),也曾经谈到过关于中国的故事:“在每个地区,人们都制订了一些具体文字。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所知道以及我所能回忆起的情况,首先从大地一端开始讲述。在塞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经过子午线上空的光辉的阿瑞斯战神之星体不能违背人心而用铁器杀人,同时与阿瑞斯战神有关于昔普里斯也不能强迫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与别人的妻子私合。尽管在他们之中,阿瑞斯战神每时每刻在天空中央巡视,塞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48)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伪克雷芒的认识》一书也说:“燃烧着的星体火星也不像在你们之中一样,对他们的自由仲裁施加影响……在塞里斯人中,对法律的畏惧比人们在其之下降生的星辰还要强烈。”(49)
李约瑟对这些描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在当时,“人们对中国人道德的描述虽然理想化,但是,儒家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点滴言谈,竟如此传到了被某种占星学和诺斯替教派的迷信统治着的世界中,这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思想的传播,可能不难理解,因为她们产生在古代丝绸之路畅通后的两个世纪之中。”(50)
二、“丝绸之路”上的科技文化交流
自张骞“凿空”西域,这条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犹如今日的因特网,将亚欧非大陆连接起来,使得中西文明实现了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关于丝绸之路,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途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广。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我常常想,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统只有几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因此说,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大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欧亚大陆的历史纽带。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也论述过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他说:
我认为,这条丝绸之路从各方面被重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丝绸之路”作为亚欧两洲的动脉,是世界史展开的主轴。欧亚大陆是由蒙古利亚、塔里木盆地、准噶尔、西藏、帕米尔、河中地区、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几个地区构成的。丝绸之路把这些地区连结起来,使其互有联系而得到发展,从而表示出一种动脉的作用。
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上主要文化的母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在此放出了异彩,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出现了拜火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它们向东西各地传播,给予人类文化以巨大的影响。
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由商队传到东西方各地,虽然也发生了各种改观,但对各地的文化却起了提高和促进的作用。在历史上,这一点是最受重视的,丝绸之路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注目,也主要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51)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通道,政治文化通道,也是一条科技文化交流的通道。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地理知识。秦汉以前,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本部。对于中原以外地域的认识,虽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记载了,但远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同时又是模糊的。塔里木盆地一带是什么样的情形,就非常模糊。琉球(日本)之岛,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域。对于更远的地方,就更无所知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政府的使节和商人,先后走到了中国本土以外很多的遥远地区,他们从外国带回来许多关于异国风土人情的记录,这样就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改变了中国古代所谓“天下”的概念。
张骞把他亲身经历和传闻中的国家,如大宛、康居、奄蔡(里海东北)、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枝、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物产、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以及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知识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这些不同程度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再如,汉和帝永元九年(97),甘英出使大秦,西抵波斯湾,为风浪所阻,未达目的地,但他回国把沿途见闻详加介绍,“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后汉书·西域传》)。这对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对科学技术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人员的往来更为频繁。仅沿“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后,中国西往的使者,一年之中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回,来回时间长的达八九年,短的也要几年。从汉到唐的一千多年间,“丝绸之路”虽几经中断,但基本上是畅通的,沿着这条路保持大规模的经济贸易交往,随之而来的是科技文化的交流。秦汉时期,沿丝绸之路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丝绸、铁器(包括铁农具和兵器)和漆器,与之相应的是丝帛生产技术、冶铁术和髹漆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对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南亚、西南亚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丝绸及纺织品的外传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丝绸的国家,这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考古发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6000年前文化遗存中有雕蚕形虫文的象牙盅;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有半个用锐器割裂的蚕茧;浙江吴兴钱山漾4700年前文化遗存下中有平织丝织物和丝带、丝线,其线由十多根家蚕单丝捻成。这证明中国传统丝绸的生产不迟于新石器时代。
商代卜辞中有不少桑、蚕、丝、帛等字,殷墟出土铜器常有细纹遗痕,《管子》称桀之时“薄之游女工文绣”,可知夏商已有纹织。西周郑、卫、齐、鲁、秦、楚、越等国均有丝织记载。《诗经》中屡见锦字,锦属色彩织物,又出土周器中常见绮纹痕迹,绮属斜纹织物。至春秋战国,丝绸进一步发展,形成齐鲁、陈留、襄邑等丝织中心,南方楚、越丝织也盛。绮、锦之外,纱、縠、罗等轻薄织物均已出现。
汉代丝绸有较大发展,复杂的提花织机已基本定型。齐鲁、中原之外,蜀成为重要产地。见于文献者已有十数个丝绸品种。国家重视蚕桑,设官管理,设官织室,并从事国内外丝绸贸易。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均输收帛达500余万匹,通匈奴时动辄赐“彩缯千匹”。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甚频,但丝绸不衰,时有19个州产绸。蜀锦声誉日隆,江南发展尤快。丝绸在国家财政上的地位也更重要,租调收绢(帛)绵(丝)、帛,并流通为货币。
2.绢丝大量外销
西方有人说,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当时生产过剩的丝,所以一再出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但其中有一点没错,那就是,自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的丝在西域知名度更加高了。《史记·张骞列传》记有“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由此可知张骞是在见到中国货以后,开始作调查的;未出国之前,并不知外国有中国货,也不可能作调查准备。所以说张骞能善尽其出国之使节,善用出国之机会,而获得意外收获则可,如果把结果当做动机及目的则不可以的。
然张骞通西域后,中国丝大量向西方倾销,这是事实。因为丝这种物,人工既精,应用犹广,远胜于西天来的天马、葡萄、夜光、明珠之类的,所以东西交通未开之前,已有辗转潜运至中亚,甚至远至欧洲的。
上述可知,中国丝闻名于外,当在汉代以前。《史记·货殖列传》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其缯物,间献遣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意思是“乌氏”地方的商人名叫“倮”的,以畜牧起家;畜既多,就出售,以所得之钱收购精致的丝货,从间道运销外国,获利十倍,再购买中国所最需的牛马。如此辗转贸易,竟成为巨富,所拥有的牛马不知其数,秦以封君视之,并请其长来朝中,参与国家大事。
当汉代通西域时,中国丝不仅已闻名于西方各国,而且产量已足供行销国外。故欲知汉丝何以能畅销于西方各国,必须先知道其在国内的生产情形。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主要运输的商品,就是中国的丝绸。汉唐时期,丝绸是中国皇帝用来赏赐各国使者和各民族首领的珍贵礼品,是同各国交换马、玉等物资的主要物品,同时也是中外各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有的国家,如安息、条支等国的商人还曾垄断国际丝绸贸易,阻止中国和罗马直接交易,以便从中牟取暴利。这样,曾经在历史上出现“驰命走释,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伊吾之右,波斯之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册府元龟,985卷》)的繁荣局面。当我国丝绸远销到西方各国后,一方面深受这些国家人民的欢迎和赞扬,把它当做至宝,但同时也引起他们本国的经济变化。繁盛的贸易引起西方史家的不胜惊叹:“丝至罗马,价等黄金,然用之者众,故金银乃如水东流。”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是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男女贵族都争穿丝绸衣物。据普林尼约略估算,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支付的货款,在1亿赛斯特(ses-terces)上下,约合10万盎司黄金。因为这样,它曾造成罗马的黄金和白银大量外流,给帝国经济带来严重负担。梯庇留斯大帝曾经下令禁止男子穿丝绸,但由于贵族锦衣绣服已成为习惯,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奴斯在他的著作《史记》中指出:“昔日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不仅不能禁止,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用丝绸,并用作帷幕帘帐等,用途愈益广泛。同时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需求,罗马商人更是东经大夏,直接到中国来贩运丝绸。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所著《博物志》中,深慨贵族“奢侈之风”,并指责他们“远赴赛里斯以取衣料”,据考证,马赛里奴斯对中国的记载,就是根据马其顿商人梅斯派遣经理赴赛里斯购买丝绸时的见闻而写的。我国丝绸的输出,从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也得到证实。苏联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奥格拉赫提,贝加尔湖以南的伊尔莫瓦巴德、孔斯克以及中亚的肯科尔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蒙古的诺因乌拉,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地中海沿岸的杜拉欧罗波、哈来比和瑞典梅拉林湖畔古墓葬中,都发现了我国生产的丝织品。
经过丝绸之路,除输出丝绸之外,中国还输出铁器、陶器、漆器、皮革和大黄、肉桂等药材。据普林尼《博物志》记载“中国输出的商品有铁和皮革”。还说:罗马市场上有各种铁器出售,而且“在所有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
3.冶铁、制陶和穿井技术的西传
生铁冶炼技术发源于中国,我国的冶铁技术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冶铁技术相联系,我国炼钢技术出现也较早。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秦、汉的一些著名宝剑,如干将、莫邪等名剑,便是用优质钢制成的。从当时世界来说,许多地方还不知做漆器和铸铁。《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张骞报告:“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后来,“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显而易见,中亚各国炼铁炼钢技术都是张骞通西域后从中国学得的。史书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这些屯田卒和屯田官的到来,使天山南北冶金业发生很大变化,在考古资料中有充分的表现,属于汉武帝以前也就是张骞通西域前的罗布泊早期墓葬中仅有少量铜管和铜环。约为公元1世纪至4世纪,即张骞通西域后的罗布泊晚期墓葬则发现了多种金属制品,如铁刀、铁簇和铅制器物等。尼雅遗址中亦有镰刀、刀、锄、斧、链等铁器和铜匕首的发现。尼雅、库车、洛浦等地还保存了古代冶铁、炼铜的遗址。由于西域冶金业受内地影响,故在生产工具和产品方面都带有内地特点。《汉书·西域传》说:“自且末以往……作兵略与汉同”。库车阿艾山冶铁遗址出土一件陶制吹管,是风箱上用物,据研究与传世的“霸陵过氏瓴”相似。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铜镞和铁镞,多作三棱式和双翼式,是内地镞的常见形式。(52)
内地制陶技术也逐渐西传。考古发现,罗布泊遗址及晚期墓葬中出现一批制作较好的灰陶,有罐、灯、甑等,无论是形制和制作技术上都具有内地陶器的风格,说明是在内地影响下的当地产品,是内地制陶技术传入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1961年昭苏县还发现了西汉乌孙的墓葬,这里出土的陶器亦具有内地风格,其中有一件陶罐,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更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
汉军在鄯善、尉犁、乌孙、车师屯田,使用锄、钁、犁等先进农具,又挖掘沟洫渠道,引水浇地。鄯善、尉犁等国仿效学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西域各国靠汲河水和渠水饮食,汉代在西域屯田,中原的水利灌溉技术也随之传入西域。《史记·李广利传》载,汉武帝遣李广利攻打大宛时,“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帮助解决了饮水问题,这是明确记载中原穿井技术传入大宛的可靠例证。由此可见凿并技术传入西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屯田的士兵把这种方法带到西域;二是西域诸国在征战中俘获汉人,将技术传入。新疆今天还广泛存在的“坎儿井”,就是一种地下渠道,以分布在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及哈密四县为最广。经考证,为汉代传入。汉族士兵和商人把打井技术传进西域,对改善西域人民的生活是一大贡献。(53)
4.西方物产的传入
西方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经丝绸之路也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一些中原没有的物种,其中以葡萄、苜蓿最为知名,此外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输入的。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印度的胡椒、姜、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许多香料在当时被作为药物使用。同时玉米、占城稻、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传入中原,丰富了农作物的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
另外,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和中亚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畜牧业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得乌孙马,后来又得大宛汗血马,“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据《史记》记载:“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今伊朗)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此外今喀布尔河下游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大狗等也是随朝贡而传入中原。
5.大宛马的意外收获
中国古代不乏良种马,河南洛阳金纯出土战国时代的铜马,其躯体雄伟,应为富有纵越力的良马,但是后来物种逐渐退步了。中亚一带则盛产良马,康居、大宛的马很出名,尤其是大宛,“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据《唐会要》卷72记载,康居马也是大宛马种。自从丝绸之路开辟后,中亚地区马匹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先求匈奴马补充,然后继之以大宛马及乌孙马。汉武帝所求“汗血宝马”,虽未能乘以升天,但是客观上却使中国的马种得以改良,应该说是意外收获吧。
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她的宽容性,她不但能无私慷慨地赠予,也能巧妙有选择地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宽容性,使中华民族能够博采众长为己所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评价丝绸之路的作用时说:“海通以前二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是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汇合处,是中外交流的传送带,是人类历史进步的见证人。
三、丝绸之路交换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
1.物质交流总是先于思想
“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由于生存的困境,需要建立一条通道来进行物物交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他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水光山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物质的享用带来对文明生活方式的渴求,推动先进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有历史学家说过,洋货不如大炮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洋货不如思想那样感染人心,但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入每个人的生活。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后,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戈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信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人类各种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多种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在丝绸之路上自由行走流动的商人和科学家,为丝路沿线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带去了生产、制造这些物质的技术,推动了沿线地区社会的进步。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四、“丝绸之路”改变中国人的地理空间概念,树立了“交通”、“汇通”的观念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极为重要。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面”。“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上述三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这三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互相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
古老的中国文明,形成并发展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南面崇山,北面荒原,东临大海,西临大漠,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就连彼此之间互通音讯也殊非易事,要越过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阻碍着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也遮蔽了古人的眼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都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一词,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上古时代或指京师,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如《诗经·小雅,六月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养成了国人自我中心的认知习惯和“华夷”思想。“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使得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天地近乎两个平行平面,自己居住在地平面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华夷观念作为一种畸形的地理文化观,使中原人养成了一种强烈优越感,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民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局限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他们所感知的世界只有中原王朝及周边地区的国家,对此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以为中华文明与周围蛮荒之地即是世界的全部。
在人类文明的朝霞时期,当中华文明同西方各古代文明勃兴之后,先辈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还是跨越了重重障碍,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重围”,波浪式地向外扩展,古代中国除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亚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之外,与中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各地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创造,曾深深地影响外部世界的文明进程。所以,这种交流与沟通的实践,也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地理中心的观点。汉代的地学思想,带有浓烈的地理居中和四方辐辏的意识。(54)所谓地理居中,是指古代先民在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自发地把人类文明的辐射源认为是天下之中或地理位置居中。四方辐辏,则是指周边对文明辐射源的依附与归顺。地理居中与四方辐辏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没有一个地区文明的领先发展,就不可能出现文明发展的差异及文明辐射源;同样如果没有四方像车辐条一样向轴心收敛式汇聚,就不会出现一定区域内公认的地理中心或文明辐射中心。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修兵振德”,“置左右大监,监万国,万国和”,所谓“万国”当然是指原始小部落,帝尧时代,“其仁如天……百姓昭明,合万国”,舜继尧后在“中国践天子位”。《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土于先王”,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天既已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都付给先王”。从“万国和”到“合万国”,说明了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只有政治影响最大的领袖人物所在地,才能成为地理上的中心或天下之中。而中国上古五帝“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地理观,“其仁如天”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动力,使得周边各部落心向往之,友好往来,成为万国合和的中心地区,成为人类文明的辐射源。由于四方辐辏,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观念上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想法。《尚书·禹贡》、《盐铁论·轻重》“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务”。都认为中国处于天地或天下的地理中心。从地域环境看,西汉通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商品生产繁荣,汉武帝不仅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而且于元封元年在海南岛建立“儋耳珠崖郡”,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者,不可胜道”(55)。
另一方面,在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中,足迹的延伸,眼界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交通”对话的观念。
在现代汉语中,“交通”,往往被理解为诸如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等与现代化技术须臾不离的运输手段及其相关概念。其实,“交通”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交”是象形文字,像人两腿交叉形,本义为交叉,如《说文》中解释为“交,交胫也”,《战国策·秦策》“交足而待”,《礼记·王制》“雕题交趾”,《庄子·天地》“交臂厯指”,《诗·秦风·小戎》的“交韔二弓”中的“交”皆有此意。引申为交合、移交、交接、交往等含义。如《易·大有卦》“厥孚交如”,《荀子·儒效》“是言上下之交”,《吕氏春秋·知士》“静郭君之交”,《资治通鉴》“交游士林”,都有交接、交往含义。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的运行,都离不开“交”这种运动。易经认为,宇宙的最基本的结构是“交”(《易经》中的“爻”)。宇宙始于“天地交泰”,“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大戴札记·曾子制言下》)。交,不仅是天地运行的基本结构,亦是天地化生的基本原则。对天地万物来说,交就是交接、交感;对男女而言,交就是交合,而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交,更多的是指交流、交往、交融。对于矛盾对立方(在易经中就是乾坤、天地、阴阳、刚柔、男女等的划分)而言,因为有了“交”,才有可能泰、有可能通。相反,“天地不交”,则“否”。《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意思是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交”则“通”。《易》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不无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思想。通,是指通达、融通、沟通。《说文》“通,达也”。《易·系辞》讲,“往来不穷谓之通”。《易·说卦》“推而行之谓之通。坎为通”。《国语·晋语》有“道远难通”,《吕氏春秋·达郁》谓“血脉欲其通也”。白居易《琵琶行(并序)》写道:“凝绝不通声暂歇”,周敦颐《爱莲说》也讲“中通外直”。“交”与“通”合在一起,是指沟通、接通、交流,如“阡陌交通”(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旁推交通”(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等等。如果达不到“通”,那么这种“交”是一种南辕北辙徒劳无益的活动。“通”与“同”相近,是一种不同之同,是天地相交、人与人相交所要强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正因为事物之间千差万别的不同,才有了相通的必要性;也正因为事物之间又殊途同归的有同,才有了相通的可能性。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交通”、人与人“交同”。古人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指合情合理的事,大家想法都会相同。《孟子·告子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陆九龄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人之所以有爱、敬之情,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交而通之。魏学渠给《天儒印》作序时说“同此天,则同此心”;钱钟书《管锥编》开篇即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认识到了交而同、交而通的可能性,认识到了由交而通的重要性。人作为天地间的生灵,其相异性决定了交流、对话的必要性,其相通性决定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言,以对话为核心的交往、交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现代西方最风靡一时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相比较,我们在对话思想的历史渊源应该比西方更为久远,更为原初。
交通的渠道、载体是“道”、“路”。正因为有了交通而和的认识和思维,古代中国人才会积极地寻找与外界交通的机会,主动开拓与外界交往的道路,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乔家大院》的票号曰“汇通天下”,其中“走了”的吆喝,无不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走出去,带回来,交流才能融合,通则汇,汇则兴。早在中国汉代,不仅产生了这种汇通天下的观念,而且亲身实践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其意义不仅仅是开通了一条贸易“丝绸之路”,还在于它打开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空间地理上的阻隔,把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展现在世界面前,把一个新奇的世界带到中国人面前,它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树立起交流贯通的观念,汉武帝求“汗血宝马”的传说,代表了汉代逐渐出现的渴望了解世界的思想萌芽。难怪有人称它是中国“古代的因特网”。
① 司马迁:《史记》。
② 杨建新:《“西域”辨证》,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1)。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④ 司马迁:《史记》。
⑤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57(1)。
⑥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
⑦ 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⑧ 戴禾、张英莉:《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载《西北史地》1986(1)。
⑨ 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⑩ 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11) 王柄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4)。
(12) 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册,又载1915年《地学杂志》;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
(13) 王国维:《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第四卷;此外,清代人何秋涛及日本人桑原騭藏均主张月氏即禺氏,见桑原騭藏:《张骞西征考》。
(14) 杨建新:《论汉代乌孙》,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2)。
(15) 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三○《平准书》。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8)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2页。
(19) 孙宏安:《<九章算术>思想方法的特点》,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4)。
(20) 王鸿钧:《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21) 孙宏安:《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5)。
(22) 吴文俊:《从数书九章看中国传统教学构造性与机构化的特色》,见《秦九韶与数书九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5页。
(23) 王青建:《试论出土算筹》,载《中国科技史料》,1993(4):3。
(24) 孙宏安:《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式浅析》,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1,(增刊):20。
(25)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页。
(26)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
(2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5—116页。
(28)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29) 同上,第43页。
(30) 同上,第38页。
(31)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32)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33) 同上,第6页。
(34) 同上,第3页。
(35) 同上,第20页。
(36)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第29—30页。
(37)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38) 刘光裕:《论蔡伦发明“蔡侯纸”(二)》,载《出版发行研究》2000(2)。
(3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4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台北: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26—27页。
(41)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61年版,第66页。
(42) 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43)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6—77页。
(44)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台北: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8页。
(45)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页。
(46)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47)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48)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页。
(49) 同上,第58页。
(50)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51)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78(5)。
(52) 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
(53) 钱伯泉、王炳华:《通俗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54) 霍有光:《司马迁的地学思想》,见《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55)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孟昭勋,张蓉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