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 交通路线
- 长安与丝绸之路
- 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路全程探行纪实上
- 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路全程探行纪实下
- 海上丝路史话
- 丝绸之路史研究
-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
- 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
- 中西丝路文化史
- 沧桑大美丝绸之路
- 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
- 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
- 世界的中国——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寻找失落的世界遗产
- 丝绸之路2000年
- 丝绸之路——从西安至帕米尔
- 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
-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 丝绸之路——神秘古国
-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衰
- 丝绸之路在中国
- 丝路景观
- 丝路起点长安
- 丝路文化新聚焦
- 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
-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
- 中华文明史话-敦煌史话
-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 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新史
- 西域考古文存
- 丝绸之路的起源
第五节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作者:孟昭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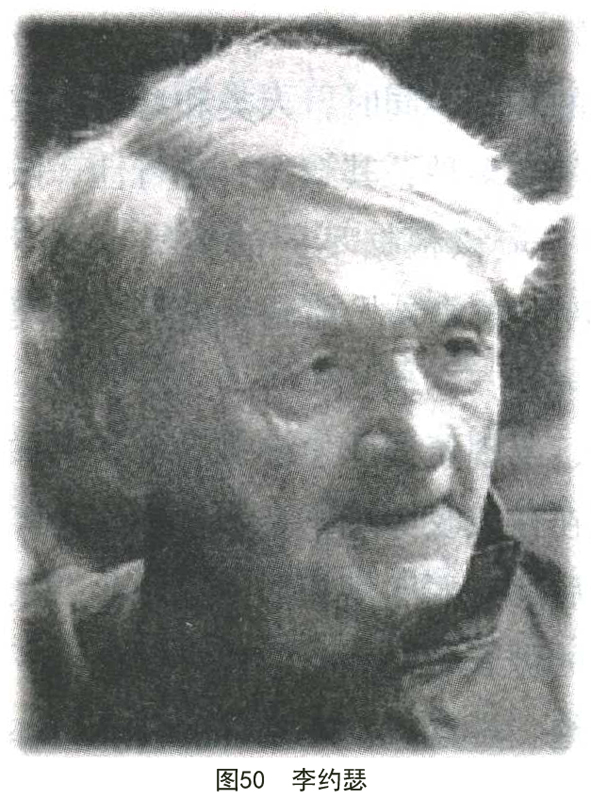
一、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
在大众心目中,李约瑟几乎相当于中国科技史的同义词,这个名字和由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他本人也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有赖于李约瑟主编的煌煌几十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又译《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更有赖于大众传媒的力量。有学者笑称,“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未必有充沛的精力和意愿去细读每一分册,何况一般读者,这成全了罗伯特·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97),而后者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对这部科学史巨作从象牙塔到大众化的新闻采写,是一种畅销书式的浓缩,可概括为“中国古代科技一百项世界第一”。这种概括对普及科学史常识当然有意义,但非要把它上升到民族荣誉感的地步则大可不必。而高举科学大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初衷恐怕恰恰是李约瑟在中国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中国科技史专家刘钝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一词,指出:“这当然不等同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感情,也部分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98)为的就是警醒国人在认识李约瑟及其著作方面的一些误区。他将“李约瑟情结”大致概括为三种表现。
第一就是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方面。的确,李约瑟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主要兴趣是在伦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通过李约瑟的工作,人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片面地理解成替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技术成就树碑立传。
第二是关于对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习惯于这样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好像李约瑟那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其宗旨就是要解开中国何以未来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其实现代的历史学家对李约瑟的工作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认为他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是推进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问的相互理解,开创了将非西方的传统和成就整合到科学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
第三就是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由外国人来书写这一事实感到不安。这同样源自一种略显狭隘的民族自尊心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所谓的“李约瑟情结”的背后,其实是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内心的自大复自卑的心理,这一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早就在他笔下的阿Q身上活灵活现地展示过。“我先前比你阔多了”,这是阿Q的口头禅,想想这句话倘若是由比自己更有身份的外国人承认并说出来的,那该是多大的满足啊。这就是刘钝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的第一种表现,跟第三种表现——痛心疾首这一伟大的工作为什么不是中国人自己做的异曲同工。这一认识的主观性与片面性自不待言,对心理学略知一二的人都了解自卑和自大常常是纠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的自信有时候常常是内心自卑的另外一种表现,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自卑也会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我们不妨看看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一些人在网络世界炮制出的对“四大发明”的质疑,这种声音其实就是自卑的另外一种直接表现,无异于无知之士“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在他们的论述里,李约瑟就是炮制“四大发明”说的始作俑者,“非西方中心论”也成了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的李约瑟哗众取宠的东西(李约瑟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被他们适时地视而不见)。自卑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到底也是罕见。
这也正是我们在认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科技时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言以蔽之,科学的首要要求就是客观,认识也是一样。掺杂进去了太多主观情绪的认识肯定是会有失客观的。诚然大约明代以前,中国在许多技术方面,都是领先于世界的。甚至到清初,我们还以“天朝大国”自诩。但是必须承认西方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当时我们并不知晓。到了晚清,皇帝发现他们的自鸣钟的确有点意思,但也认为那不过是工匠做的雕虫小技而已,爱不释手之余,还是以蛮夷称之。鸦片战争一起,国门以一种我们不情愿的方式洞开,我们知道了洋鬼子的船炮利器,我们纵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艺,再加上忠义之士的视死如归,也终究无济于事。失败的命运促使仁人志士发愤而起,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兴洋务、办厂矿、译洋书、谋立宪,以至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天朝大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曾几何时,提到中国,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地大而物并不博,人多并非好事。提到中国,就是“四大发明,灿烂文化”,殊不知,近代外国四百大发明也不止;中国文化有灿烂的地方,也有不灿烂,甚至鲁迅说的“吃人”的地方。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说到外国,就是腐朽垂死,水深火热,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要让他们过上像我们一样幸福美满的生活——故不论失掉自信与否,首先就失去了平常心。正是因为缺乏平常心,我们才无法参透李约瑟投身中国科技史研究,致力于“非西方中心论”的本意所在。他的立场仍然还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新发现来警醒自己的同胞:你并不是世界的唯一。如果我们回溯李约瑟在踏上科学之路时就逐渐形成的信念,当更能理解他这一工作的根本目的所在。他坚信“人类生活中包含着各种少不了的经验,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相互矛盾,彼此还是可以解释的。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能达到绝对真理,不要认为某一范畴是唯一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只有全面地体验所有的范畴,才有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99)。李约瑟投身中国科技史研究,当然不乏所谓的“中国情结”,即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要为认识自己所处的西方文化打开另外一扇窗户,继而推进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仅仅将其视为一热爱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树碑立传的西方人,到底是太过狭隘了一些。
二、李约瑟的“中国情结”及其他
不过有意思的是,至少在37岁之前,李约瑟(当时还叫尼达姆)对中国这个位于东方的古老国度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一个偶然闯入他生命的中国女子带他认识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并让他因此迷恋上了这个国家的一切,他之后的研究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要知道,37岁之前的李约瑟,是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年纪轻轻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很显然,这一转折是他一生的一个关键。诚如他自己所言“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00)。
这个改变了李约瑟的中国女子就是鲁佩珍,李约瑟暮年的第二任妻子,在妻子的名分上她只陪他走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然而,众所周知,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始终是事业上不离不弃的伙伴。
鲁桂珍(1904—1991),1904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鲁茂庭(字仕国)是南京一药商。她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攻读生理学,后在上海一家医学研究所进修生物化学。抗战初期,未婚夫(据说是空军飞行员)牺牲在抗日前线,这是当时年逾而立的鲁佩珍立志成为“独身主义者”的最初动因,也是她决意远赴欧洲留学,献身于科研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1937年鲁佩珍远赴重洋进剑桥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尼达姆夫人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这位中国女科学家身材娇小、聪慧活泼、个性鲜明,深得尼达姆夫妇的喜爱,经常被导师邀至家中,饮茶进餐聊天。不经意之间,竟然彻底改变了尼达姆的后半生。
鲁桂珍的父亲鲁茂庭不仅是女儿留学的经济支柱,也是她科学之路上的一个向导。父亲曾写信给鲁桂珍说:“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研究,还可能发掘出更有意义的事实。至少应当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鲁桂珍曾把这封信念给尼达姆听。这些,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全部科学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01)。这位年近40岁的英国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汉字,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36岁的鲁桂珍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后来李约瑟又从一位捷克汉学教授那里接触到《庄子》,由此迷上了道家学说。夫人德萝西全力支持,夫唱妇随,不仅改姓为李,还把名字Dorothy音译为中国化的“大斐”。
学界公认:“假如鲁桂珍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技史学界就不会出现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有一个约瑟夫·尼达姆”;“鲁桂珍是不朽巨著《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引导者、激励者,正是她引发出了一个不朽的李约瑟”。(102)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桂珍是李约瑟后半生中国情结的一个始作俑者,亦可说是一个中介。而李约瑟本人则又是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中介。
不过,综观李约瑟的生平,很多人发现,他终其一生都在做一种平衡的工作,无论是在早年不和的父母之间,还是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三人行”中。生活上的际遇竟然与学问之路如此契合,倒也颇令人深思。我们知道,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全科医生和麻醉师,母亲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兼作曲家。可能是性格和爱好不同,父母两人不甚相投。作为家中独子的李约瑟,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想从中架桥调和,让父母和好,但因缺乏条件并没能实现。父母的这种性格分歧对他的影响极大,后人推测他很可能从小就开始学习在这种分歧之中达到自己的平衡。也可以说他无意识地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科学的钻研精神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宽阔的胸襟和勇于创新的品格,而为了使父母亲能和睦相处,他又使自己处在“架桥”的状态中,在家庭纷争中得以保持自身的平衡,永远谋求把分裂的东西合并起来。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李约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调,并表现在他对待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等若干重大问题的态度上。
当然,推动李约瑟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投身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的动力还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女助手和自己早年生活经历的推手,著名科学史专家刘钝就发现,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经济大萧条等事件对青年李约瑟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苏联代表团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表现也对他的思想形成了不小的冲击。而早在1929年,李约瑟就出版了《唯物主义与宗教》,30年代他又陆续发表了《赞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与社会革命》、《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文章或文集。可以说李约瑟是当时剑桥大学“有形学院”的一员,他相信新人文主义的理想,相信人类在科学领域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消除一切种族的和阶级的偏见,促进民主和平等社会的早日到来,相信科学如同艺术和文学一样,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换句话讲,他相信自然的统一由科学的统一所反映,而后者不过是人性统一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他对非西方文明同情和理解的一个根本基石。这一切导致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之外李约瑟思想的两块重要基石。(103)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李约瑟又独钟道家,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他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104)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另一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教授认为“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105)。但这到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毕竟,如果没有,“中国情结”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作为生物化学家的尼达姆后来会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热爱是成就其一生事业的关键。
三、李约瑟眼中的中国科技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囿于欧洲中心论,多少认为亚洲文明没有产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当然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即对自然科学进行数学假设,再用系统的实验加以验证的体系的确崛起于近代西方。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即西方近代科学并不能与科学画等号,时至今日科学的真实内涵尚属当代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退一步说,就是以西方科学为参考系,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深入研究也对一向忽视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的贡献这一倾向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在早些时候,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106)“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我们骄傲和自卑的理由。我们不必为过去而过多地烦恼。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揭示其与未来的关系”(107)。为了了解世界和中国的过去,他耗费半个世纪的心力主编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该巨著总共7卷,34分册:
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1954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3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及水运机械钟在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内容最多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中国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动物学和医学其他分册正在准备中。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分析其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1954年该书第一卷出版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ArnoldJ.Toynbee,1888—1975年)就发表评论说:“李约瑟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除中国海峡两岸和日本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全译本外,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德国、墨西哥及中国香港也出版了节译本。中国科技史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学科,主要工业国家都已建立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机构,并自1982年以来,每2—3年就有一次中国科技史的国际会议。当然,该书的广泛流传对世人认识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这里就以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和天文、数学为例,一窥李约瑟眼中的中国古代科技。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中国的皇权政治有密切关系。皇帝通过科举制度招揽知识分子充实他的官僚队伍,因而就存在着“正统的”科学和“非正统”的科学之分,前者通常有财力和人才方面的便利。造纸术的发明便是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与封建官僚的归纳总结相结合的典型。在植物纤维纸发明以前,我国使用甲骨、竹简等作文书工具。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是在西安等地出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纪。这些纸以大麻和苎麻纤维制成,质地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东汉蔡伦是主管宫廷作坊的小官,他总结经验,深入实践,于105年发明了质量较好的纸,以树皮、破布、废麻为原料,成本也大为降低。至东汉末年,造纸业已形成一门独立的手工业。
纸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印刷术的发明就成为大势所趋。雕版印刷术一般认为是隋唐之际发明的。目前所见明确标有年代的最早印刷品是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宽1尺,长6尺,用7张纸黏合而成,除印文字外还有图画,印刷已相当精美。唐代中期的长安和成都等地印书业已相当兴盛,主要印农书、医书和字帖等。欧洲人最早看到的印刷物是蒙古人入侵欧洲时所带的纸巾和纸牌。现存欧洲最早的印刷品出版于1423年,那已是《金刚经》之后555年的事了。宋代以后印刷术有进一步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毕昇发明泥制活字印刷的事迹。元代王祯《农书》中附载有一篇《造木活字印书法》,详载了制造木活字和利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方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专著。欧洲最早用活字印刷的是德国人古登堡,他于1450年制成铅合金活字,印刷出版了《二十四行圣经》等书。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对传播中华文明、提高民族素质有重大意义,而四大发明经由古代丝绸之路传往欧洲,在欧洲社会中所起的革命性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
发明指南针的先声是对磁现象的认识。在西方,英国人尼坎姆于1190年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现象,知道地磁偏角存在已经是15世纪的事了。而在中国,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所载的“司南勺”可能是最早的磁性指示方向器。到了宋代,《武经总要》载有一种“指南鱼”,是以薄铁片剪成,用火烧红后按一定方向和倾角蘸水冷却制成的,使用时令其平飘水上即可指示方向。这是人工磁化的最早记载,其制作方法还表明当时人已开始利用地磁偏角了。稍后的《梦溪笔谈》又记载了以磁石磨针而制成的指南针,作者沈括还记述了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法并讨论其优劣,地磁偏角最早的书面记载也开始于沈括。朱阈则于1113年在《萍洲可谈》中首次提到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
最后我们来看火药,我们知道先秦本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文化中也曾出现过跟西方科学相一致的因素,诸如墨家对力学、光学和逻辑学的贡献。然而这些“非正统”科学最终也没能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尤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趋于湮没无闻。唯一的例外应该说是道家学派。”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乏当权者出于长寿的心理而给与的政治上的支持等,但其根基则扎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炼丹术士的最大成果就是歪打正着,炼出了足以摧毁欧洲封建堡垒、骑士团的盔甲和奴隶多桨船的火药。西方在13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中就记载了用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此后不久,火药就用到了兵器上。史料记载,公元970年和1000年都曾有人制成了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1044年的《武经总要》提出了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及其制作方法。早期的火药武器都还是以弹射或抛掷的方式投出,然后利用火药爆炸燃烧以杀伤敌人,但1259年发明的突火枪则是以火药的爆炸力射出“子窠”的管状火器,这是现代枪炮的发端。明代以后火药兵器更有大发展,手榴弹、地雷、水雷、定时炸弹、子母炮等都出现了,以火药作为推进动力运送火药至敌方爆炸的火箭也出现了,并有单级、二级、往复火箭等多种类型。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导致火药发现的炼丹术是在中国起源的,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14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著作。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300年)提到用锡、矾、寒监制造二硫化锡,而欧洲直到14世纪才初次提到此物。作为生理炼丹的副产品,李约瑟发现中国古人早在11世纪就开始从人尿中提炼激素作药物,而西方直到1927年才由阿什海姆和宗德克从尿中获得性激素;更有甚者,在提炼人尿中的类固醇激素时,中国古人竟然采用了皂素沉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西方到1915年才由温道斯发明,完全是现代化的方法。
四大发明之外,中国的天文和数学成就也很大。天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列为官方正统科学。因为统治者对授时特别关注,历政是国家政策,每个朝代都设有天文官,司天监是内府机构不可缺少的部分,采用皇帝颁布的历法就是臣服的标志,根本不允许民间私修天文。由此积累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古代天象连续观测资料,这些资料已成为现代天文学界十分珍视的宝贵遗产。李约瑟发现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自春秋至清初,日食记录约有1000次,月食记录约有900次,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首次记有哈雷彗星。自公元前28年以来系统地记录了太阳黑子现象,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次超新星记录,其中宋代记录到的1054年金牛座超新星爆炸的资料对现代射电天文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现在我国。公元前4世纪石申、甘德的《星经》比西方的伊巴谷同类作品早300多年,而其中星数比《天文大成》中的多三分之一。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约公元8世纪的星图是现存最早的,载星1350颗。而国外现存星图没有早于14世纪的,在17世纪前也没有一幅星图载星超过1100颗。我国古代历法之多居世界首位,前后共有105种。二十四节气为我国所独有,是为农业生产掌握时令而创的,大约在战国时期即已完备。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古四分历”即定一回归年为365.25日,与今测值只差11分14.53秒。南宋时期的“统天历”(1199年)的数据为365.2425日,与罗马教皇十三世在1528年颁行的现今世界通行的格里高历所用数值相同。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主要仪器,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东汉张衡除了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之外,他还创制了“水运浑天仪”,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元代郭守敬是赤道式天文装置——简仪的创始人,简仪是改进后的浑仪,它的赤道装置中的支架结构与近代天文望远镜普遍采用的天图式装置基本相同,而这种装置在欧洲18世纪才开始采用。中国人还利用机械装置使浑仪自动旋转,与天空每晚视运动同步进行,这就要求有机械钟的发明。李约瑟指出: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则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它是14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但实际上早在723年已由中国的僧一行制出。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合浑仪和浑象为一体,既可用于天文观测又可与以水力运转的浑象核对,还能自动报时。其中巧妙的擒纵器使报时机构作等时间间歇运动,堪称最早的机械钟。
天文历法的进步是以数学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尤其是代数学成就斐然。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可称是我国最早的天文数学著作,其中已有勾股定理和比较复杂的分数运算。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九章算术》则是我国第一部最重要的数学专著,其中所述的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等都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关于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则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三国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了详注,用出入相补原理证明勾股定理,用无穷分割法证明方锥体的体积公式,用圆内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接近圆面积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π=3927/1250=3.1416。此后南朝的祖冲之继续研究圆周率,得出3.1415926<π本纪中记载科技内容为计量对象》,载《科学研究》2007(2)。
⑤ 孟庆云:《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载《中华医史杂志》2002(3)。
⑥ 赵显明:《试析程朱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载《晋阳学刊》1995(6)。
⑦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⑧ 席泽宗:《科学史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⑨ 《王安石全集》卷第六十二。
⑩ 《王安石全集》卷第六十二。
(11)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58页。
(12) 《朱烹·朱子语类》,见《四库全书》,中国台北:商务印刷书馆,1986年,第25页。
(13) 《朱子语类》卷十八。
(14) 《朱子语类》卷十五。
(15)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16)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5、200页。
(17) 《六祖法宝坛经》。
(1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2页。
(1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页。
(20) 袁运开、周澣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577、578页。
(21) 赵国权:《从科技创新看宋代的科技教育改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5)。
(22) 沈括:《梦溪笔谈》。
(23) 沈括:《梦溪笔谈》。
(24) 乐爱国:《北宋儒学背景下沈括的科学研究》,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6)。
(25)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论文集》,1988年。
(26) 朱熹:《朱子语类》。
(27) 朱熹:《朱子语类》。
(28) 朱熹:《答江德功》。
(29)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03—517页。
(30) 〔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2页。
(31)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6页。
(32)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33)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34)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09—210页。
(35) 孙锦泉:《中国造纸术对8—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36) 杨巨中:《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37) 沈括:《梦溪笔谈》卷18。
(38) 〔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1页。
(39) 李晋江:《指南针、印刷术从海路向外西传初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6)。
(40)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1页。
(42) 余军华、李贞芳:《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视野的解读》,载《经济师》,2007(2)。
(43) 许会林:《中国火药火器史话》,北京:科普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44) 刘旭:《中国火药火器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247页。
(45)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207页。
(46) 潘吉星:《中国对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2)。
(47) 王充:《论衡》。
(48)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49)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
(50) 李晋江,《指南针、印刷术从海路向外西传初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6)。
(51) 朱寰、王晋新:《论西欧大航海活动的科技文化条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1)。
(52) 潘吉星:《中国对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2)。
(53)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2页。
(54) 万斌、金利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1)。
(55) 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载《学术研究》,2002(7)。
(56)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载《今日中国》(中文版),2001(12)。
(57) 阿浦:《中国航海事业的先驱——徐福》,载《瞭望》,1984(37)。
(58)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9) 班固:《汉书》。
(60)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译,第447—448页。
(61) 〔法〕布尔努瓦著,耿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杜2001年,第45页。
(62) 卢苇:《唐代丝路的变化和海上丝路的兴起》,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63) 《中国全史·中国宋辽金夏科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页。
(64) 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比较之研究》,载《南方文物》2005(1)。
(65) 史仲文编:《中国元代科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66)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8页。
(67) 张廷玉:《明史·郑和传》。
(68) 金水兴、杨权斌:《郑和航海与新世纪航海技术展望——兼论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技术发展的贡献》,载《航海技术》2005(3)。
(69)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70) 王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药外传:宋代中药海道外传路线考述》,载《广东社会科学》1992(2)。
(71) 陆芸:《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交流》,载《中国宗教》2007(10)。
(72) 吕变庭:《论回族先民在宋代科技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3) 蓝勇:《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载《学术研究》1995(6)。
(74) 蓝勇:《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载《学术研究》1995(6)。
(75) 刘树勇、王士平:《明代科学发展的迟滞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
(76) [清]高宗敕撰:《钦定续通典》卷十九《选举三》。
(77) 阎若璩:《潜丘札记》卷四上,清乾隆十年春西堂刻本。
(78) 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79) 张学智:《中国实学的涵义及其现代架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80) 金其桢:《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8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82) 李贽:《四书评·大学》。
(83)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4《贺李汝立应科举序》,崇祯十一年刊本。
(8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85) 刘重日:《明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略论》,载《求是学刊》1994(3)。
(86) 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87) 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88) 汪前进:《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科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89) 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载《学术月刊》1999(1)。
(90) 中国实学研究会主编:《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61页。
(91) 王允红:《朱载堉和十二平均律及其对中西方音乐的影响》,载《音乐探索》1995(4)。
(92) 郭涛:《16世纪的治河工程学——<河防一览>》,载《中国水利》1987(1)。
(93) 金萍、丁祖荣:《关于程大位及其<算法统宗>评价问题的探讨》,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3)。
(94) 汪前进:《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科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95) 刘明:《论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及其实践——兼论<农政全书>的科学地位》,截《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96) 赵书刚:《吴有性<温疫论>对传染病学的创新性贡献浅释》,载《中医药学刊》2005(1)。
(97) 马湘一:《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物质化观点》,载《书城》2007(9)。
(98) 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
(99) 程燕平:《古今中西第一人——李约瑟及其中国科技史研究》,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8)。
(100)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0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24页。
(102) 参见陈明远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O10081uf.html
(103) 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
(10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105) 江晓原:《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
(106) 李约瑟著、刘小燕译:《世界科学的演进》,转引自《人类应该善待自己》,振兴、陈民琦,《社会观察》2004年第5期。
(107)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108)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自然杂志》,1990(12),第818—827页。
(109) 马湘一:《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物质化观点》,载《书城》2007(9)。
(110) 具体内容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3/09/content_767365.htm
(111) 刘钝、王扬宗:《“李约瑟难题”: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一书》)。
(112) 刘钝、王扬宗:《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瑟难题”研究》,载2002年4月24日第24版《中华读书报》。
(113) 刘钝、王杨宗:《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瑟难题”研究》,载2002年4月24日第24版《中华读书报》。
(114) 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前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亦可参见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页,网址: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ndpzl.htm
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孟昭勋,张蓉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